西環碼頭自3月起遭海事處以防疫為由封閉,不准工作人員以外人士進入,大家失去了一個打卡勝地。除了打卡碼頭,香港還有很多不同功能的碼頭。我們走訪香港不同碼頭,嘗試拼湊出碼頭和渡輪昔日的風光,以及如今沒落的原因。
【觀 塘】
香港作為一個沿海城市,碼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過去陸路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市民也要靠水路去不同地方,甚至乎可以駕車上船。三十年代,香港設有汽車渡輪路線,最初只有來往中環和佐敦道的航線,到後期加至北角、觀塘、九龍城等也設有汽車碼頭。「現時觀塘碼頭只有四條行車道。」在船公司工作了四十年的胡永新解釋。
一九七四年,觀塘碼頭汽車渡輪航線啟航,那時有六條行車線供車輛駛進碼頭。同時設有一條斜路讓汽車上二樓上船,因為最初時汽車渡輪兩層也可以載車。之後才將部份船隻二樓改裝成可以載人。胡永新憶述當年打風前觀塘汽車碼頭的情況,「那時將近打八號風球,有約一千人在候船室等候。我要立即加開一班船,一次過載全部人過對面海。」
七十年代海底隧道和地鐵先後通車,汽車渡輪的需求大大減少。結果在一九九八年最後一條來往北角及九龍城的汽車渡輪航線停辦後,市民便無法再駕駛愛驅上船過海。現時香港只剩下三個汽車碼頭,分別是觀塘、北角及梅窩,當中梅窩汽車碼頭只是作緊急情況下使用,如青馬大橋等交通設施無法使用時,可向相關地區市民提供緊急服務。因此現時仍會恒常使用的汽車碼頭,就只有觀塘和北角,每日有固定約四十航班往返兩地。那麼到底是甚麼車輛還要靠渡輪過海?由於現時載有第一、第二及第五類危險品的車輛不能使用海底隧道,只可以靠汽車渡輪往返北角和觀塘。
採訪時遇上需要運送第一類危險品的渡輪,發現現時一層大約可以接載十輛危險品車輛。「以前一層可以泊約四十四輛私家車。」有三十八年駕駛船隻經驗的梁樹添船長介紹船隻甲板,以前的私家車體積較小,現時一個車位,當時可泊兩輛車。添船長是水上人,上岸後曾經在工廠工作,不過覺得工作乏味,最後還是決定回到船上工作。他再帶我們到駕駛艙,示範如何控制船隻。若載有危險品的船隻,航行前先要升一面紅旗,提示其他船隻提高警覺。現時來往北角和觀塘的路線較以前簡單,「以前這裏是機場跑道,有十數支燈指示飛機升降,所以船隻不能駛近。」
有別於一般船隻,這艘船有三個軚盤,分別控制船頭、船尾和油門。他表示要花兩、三個月練習才可以操控到這艘船,「我以前也要趁放假時,觀摩其他船長如何駕駛,然後再自己練習。」添船長又指如果由水手開始行船,要花上四至五年的時間才能當上副船長或船長,所以也並不是一件易事。
添船長曾經駕駛過不同船隻,無論載人載車也難不到他。他指自停辦汽車渡輪航線後,公司也經歷了數次轉型。先是改為接載建築工人到赤鱲角機場,之後又做遊客生意,載他們遊維港、看煙花等。「(以前試過)剛離開長洲時,有一位孕婦突然說作動要生仔。那時候只好立即找船上有醫護經驗的人,清潔洗手間,讓她在內生產。」添船長笑說翌日那位孕婦的丈夫買了一打西餅給一眾船員,答謝他們幫忙。他甚至遇過有乘客因為失戀或生活不如意而突然跳海。相較之下,現在只需要每日運送危險品車輛往返維港兩岸、檢查船隻配件等,自然就輕鬆多了。
被問到現時是否很少人願意入行時,添船長笑說近來還是有數名新來的副船長,當中更有一名女同事!他補充說,近數年入行人數都在下跌,「近年地產收入高,好多人都喜歡做地產,讀得書嘅就寧願做建築工程。」他並不擔心行業式微,「總會有人駕駛,人數可能再少一點而已。」對見證着汽車渡輪碼頭高峯與低谷的添船長來說,入行人數減少只是另一個轉型的契機,畢竟他一路走來都是不斷從轉變中尋求生存空間。現時面對這個困境,既來之則安之,將來總會找到生存方法。
反而令添船長思考得更多是自身的問題,年屆六旬,他說是時候退休了。看看身後的巨大渡輪,他感嘆希望可以多做幾年,只要自己身體情況許可,也想盡可能繼續駕駛船隻。是甚麼令他近四十年也願意留在船上?「呢艘船差唔多係我屋企。」有時候工作晚了,就直接在船上睡。船員們就像家人般,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今晚吃甚麼、怎樣煮,「開開心心便是一天。」在外人眼裏,渡輪只是一種交通工具,但對一眾船員來說,卻是他們生活半生的地方。碼頭與渡輪,就是他們最親切的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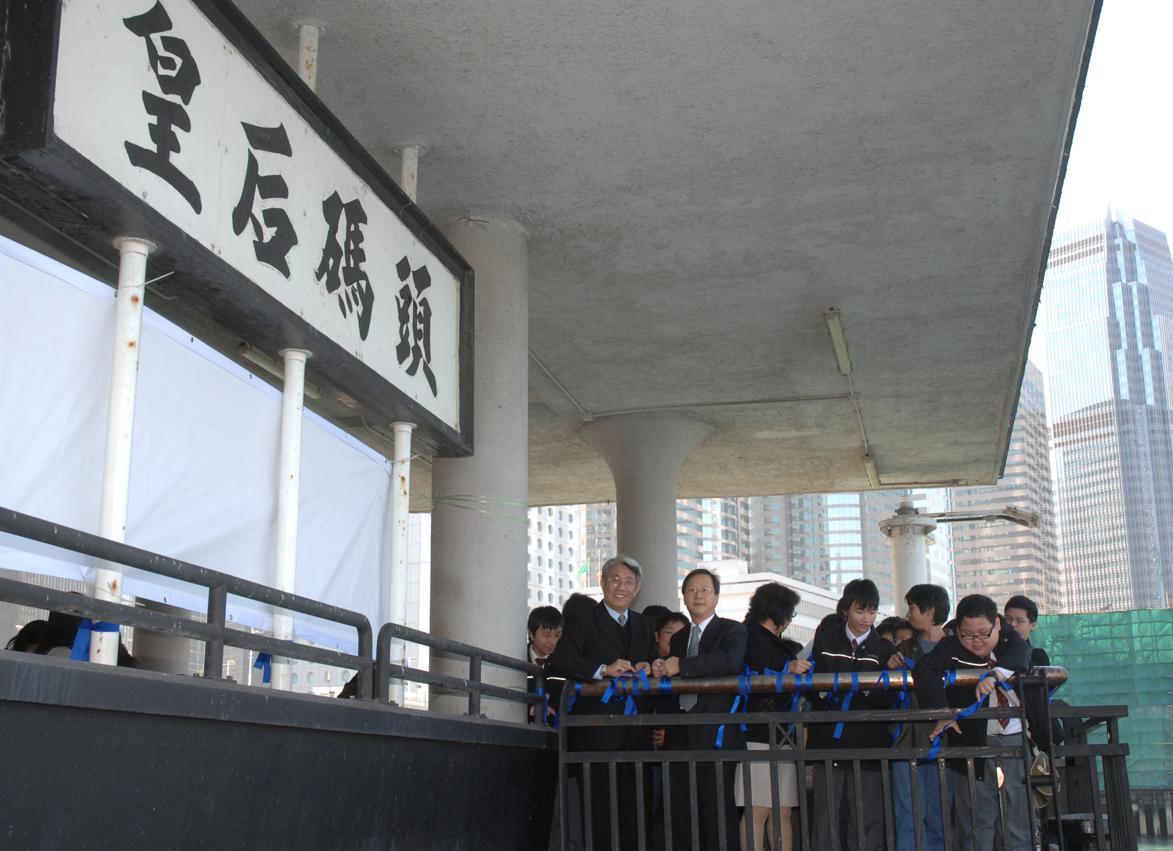
【北 角】
假如大家從九龍城碼頭出發,乘船前往北角。落船後,你就會發現一個可能是全港獨有的碼頭奇景。還沒出閘,你便會聽到叫賣聲,「埋嚟睇埋嚟揀。」出閘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檔檔海鮮檔。大抵全港市區,就只有北角西碼頭有「附設」魚檔。
90後劉婉婷(Belle)是書籍《沿海小札—記東區碼頭》的編輯之一。她聯同另外兩位拍檔親自做資料搜集、訪問街坊等,發掘東區碼頭不同的有趣故事。這次她就帶我們到北角碼頭,介紹這裏其中一個特色民間宗教活動——放生。
在北角西碼頭建成前,沿海一帶已有攤檔擺賣。直到碼頭落成,攤檔才遷入碼頭內梗舖。而且碼頭位於大型商場北角匯對出,即以前的北角邨,接近民居,漸漸吸引不同人來到這裏買海鮮放生。Belle曾跟隨不同團體放生。她指放生地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糖水道碼頭,第二則是西碼頭內的滑梯。
「這條滑梯聽說是海鮮檔特意為放生客而設。」她解釋如果直接投放一些甲殼類海產進海中,海產容易因硬殼撞擊海面破裂而死亡。故此便可以用滑梯減低牠們直接撞擊水面的衝擊力。不過有時候放生客會跟附近的釣魚客爭執,「例如在糖水道碼頭放生,幾步之遙就已經有些釣魚客在釣魚,甚至會用魚網撈。」
採訪時先後遇上兩個放生團體,那時才發現,放生的人不只是中年人或老人家,還有些目測只有廿多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會先念經上香才放生;有的則會直接放生。看見魚檔用手推車將一箱又一箱的海鮮推到滑梯附近,不禁向Belle問,放生的海鮮種類有沒有限制?「曾經問過幾位海鮮檔檔主,他們都說沒有限制,甚麼海鮮也可以放生。」
整個下午,除了鱔、八爪魚,連魔鬼魚也有人放生。當日其中一個放生團約20人,Belle指曾經看過約有40人的團體在這裏放生。每逢初一、十五或假期會有較大型的團體放生,但即使平日也會有附近居民來放生。
問Belle為何會以碼頭為寫書題材,她指香港由一個小漁港發展至國際大都會,碼頭和船彷彿就是大家的根,「我們常說好鍾意香港,會不會着緊多些、用筆記錄下來?這樣才表達到『有幾鍾意』。」她直言為書本做資料搜集前,對碼頭有着很浪漫的幻想。特別是對新一代來說,整個成長環境中,基本上都是港鐵和巴士,「碼頭會不會是我們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但在過程中,她發現碼頭除了是一個日常出入的地方,附近的居民更可以在這裏找到心靈寄託。




【九龍城】
碼頭除了讓市民往返香港各區,更是讓人探索世界的地方,正如歐洲各國當初也是乘船來到這片東方土地。那麼到底香港的碼頭歷史可以從何說起?
對香港歷史有深入研究的鄧家宙博士帶我們到九龍城碼頭,他推斷早在宋朝期間,九龍城一帶已是有約2,000人的村落。按地理位置看,九龍城一帶對海上絲綢之路來說,是南中國其中一個重要的補給點,「馬頭圍原名是古瑾圍。有人推論這裏會不會曾有一個大型碼頭專門替海外船隻補給,所以這個地方就叫馬頭圍?」不過鄧博士補充指,這個說法仍要待發掘出一些碼頭遺蹟等才能肯定。
雖然未能肯定宋朝年間有沒有碼頭,卻可以肯定清朝時,九龍寨城有碼頭供人出入。「外來的人去九龍寨城除了經陸路,也會由水路進來,所以那裏有一個龍津碼頭。」鄧博士稱當時龍津碼頭是一個較知名的碼頭,然而對比現代碼頭還是有很大分別。
他指現時碼頭可分為兩種生態,一是本地居民生態,例如碼頭附近通常也會有巴士站、街市等,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特別是巴士站,因為香港地形限制,居民需要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到內陸不同地方;另一種則是專供外地人使用。因此在碼頭附近會有客棧、酒店和風月場所等,例如以前的油麻地碼頭和石塘嘴一帶。
鄧博士認為,隨時間推移,碼頭和渡輪的角色越來越被淡化。在他眼中渡輪還是無可取代,「船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直接點對點。」他舉例說,如果九龍城或紅磡居民要去北角,很多人都會選擇渡輪,而非巴士或地鐵。更重要的是,碼頭對香港來說象徵探索世界,「特別是古代,我們的生活圈子就只有自己條村。」鄧博士解釋,每個人就像一個點,會跟其他人產生連結。以前我們只能連結自身所在的地方的人們,不過當人們可以在碼頭乘渡輪出發往不同地方時,就可大大擴闊人們的生活及社交圈子。



記者:麥景朗
攝影:周芝瑩、潘志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