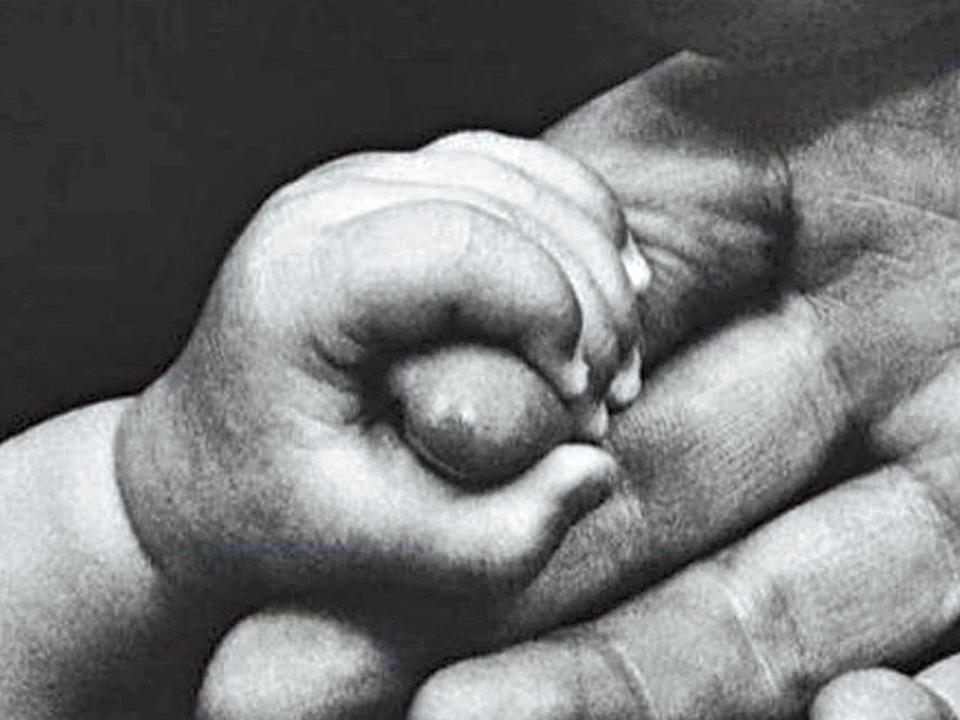《心碎的女人》(Pieces of a Woman)理應是Vanessa Kirby一個人的故事,因為只有她的角色Martha,才如實明白由懷胎到分娩,到目睹BB在自己眼前出現,再轉瞬間死亡的痛楚。
撰文:月巴氏
我是一個深受殘酷血腥電影訓練的人,亦早知《心碎的女人》會有一場接近半個鐘、一鏡直落的分娩戲,做足心理準備,估不到看的時候,還是頂唔順這種(我絕對不能體驗的)痛楚,其間甚至諗過fast forward或跳過去就算——但不能這樣做。這個痛的過程,是讓整個故事成立的前設,正如我們去經歷生命,也不容許加速度過或跳過某一段過程。
在過去,這場戲大概只會用五分鐘、甚或暗場方式交代就算,導演Kornel Mundruczo卻要我們直視整個過程——他的伴侶,亦即這齣電影的編劇Kata Weber,便經歷過流產的痛苦。《心碎的女人》,源自這悲劇。然後一個半小時,是悲劇的各種後遺。這明明是一個人(或一對夫妻間)的事,卻變成眾人之事。躁動的藍領老公Sean失望極了,但依然想找方法拯救自己和太太,戒掉酒癮的他選擇了飲酒,又嘗試用暴烈的性,去拉近自己與Martha的距離,但統統失敗(麻醉自己這方面倒很成功),最後甚至搭上另一個女人。
Martha反而很平靜,出奇地平靜。很快,就回到工作崗位(卻發現自己張枱被另一個男人佔用);收工後,不立即回家,去夜場,遇上男人挑逗來者不拒,卻又突然回復理性。她用理性,對抗痛楚。這種痛楚明明只有Martha才明白,偏偏世人都樂於參與分享。
潛伏社會的道德判官紛紛責難助產士,指她是害死BB的元凶;阿媽(Ellen Burstyn飾)啲friend遇上Martha,會親切慰問,但Martha只覺煩,心諗關你鬼事——阿媽啲friend之所以知,全因這個控制慾過強的阿媽,太想為個女討回公道,於是死去的BB變成象徵公義的物件,這個短促的生命,在世人的積極介入下,扭曲成一個意義被任意添加和使用的存在物,Martha最不能接受這一點。
但應該怎樣去補償這份痛楚?一般人的看法:用法律將助產士定罪,判監,並取回金錢賠償。約定俗成,罪與罰,不可分。
萬般不願的Martha,最後還是來到(為她討回公道的)法庭,在回答(站在自己一方的)檢控官和辯方律師提問時,恍如再經歷一次那份痛楚,那份由懷胎到分娩到目睹BB在自己眼前出現,再轉瞬間死亡的痛楚,她承受不住,想唞一唞,法官批准,退庭,下午繼續聆訊。
Martha很想知道,這個曾經短暫來到世界,並在自己懷中哭過呼吸過的真實生命,對她,存在着甚麼意義?意義,主宰着她面對這場訴訟的態度。Martha的抉擇,由你自己去看;只想說的是,這不是一場壹號皇庭,不是女人復仇戲,更加不是試圖宣揚用大愛戰勝一切,而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女人怎樣面對自己,面對只有自己才能明白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