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環荷李活道的Club 71(七一吧),前身是座落蘭桂坊的Club 64,30年來都是香港學運和社運界聚腳地,在反送中時即使生意冷淡,仍然多次向示威者開放,如今敵不過武漢肺炎,一個時代的酒吧,要告別了。
十幾年前羅大佑請了一位居港英國人為他維修木結他,那英國人拋下一個中環地址,要他去那兒取貨。羅大佑沿卑利街斜路轉入一條冷巷,才發現藏身百子里公園前的酒吧Club 71。
這兒跟中環其他酒吧不同,客人有大學講師、社運人士、文化人和音樂人,即使素未謀面也很易打成一片,令這位結他技師Simon Pinder深愛不已,多年來常約客人來交收結他,包括後來成為朋友的羅大佑。
Simon說:「香港的酒吧要麼全是外國人,要麼全是香港人,只有這兒文化融合,外國人和香港人對等交流。」Club 71的外國人也特別關心香港時事,Simon常跟其他酒客討論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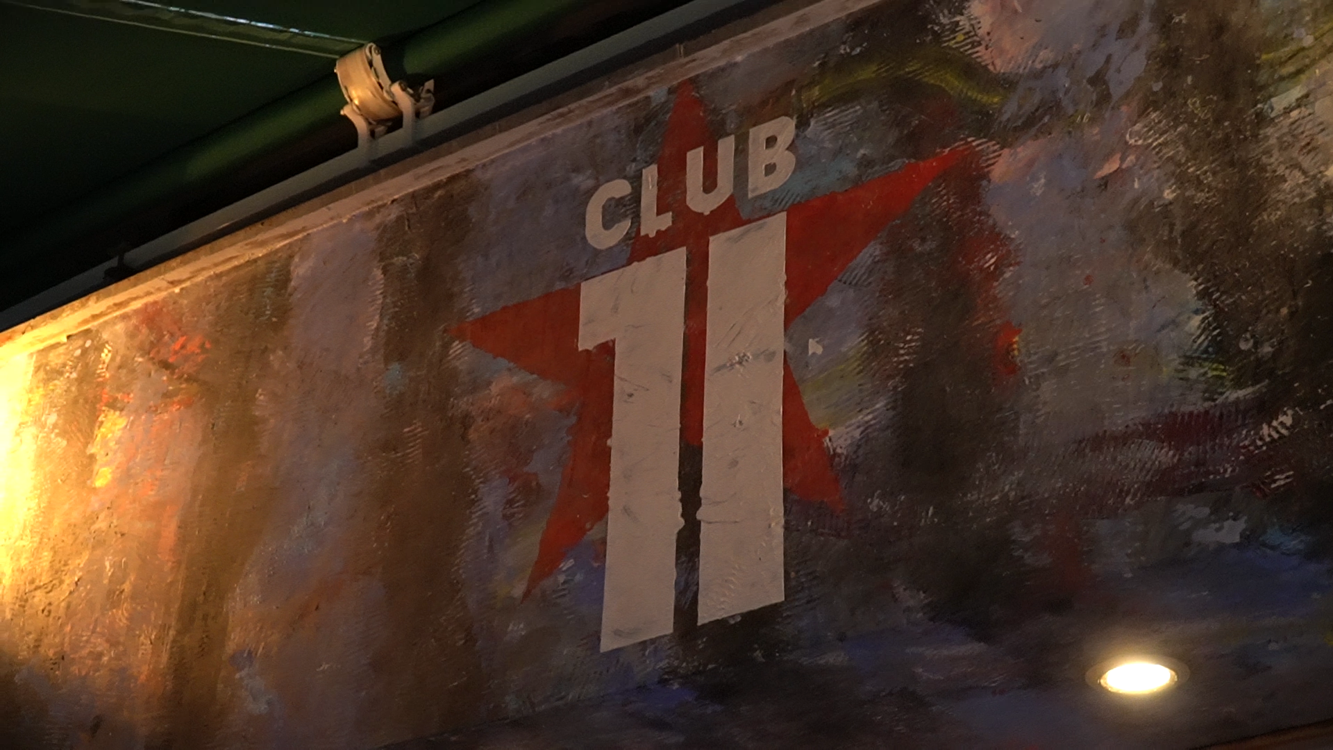

這晚他跟太太Freda抱着子女來Club 71。雨傘運動那年,他們在Club 71相遇,女方是髮型師又參加反高鐵運動,Simon對她一見鍾情,當晚問了她的電話號碼,兩日後約人家拍拖,居然又走去Club 71。
雙方的朋友多是Club 71常客,婚禮也乾脆在這兒舉行,婚後照抱着子女來酒吧,在人家飲酒的椅上換尿片。Simon:「Club 71是令我留在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我住離島,這是我在市區的家。」
Club 71反送中時經營困難,獲業主減了一點租金,但武漢肺炎令生意更慘淡,休業三個月要照交租,這時業主要求收回原有租金,Club 71老闆馬麗華決定於10月30日結業。消息傳出後,這晚很多人像Simon趕來幫襯,大家對這間酒吧戀戀不捨,反而要馬麗華安慰,「有些人口裏沒說可惜,但眼神很不捨,不過凡事有聚有散。」
Club 71的酒客與別不同,因為這位酒吧老闆也與別不同。1990年,即六四屠城翌年,馬麗華明明滴酒不沾,決定跟朋友在蘭桂坊開Club 64,她當時想,「如果日常生活有人提六四,一年就不會只有六月四日才提。」
正如一年半前,店舖沒有計劃做黃店,只因為參與反送中而吸引同路人,Club 64也自然吸引了關心社會的酒客,約聚會就說:「今晚去六四。」2004年,Club 64抵不住蘭桂坊租金要結業,半年後搬到現址,改名為Club 71。
一間酒吧結業,酒客大可以去另一間酒吧,但Club 71不是普通酒吧,而是結識志同道合的地方,於是像Simon這類Club 64舊客,才會不離不棄追隨到Club 71。



這兒的客人卧虎藏龍,試過有人高聲讀詩,鄰桌用笛音和應;有人把玩牆上的結他,即有其他樂器和音,馬麗華說:「在這兒玩音樂無需約定,只要有一個人開始,自然有其他人加入,試過有人帶着大提琴來,我們要關門隔音。」
Club 71沒有廚房,只供酒不賣食物,大家也不介意買外賣來飲酒,甚至帶自己煮的食物來分享,「有位客人經常下廚,明明那晚煮三鞭湯,又會故意為兩位食素的同事煮齋。」其中一位食素的同事正是店長陳小萍。她以前是學運骨幹,做過環保組織和議員助理,擁有一個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四年來負擔Club 71主要工作。她連休班的日子也約朋友回來聊天,明明自己是客人,也欣然為其他客人服務,斟茶遞酒。
由Club 64至Club 71,馬麗華經營酒吧至今30年,早就想有年輕一代接手,也很樂意熟客自己開又叫Club 71的酒吧,她說:「很多客人跟我說七一吧跟其他酒吧不同,來到好像回到家裏,很易找人聊天,那麼最好每區都有七一吧。」


採訪:呂珠玲
攝影:陳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