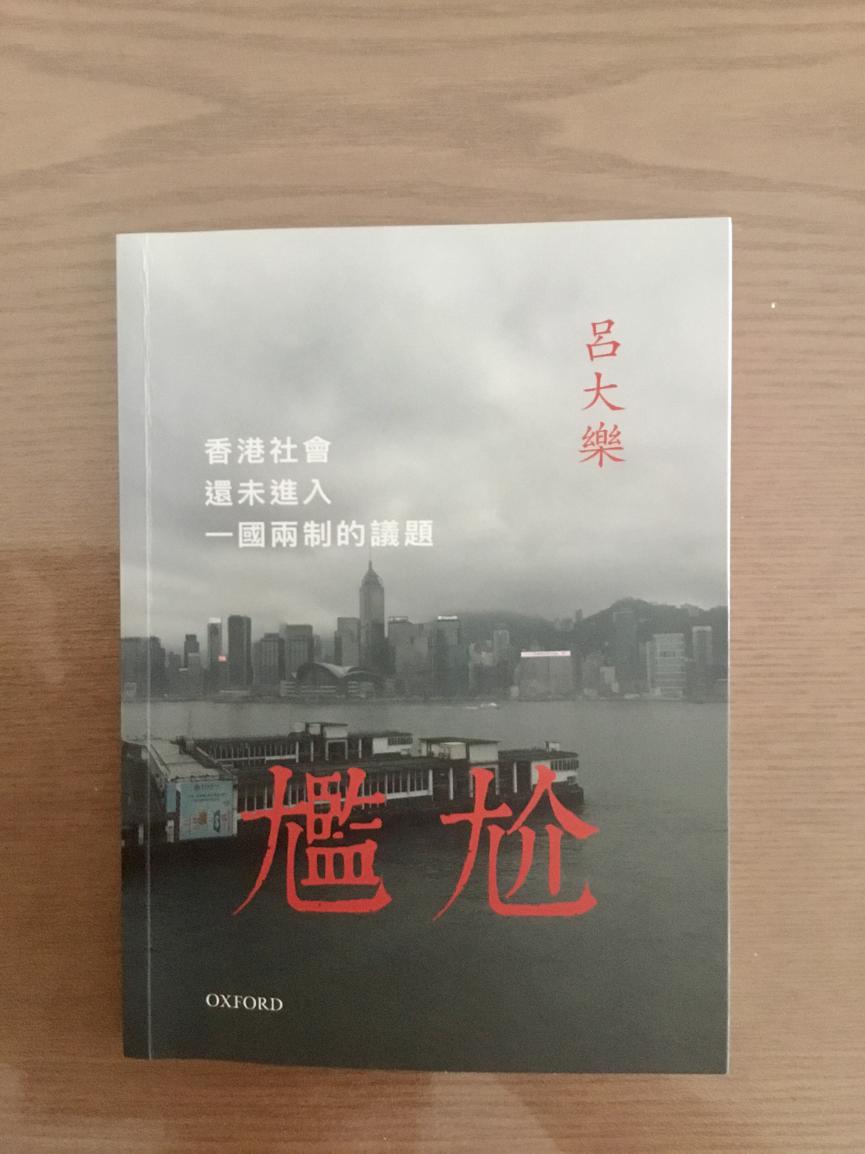
陳同佳是否赴台自首,又再令香港人思考反送中運動的前因後果。對於香港未來,中共已畫下紅線,港獨不容討論,一國兩制可以討論,但中央全面管治權沒有討價還價餘地。香港人對這種現狀並不接受,於是由2014年開始爆發持續的抗爭運動。
今天介紹呂大樂的作品《尷尬》,這書可說是在持續抗爭運動下,對九七回歸至今「一國兩制」問題的反思。
作者認為持續的抗爭,沒有帶來制度上的變革,「2019年反修例運動將衝擊推上到更大的規模,但因一樣承襲了之前兩次社會衝突的特點,就是沒有進入現有的政治框架之中,從中摸索改變的空間。這些社會運動沒有發展出什麼談判、議價的元素,主要是只有『全贏』或『全輸』二選其一,基本上不會在既存的框架來尋求空間。由於這是一場『全贏』或『全輸』的遊戲,路線是否純正變成為很重要的考慮點;任何中間落墨,或者議價的意圖都會招徠懷疑。」
呂大樂認為香港問題的尷尬位,是所謂前途問題從來都不是追求一個將問題圓滿解決的方案,而是想辦法怎樣可以令現狀不會發生巨變,這是政治妥協的結果,妥協背後的想法,是維持現狀,而所謂維持現狀,並不單止指九七前,而且是九七後將「現狀」延續下去,這種「不變」成為了束縛,於是素來靈活適應變化見稱的香港人,抱着一種靜態思維而不自覺。在這種「冷藏」香港的政策中,制度發展停滯不前,但市民對問責及參與呼聲日高,於是形成巨大落差,政府支持度不斷下降。按照一國兩制原來的構想,是需要資產階級的積極參與的,但商界卻在政治舞台上缺席,未有投入建設一個符合資本主義長遠發展的政治制度,並扮演其獨立的角色,對香港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另一尷尬之處是香港的建制派,他們沒有發揮協助政府施政的角色,當權者無法駕馭一個並非完全民主化的整體,本來處於優勢的政治建制也從來沒有做好作為建制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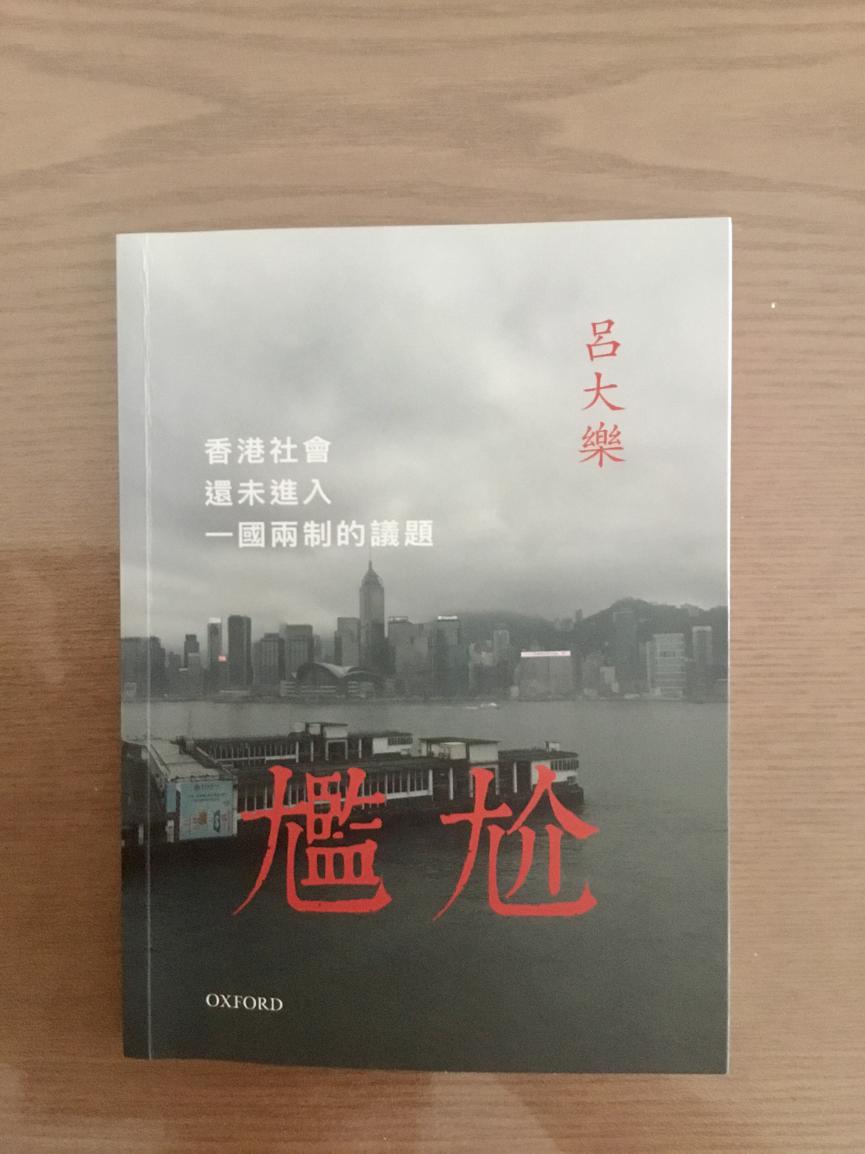
作者指出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耐人尋味之處,是假設特首可以單人匹馬進入政治系統裏主持大局,而政治藍圖設計的潛在議程是對選舉政治、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的排斥。
作者對一國兩制的病徵的診斷都是正確,但究竟「病灶」何在呢?是香港商界懶散、建制派欠水平、公務員名過其實,中共欠長期規劃……?如果找不出「病灶」便很難對症下藥。我嘗試提出另一個解說:冷藏香港是中共計劃之中,起初源於妥協,其後變成了方便的藉口,冷藏的目的是要令中共的組織機器逐步控制議會、政黨、選舉政治,以至政府,即是buy time!無論資產階級治港、愛國者治港等都是「掩眼法」,資產階級代表本是香港商界代理人自由黨,九七前有劉漢銓譚惠珠另組工商界政團港進聯制衡,2003年七一後中共肢解自由黨,挖走林健鋒、發叔、劉柔芬加上西環契女另組經民聯。至於愛國建制派山頭林立,又民建聯又新民黨,這不就是中共的部署嗎?特首駕馭不了半民主化的體制,源於背後還有黨組織,特區政府弱化的政治能量,才符合中共的利益,因為一切政治權力只是轉授。對呂大樂而言,特區政治體制設計的不合理,耐人尋味,因為他欠了分析共黨在香港管治這一塊重要砌圖。
一國兩制始於權宜,終於權術!
撰文:劉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