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代理的案件涉及政治,很敏感、很危險。」2020年12港人偷渡案中,一些相對陌生的人權律師名字走進公眾視野。與近年大多數內地維權案一樣,他們遇到了被拒會見、被司法部門施壓退出的難題。
事實是從2015年709大抓捕,到2018年大規模吊銷執照潮,站在最前線的中國維權律師幾已倒下。不能在法庭上辯護的律師們,職業生涯搖搖欲墜,維權又從何說起?大抓捕後無法執業的王宇、投入人權領域的年輕律師,都把眼光看得更遠——維權律師的舞台不只是法庭,更重要是法庭外的揭露,並為未來作力量的保存。

「如果我有牌的話,那是肯定會去參與。港人被抓雖然非常敏感,但作為我們來說,對香港人都有一份感恩之情,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機會,去表達感恩之情。」曾為郭飛雄、黃琦等異見人士擔任代表律師的隋牧青,多次在訪問中提到港人案,這種想辦而不能辦的心情。
因為早在2018年,他已被當局無預警吊銷牌照,終止了他19年的律師生涯。
「他們(廣東司法廳職員)是用一個藉口,說司法部門要檢查工作,我是律師所裏很特別的人物。到了律師所,他們衝進來十幾個人,又拍照又錄像的,宣佈要吊銷我的執照」。不止是隋,那一年,從年初的余文生、祝聖武開始,大批知名維權律師被註銷或吊銷律師執照,圈內人稱之為「吊證潮」。

註銷律師證理論上仍然可以再申請,但吊銷可以說是為律師判了死刑,因為律師無法出庭、無法代理訴訟案件,是對律師最嚴厲的處罰,而52歲的隋牧青恰恰是後者。過去三年,他一直在家裏休養生息、照顧孩子,基本沒有收入。他希望靠寫文章賺一點打賞,但一開設微信公眾號卻又被封掉,重新就業的問題懸而未決。
「2018年吊證潮後,吊證註銷的一大批,事實上很多律師即使沒有經過吊銷程序,但仍然無法執業,可以說基本上過去的一線律師,絕大部份都被消滅掉了。」
在北京,709大抓捕當年被抓的第一人王宇,正是未經歷吊銷執照程序,但無法以律師身份執業的一人。「我的執照既沒有吊銷也沒有註銷,但因為司法局限制我轉所,我們所在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又被吊銷了,也沒有律師所接受,所以不能執業。」她的丈夫包龍軍也在709後,實習律師的身份無法轉為正式執業律師。
王宇本是中國著名的「死磕派」(意指作對到底)律師。她所在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大量代理法輪功、訪民等敏感案件,並且透過網絡平台,將代理的案件、法庭內外的違法情況傳播開去,使許多不為人知的案件成為熱話,因此成為當局「眼中釘」。2015年7月9日,709大抓捕便就從抓拿王宇開始。她在受威脅之下,上演了電視認罪的經典一幕,經歷關押及監視居住13個月,才重獲自由。
雖然無法執業,但在中國,訴訟案除了律師代理,還可由當事人委託其他公民代理。這成為王宇代理案件的途徑,過程中卻屢遭當局限制。「比如有十個案子,可能有八個受限,但大多數都被限制,而且是完全針對我們個人」。例如現在做公民代理需開設社區介紹信、無犯罪紀錄證明等文書,她試過成功開出,甚至已經開庭,也會被公檢法部門針對,要求社區撤回已開出的介紹信。加上無法代理刑事案件,基本只能做拆遷等民事案件,「時間長了,找我們的人越來越少了,案源很快要枯竭」。

工作上清閒不少的王宇,這半年忙於照顧患病的父親。生活被逼退到如此地步,但她嫉惡如仇卻勝似當年。在訪問中,她仍然一遍遍重複「中國沒有法治!」「中國是有法律而無法治」的論述。幾十年來作為法律人,這樣說看似很矛盾?在沒有法治的國家,要怎麼談法律維權?
「雖然這個法律是欺騙全世界的,但既然你把法律頒佈出來,我們就要把法律作為真正的法律去用」。王宇認識到這一點,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她因投訴天津市公安局不作為,而被構陷入獄兩年半。正正是親身體驗到司法黑暗,在2011年獲釋後,她從商業案件轉為全力做維權案件,幾乎沒有代理過其他案件。因為做一宗維權案件花費的力氣,足以做五至十宗其他案件,向看守所要求會見,總是關卡重重,被拒絕是家常便飯。2014年代理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案,她去了新疆三次,才成功會見到當事人。「要跑派出所、要跑檢察院、要跑公安局,反正跑很多地方,你要去控告、去投訴。如果公安說不讓會見,你就回來了,那你永遠也見不到!你要做大量工作。」
六年前仍有可能會見當事人,但從12港人偷渡案中看到,當局會以官派律師為名,阻止真正的律師介入案件,那辯護又談何說起?王宇認為,當下中國維權律師的角色,不僅在於法庭上,更重要是在法庭外,擔當被告的代言人。
「在中國這種環境下,律師的主要工作,不是會見當事人,不是在法庭這個小法庭去辯護,而是把當事人被迫害、被打壓的事實揭露出來,把它展現於國際媒體下,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國政府對弱勢群體的打壓和迫害 ,他們的工作應該主要是這樣。」
「在法庭上辯護得再好,辯護詞寫得再美,法理闡述得再好,他會聽你的嗎?不會,他們只是黨的一個喉舌……他(法官)如果是一個法律人的話,你的代理意見闡述得非常透徹,你可能會打動法官、檢察官,但是中國不是法治國家,法官、檢察官是政府的代言人,黨、政府讓他幹甚麼就幹甚麼,讓他怎麼判就怎麼判。你寫得再好也沒意義。」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為律師,他也沒有辦法不自我保護一下,很矛盾」。因為中國的維權律師現狀,幾乎就是用一張證,甚至是自由,去救一個人,王宇甚至用「殉道」去形容。當年她被抓後,為她奔走疾呼的代理律師文東海和李昱函,一個被釘牌,一個因「尋釁滋事罪」仍被關押,不判不審。失去執業資格的她,現在苦於有一身好功夫使不出。「很多事情很着急、很想去做。我現在要是律師的話,我就要去代理他的案子,想為他們發聲」,王宇感嘆。
「我不是承認中國給的律師證,他不給我律師證,我就不是律師?但現在關鍵是,很多律師的工作我沒辦法做。很多情況你不了解。沒有事實,也就沒有辦法發聲」。
2015年709大抓捕、2018年吊證潮後,走在最前、最強硬的維權律師第一梯隊,可以說是幾被剿滅。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維權律師的未來空間難免不讓人悲觀。但年輕律師們正以更為低調的姿態,默默地各自努力着。
「709實際上是蠻影響維權律師發展,線下活動變少,很難有新的律師再加入, 所以增長相對之前是緩慢。大家看到高壓態勢、越來越緊縮的環境,年輕律師不自覺地在考量,或往後再退一步」。相較被「判死」的一線律師,80後的林洲(化名)是幸運的,他是屬於「死去又活來」的年輕一員。
與大多數圈內人一樣,林洲2010年代大學畢業後入行,早期並不關注維權領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人權律師高智晟的紀錄片《超越恐懼》,第一次知道了法輪功群體。同一時期,江西「樂平冤案」震撼全國,案中四名村民被揭遭逼供認罪、當成殺人犯羈押多年,「接觸到感覺特別不可思議」。
他開始思考,現實中的司法,為甚麼會跟自己在書本學的不一樣?解決的根本之道在哪裏?最終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了體制變革,「對中國問題有反思和思考,其實根本上是制度性的變革,如果沒有制度性的變革,維權運動是失敗的,它像永遠會有一個你看得到的天花板。如果體制不進行改變,人權的災難很難得到根本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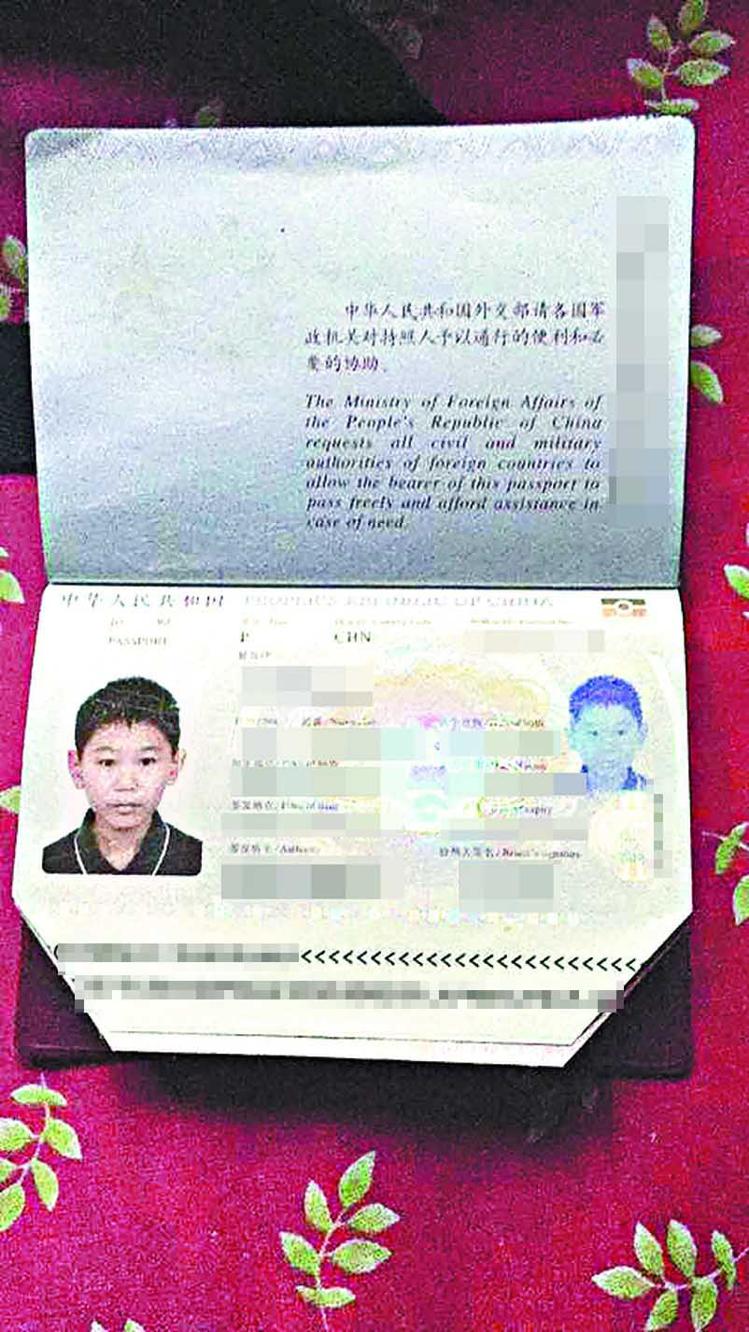
抱着這種信念,林洲走進了維權領域。當2015年709大抓捕來襲,這名「新丁」雖然不至於失去自由、面對監禁,但也遭約談傳喚、禁止出境,還因被律師所趕走,無法執業,導致律師生涯一度中止。經過多番努力與爭取,他直到去年才成功「復活」。
好不容易重操舊業,林洲如今在處理人權案件時,也採取了不一樣的策略,希望盡量延長律師代理案件的生命,避免馬上被官方解除委託。「以前辦理案件,我會寫個小文章或接受採訪(增加曝光),但為了這個事情能夠長久做下去,或為了使律師不被解聘,我可能會讓家屬去受訪,其實傳達的東西是一樣的……在夾縫裏面求一些生存空間」。
若如王宇所說,律師以「殉道」精神投入維權工作,那麼他可以去到多盡?「特別長的(刑期),可能還是會恐懼,十年八年,完全無法想像到會怎樣。但是你如果說兩三年、不超過五年,就會覺得也還好吧」。但他沒有活在恐懼裏,「在大陸,這種心理準備是肯定要有的,哪怕你再小心翼翼」。
「人權工作也是非常艱巨,還是要有堅持、犧牲,特別是在大陸這種狀況下,你要麼選擇不做,但要做的話要想到方法、目標是甚麼,你真正可以做甚麼」。
「但現在覺得說沒有必要犧牲掉,我也會保存一下實力」,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