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今個夏季,內地網劇《隱秘的角落》平地一聲雷:三個小孩捲入一宗命案,與兇手鬥智糾纏,扭曲的愛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兒童的黑暗面徹底被打開,卻又在「有邪念但不至於觸犯法律」、「殺人不見血」等巧妙的編導安排下,打出漂亮的擦邊球,避過了嚴格的影視審查。《隱》點播次數超過10億,在內地知名影視作品評分網站豆瓣獲得8.9分的高度評價,掀起久違的深度劇集風潮,更罕有引起《經濟學人》的注意。
該劇改編自中國推理作家紫金陳的小說《壞小孩》,時代背景為2005年暑假,地點為南方海濱小城。朱朝陽、嚴良、岳普三小孩在景區無意間拍到張東昇的殺人過程,四人從此命運交纏,圍繞着他們的是一連串命案。《隱》是典型的社會派推理劇,導演用上帝視角敍述「人的故事」,排除自己的道德判斷,聚焦在角色複雜的心理變化。引述《隱》的導演辛爽之言:《隱》所有人都是因對愛有錯誤的理解,維繫扭曲的愛,導致泥足深陷。朱朝陽撒盡謊言,張東昇甚至動起殺念,這成了悲劇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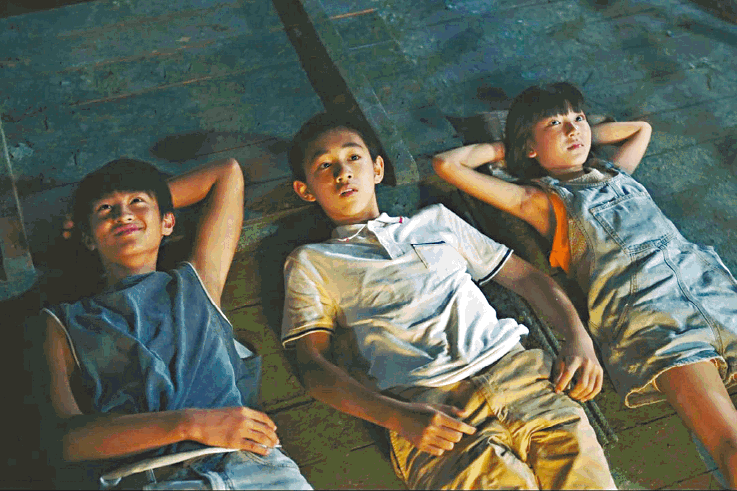

悲劇角色受傳統價值壓垮
「你們有沒有特別害怕失去的東西?有時候為了這些東西,我們會做不願意做的事情。」全劇的主題由張東昇道出,他接受卑微的佔有,承受不了得體的失去。在謙謙君子的外表下是深深的自卑,先後殺害外父外母及出軌的妻子。在角色設定上,張東昇是一個被社會傳統價值壓垮的悲劇角色。相比之下,朱朝陽的性格打從第一集已在劇烈成長。朝陽與東昇,這兩個命名有意的配搭注定了惡的滋生,已為朱朝陽作為張東昇的承繼人而埋下伏筆。《隱》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在於朱朝陽的性格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非典型的懸疑位。
在單親家庭成長的朱朝陽渴望成為已另組家庭的父親眼中的唯一,於是看到同父異母妹妹於眼前墮樓,也未敢坦白,害怕失去所剩無幾的父愛,直至在父親的遺體前才坦承過錯,連番對不起後是一陣撕心裂肺的哭聲。這種坦白與其說是讓朱朝陽找回重新出發的希望,倒不如看成是朱在無道德風險的情況下而坦白過錯。痛哭與坦白也不代表可以一切歸零、從頭來過,這點朱朝陽心裏明白。
在日漸嚴格的影視作品審查制度之下,《隱》能夠順利播出,實有賴於多個擦邊球的安排。一是關於「惡」的處理,張東昇的「惡」有其可憐之處,加上在導演特地安排下,所有兇殺案都由帶有原罪的張所犯,且最後伏法收場;而朱朝陽所滋生的惡念,並沒有直接傷害他人的生命,而只是讓惡念留在朱的內心,為觀眾留下一道開放式問題:「這股惡念會否在朱朝陽長大後發酵,導致另一個悲劇?」二是導演刻意減少兇殺過程的着墨,往往用幾個遠距離鏡頭來輕描淡寫,很少搏鬥與流血,而是將心力集中殺人動機及事後造成的心理影響。這使得《隱》巧妙地回歸主旋律,這相信是此劇成功通過審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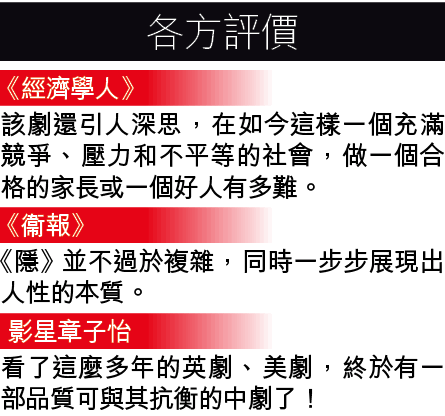
兇殺過程少 重人性抉擇
《隱》將劇中犯案者在面對人性時的抉擇表達得淋漓盡致,演員的演技亦十分精堪,不知不覺就引領觀眾到達故事的終章。豆瓣多數網友認為這部翻拍作品比原著來得細緻,一致贊同《隱》的調整更勝小說。台灣影視評論人柯志遠認為,《隱》的可貴在於成功地將層次更高的人生命題,做為角色和情節的依據,讓觀眾見證心理世界秩序的崩潰,也見證着人性層出不窮卻也避無可避的陰暗。劇中的退休刑警是《隱》的原創角色,導演借用代表着官方權威的刑警來減輕劇集的陰暗色彩,「保留一扇象徵良善與希望的,透光的窗」。《經濟學人》指出:「該劇還引人深思,在如今這樣一個充滿競爭、壓力和不平等的社會,做一個合格的家長或一個好人有多難……在傳統觀念中,一個人只有履行家庭、社會和職業責任才能贏得尊嚴和品德,而這些責任也讓許多普通人身心俱疲,這部劇對這一傳統觀念發起了挑戰。」
反派受觸動 消音留懸疑
人在成長中不斷被迫改變,生命中的各種不堪,藏於心裡隱秘的角落。礙於中國影視創作的「正能量要求」,三個小孩都有好結局。朱朝陽在徹底黑化後,讀到岳普留給自己的一封信:「我還是希望,有一天你能有勇氣的說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才算是重新開始。」朱觸動落淚後,到派出所為妹妹墮亡事件作供。惟這場戲消音處理,只有背景音樂。到底朱朝陽有沒有道出全部真相?他又能否能到救贖,得由觀眾自己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