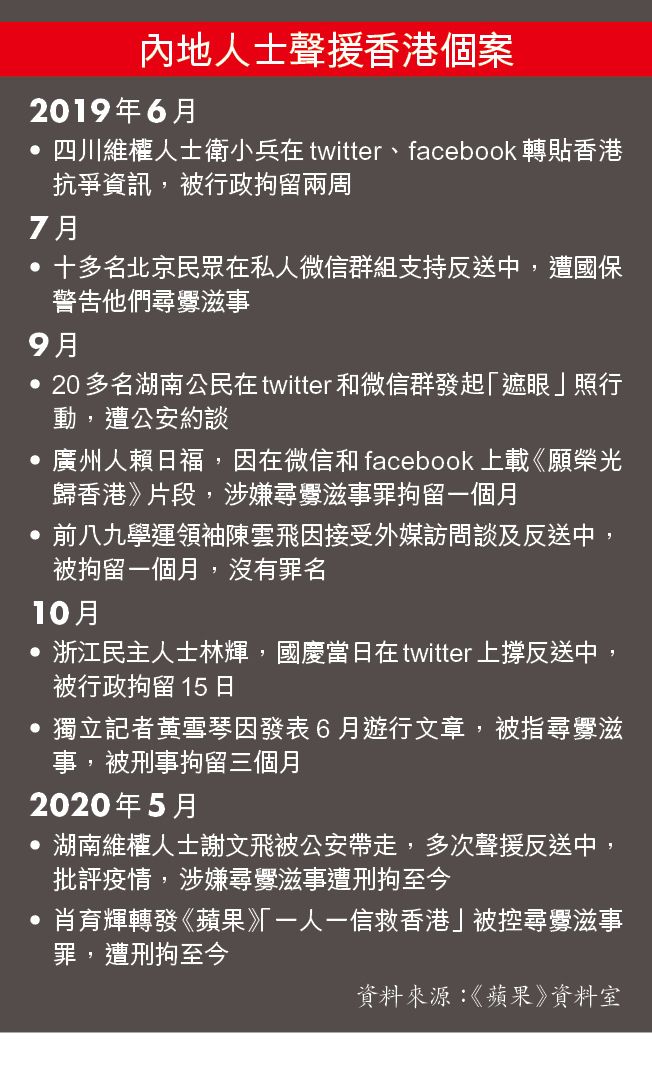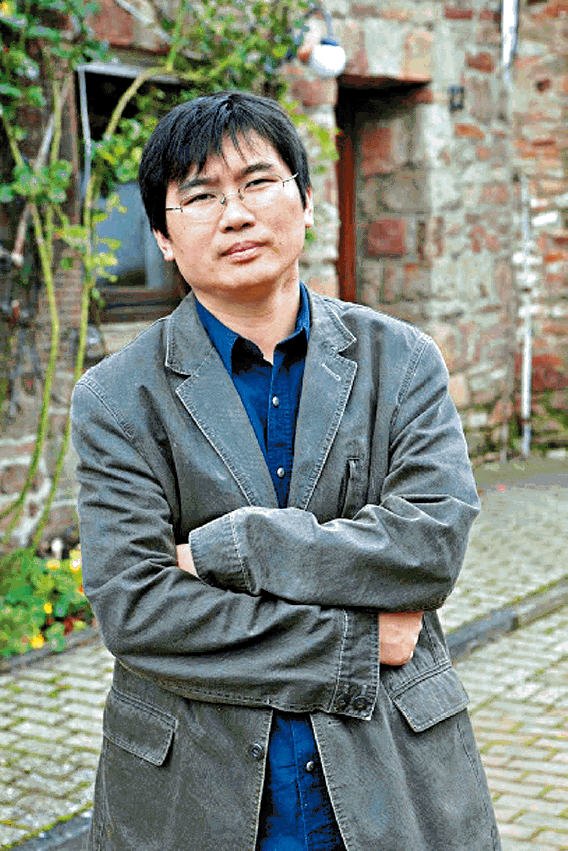
【流亡者系列三之三】
港區國安法來勢洶洶,自由收窄,打壓越見猖獗,中國抗爭者早已領教過,八九民運曾催生一代流亡者,一波波流亡潮,映照中國打壓異見史。
流亡者定義是受迫害、侵略或災害,離開所在國家者。習近平當政七年消滅公民社會,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傅希秋說,武漢肺炎疫潮下,湧現了一股難民潮,僅四個月,已接到200宗求助,是去年全年的兩倍,形容異見人士已經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
尋常百姓淪為政治流亡者,背後原因何在?
一切由公民社會覆亡說起。自由撰稿人兼女權運動參與者趙思樂三年前出版《她們的征途》,記錄中國NGO及社運抗爭者。
她回想起,2003年至2013年胡錦濤當政時,政治流亡過程仍是漸進的,抗爭者先上twitter、參與行動、認識朋友,累積經驗,摸索紅線,打壓和騷擾漸趨嚴重,才思考流亡或判斷留下來,但減少危險行動。
製造新敵人 維穩治國
2013年習近平上台,「他將中國公民社會,清理到幾乎不存在」。同年推動憲政轉型的新公民運動被取締,發起人許志永被捕;2014年最重要之一民間智庫全知行被取締;2015年推出《國家安全法》,發生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到以「益仁平」為首的維權公益組織被取締,然後是勞工運動和教會。同時尋釁滋事罪擴大至網絡上組織、指使人員散佈訊息等,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令公民網絡空間大收縮。
2014年,國際特赦組織統計,中國約100位抗爭者因聲援傘運,以尋釁滋事罪被刑拘、扣押或軟禁,包括「全知行」創辦人郭玉閃,以及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寇延丁,震盪公民社會。趙思樂比喻為拘捕吳靄儀和李柱銘,「(維穩)大型機器才剛剛發動」。當中十人被判刑,最長是在廣州街頭拉橫額的謝文飛,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四年半。
2019年,因反送中遭打壓的中國維權人士,約十宗,網絡聲援被刑拘、微信私人群組討論也被約談,精確數字無從得知。趙指,維穩機器有精力後,「現在好容易針對一些偶然發現的普通人……一來就好嚴重,因為沒其他阻力擋在面前。」
政權不斷尋找抗爭者,製造新敵人,維穩治國。寇延丁在《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曾提到,審訊者欲證明佔中是港獨,由外國勢力策動,與中國公民社會勾結,顛覆國家。趙思樂說,被捕者無名無姓,等同香港勇武被抓,「揑死你同曱甴差不多,不需要作古仔」。
周政因呼喊一句香港獨立,遭刑拘和在家監禁。趙思樂指公民社會瓦解,散播抗爭訊息少,抗爭和打壓經驗的資訊遭審查後,失去傳承而斷層。普通人在網絡社群被原子化,一旦明確表示政治立場,發貼、討論也被針對打壓。
流亡德國十年的中國異見時事評論家長平說,中國政治迫害的門檻一直很低,法治社會明文規定界線與懲罰,專制國家的法律模糊,易政治化,令犯禁後果難料,製造恐懼不斷維穩,「不安定因素正是統治手法,不確定就自我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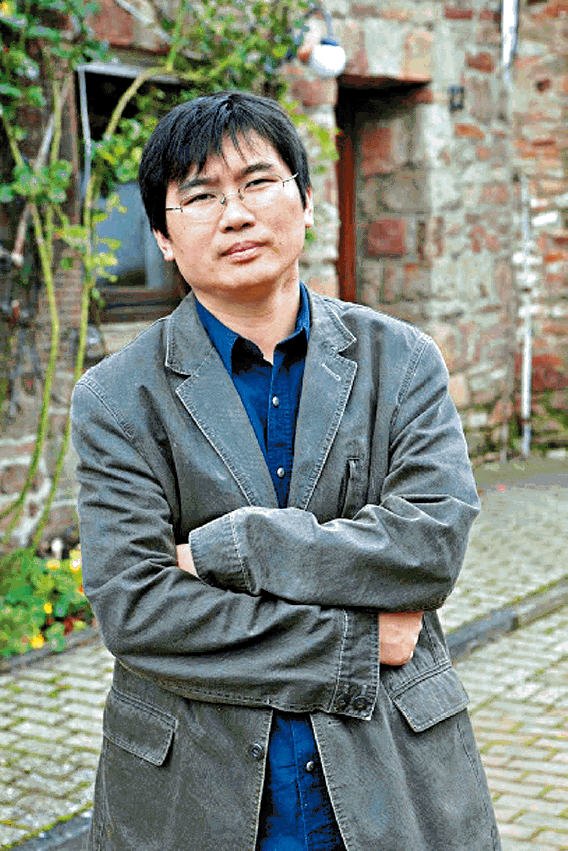
難民急升 支援機構資源耗盡
長平說,上街抗爭比上網發聲更嚴重,有組織行動比單一行動更嚴重,少數民族、宗教、人權、邊境等議題一直高度敏感,龐大的「維穩機器」到了敏感時期,只需要把某方面加強,就可以高速運轉。趙思樂說:「以前在無可忍受的打壓同正常生活之間,有好大灰色空間;但現在一碰就好大打壓,發展都成問題。」
但支持中國流亡者的機構寥寥可數。2002年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成立,支援內地地下教會,因多次營救維權人士獲國際注目,在歐美為內地人權狀況作證。創始人兼牧師傅希秋表示,「中共對自由人權的打壓到了前所未有惡化的情況」。加上近年對宗教及人權迫害、法治的踐踏,以及新疆鎮壓,許多人到了無法生存的狀態,因此出現一定規模的難民潮。傅希秋透露,每年有5,000多受助人,九成受宗教迫害,一成維權人士,各半位於歐美加和亞洲,但未有透露中國境內人數。
受助人分三類,一是留在中國境內的基層維權人士和家屬,無法在打壓之下生存,無法離國,還有境內流亡者;二是滯留他國,拿到聯合國難民身份,但未被第三國收容,仍受到中國威脅的人士;三是逃到西方國家,不熟悉環境,具備申請難民的資格,卻遇到障礙。
對中國異見者而言,「流亡不是一個選擇,是一種特權」。趙思樂接觸過數百名抗爭者,少於十人能流亡,而中國基層抗爭者常在打壓下,有刑事紀錄,難往海外申請政治庇護,外國政府介入需許多條件。
對華援助協會去年共收到100宗新增求助案,今年截至4月已有200多宗,以維權人士為主。傅希秋透露,連來港抗爭的中國留學生Alex在內,一個月內已營救了三宗個案到美國,壓力前所未見,營運完全依靠捐款,每年預算約200萬美元,「資源幾乎枯竭」。
近年逃亡難度大增,除了監控和定位電話、移動支付和實名交通登記,公安更推行全方位動態防控體系,靠監控鏡頭辨認臉部特徵,追捕疑犯。
傅希秋指出多條偷渡路線被堵,多次有偽裝公安跟蹤逃亡者至邊境口岸再抓捕。重要級別的異見人士於5至15分鐘內警方到場抓捕,低級別的則以電話通知當地執法者。成功出逃者仍許多,「不是每個角落可以時刻24小時(監控)」。
隨中國政經勢力漸強,國際談判力量大減,難以營救異議者。周邊國家如泰國和緬甸頻頻與中方合作,跨境追捕異見人士,即使聯合國難民公署已安排第三國收容,亦有可能遭遣返,如姜野飛和董廣平。
有一次,傅希秋格外痛心,一名新疆哈薩克女性進入新疆集中營之前逃到烏茲別克斯坦,但中國派人到當地機場等待她,協會牽線下,因美國國務院施壓而未有遣返,安排她經泰國轉機至土耳其,孰料在曼谷機場失蹤,「很明顯地被中共綁架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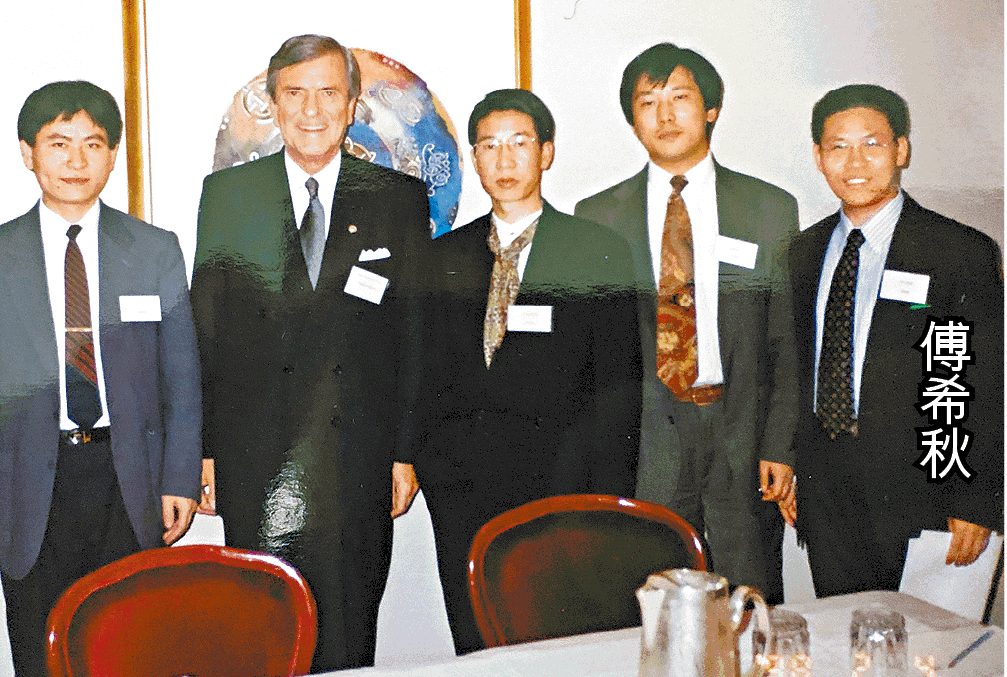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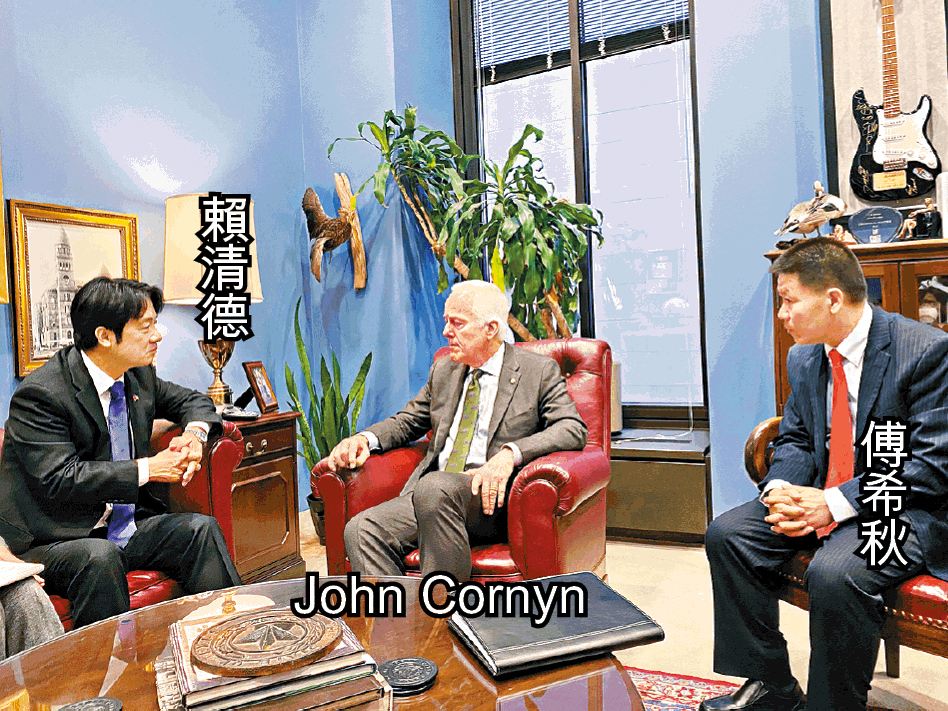
反抗專制政權 催生更多流亡者
傅希秋觀察,許多中國流亡者在泰國滯留多年,符合難民資格多,批准往第三國收容數字較少,質疑聯合國難民公署受中國影響。他指,流亡者無收入無簽證,害怕泰警及中共特工抓捕,彼此互不信任,家人受要脅斷絕來往,有些更無奈回國。
長平說,中共視曝光人權打壓為污點,常以家人要脅,要求低調解決事件,尤其不可受外媒採訪。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林榮基至少還有發聲的自由,而李波的自由代價就是永遠沉默」。長平續道:「只要存在專制政權,一定有人反抗,反抗就必然流亡。」
九七前香港是流亡中轉站,九七後港府配合中國打壓異見人士,令長平在2011年流亡。他經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在浸大任訪問學者,創立時政雜誌《陽光時務》後,國內家人受壓,申請工作簽證被拒。當時他在法國,入境處來電叫他回中國辦簽證,他詢問:「能不能保證我回香港?」職員答道:「調查組跟邊境組是兩個小組,不干預他們工作。」
趙思樂預計香港抗爭者面對國安法,將包括被國安調查、監察、拘捕審訊,而條文所提到的國安機構,可由國家安全局擴大至所有機構,外國勢力如外媒、國際NGO、領事館均會消失,「但惡化(速度)可能比中國還快」。關鍵是人大常委會多快制訂法律,條例有多具體,以及政府配合程度,「如果常委會年內制訂要一個香港版的網絡安全法,港府和香港法院能配合約束本地的網絡服務嗎?」
中國抗爭者已失去戰場,只能奮力留住記憶,趙思樂說:「在中國堅持的人,更似是維持生命的尊嚴同意義。」中國抗爭者多數缺乏流亡的經濟、語言基礎,加上資歷清零,生計也成問題,甚至有前大學教授做清潔工,但最嚴重是精神痛苦。
「戰士失去戰場會處於更加原子化狀態,身邊沒人知道,沒人care你所care的,是一個好失去價值的狀態。一個對社會有感情、對某些價值有追求的人而言,流亡是要用盡自己願意付出的所有代價,之後再去考慮的事。」她說,香港尚有奮鬥空間,抗爭者需思索並選擇付出的底線,「香港仲有得用盡最後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