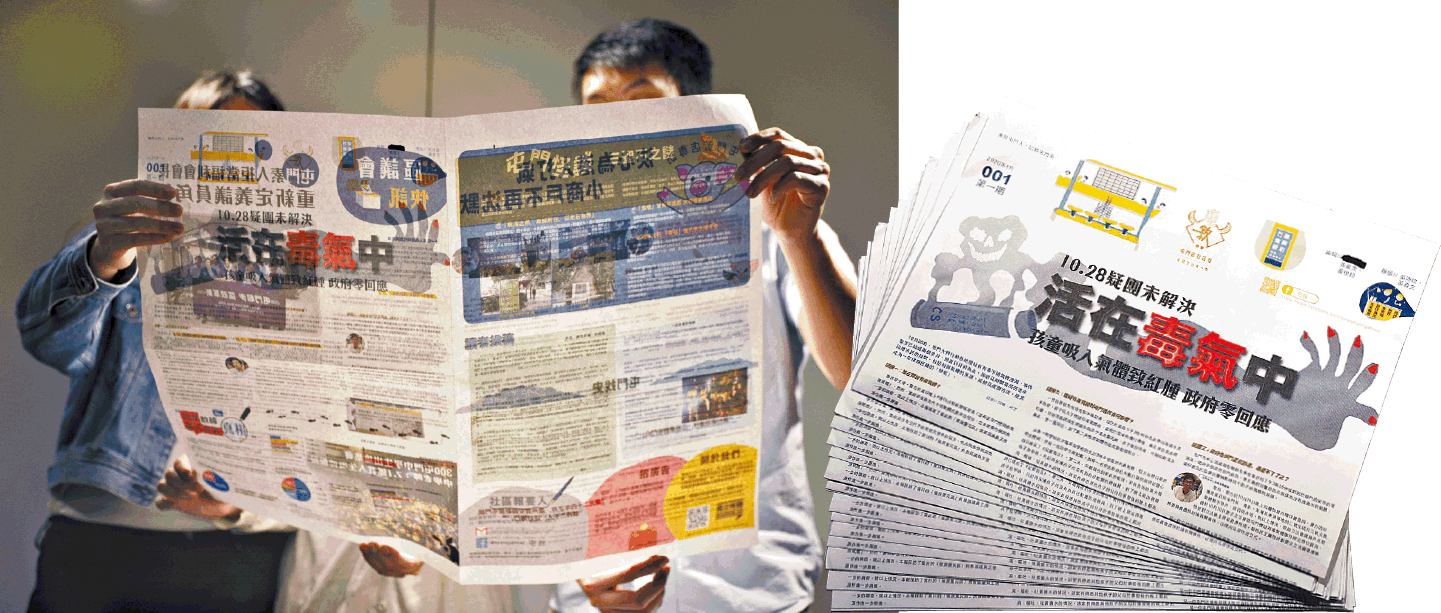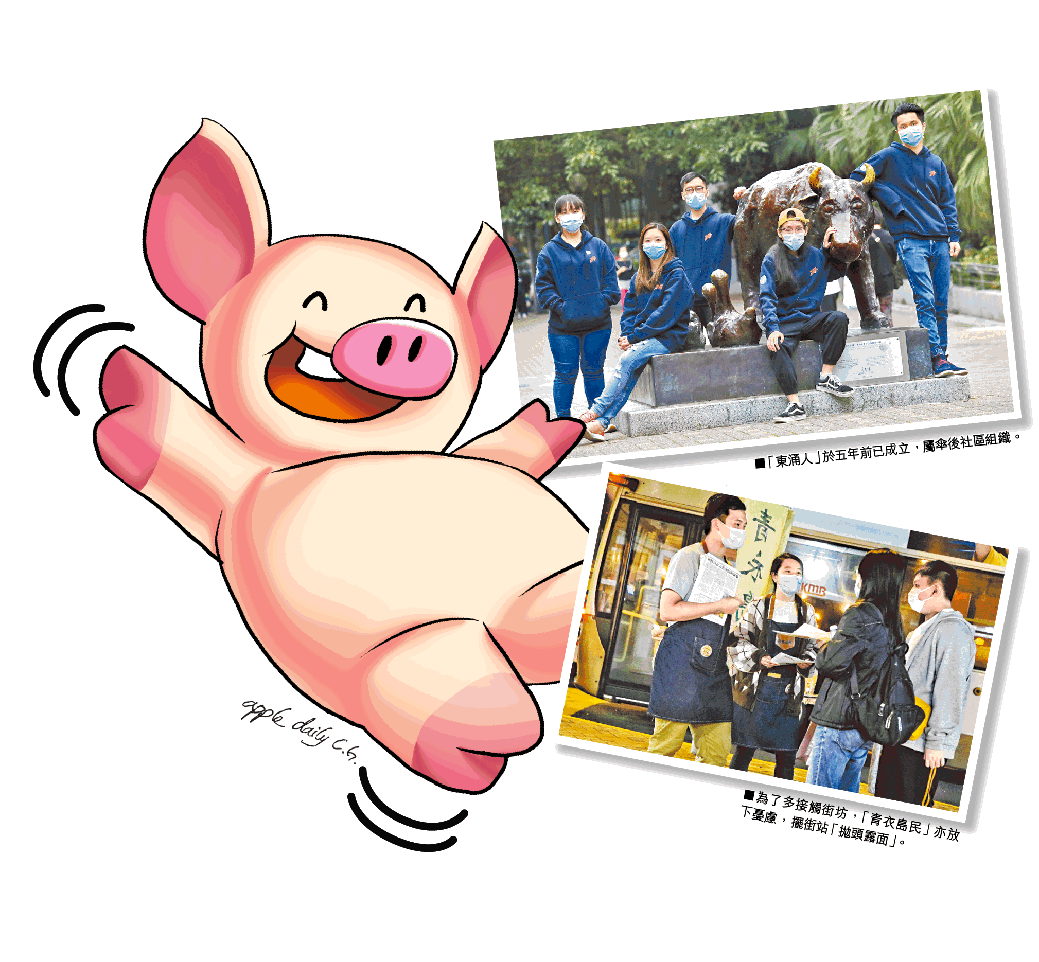
反送中運動之初,各區街坊紛紛自設連儂牆,一年下來,大多已被摧毀,然而連儂牆帶來的影響沒有就此消失。它們奠定了社運在社區開花的基礎,多個社區湧現了因反送中運動而成立的街坊組織,也有街坊主動籌辦地區報,同時,也有義工新血加入既有的社區組織。他們期望通過深耕細作的社區服務,消除黃藍之間的隔閡,為街坊提供更多社區資訊,團結街坊。
撰文:趙曉彤
攝影:黃耀興 梁志永 許頌明 張志華 何家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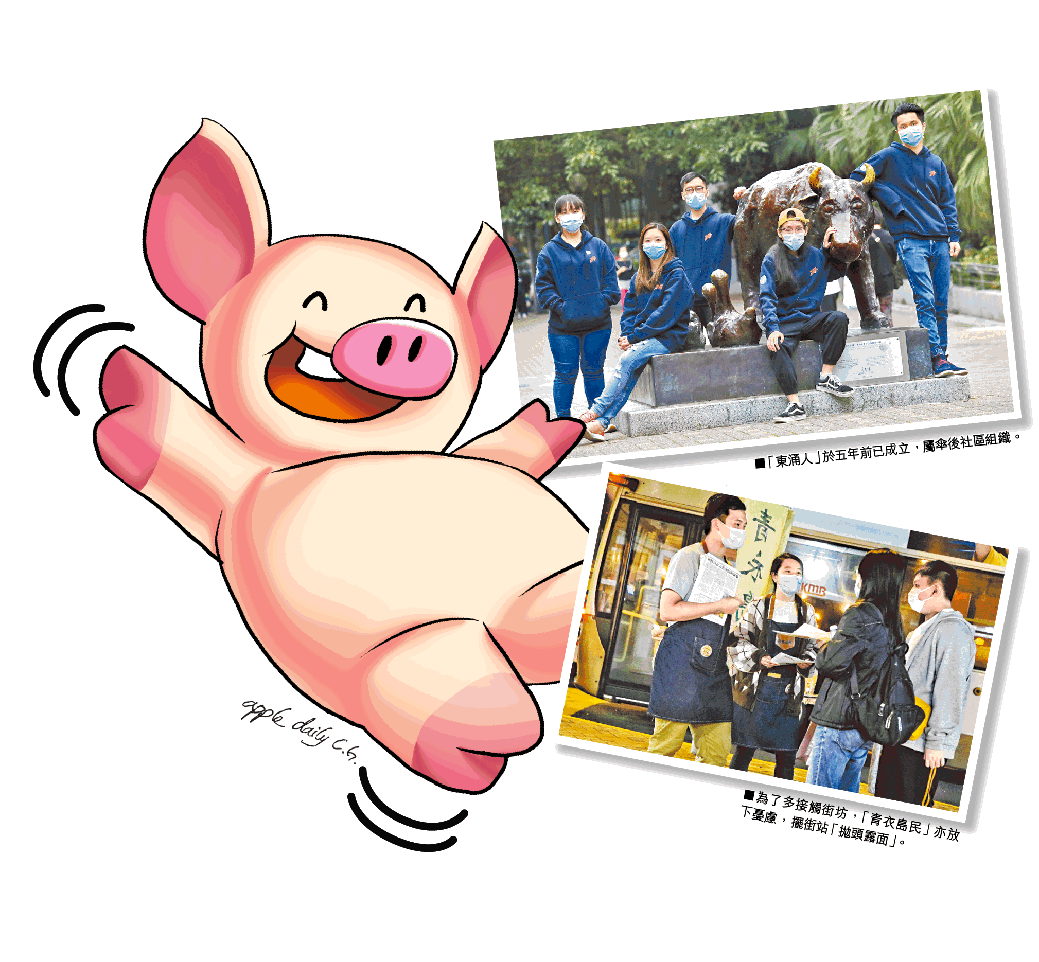
第一階段:為反送中出發
初夏的晚上,青衣的街坊組織「青衣島民」成員Eric與數名義工,於青衣街坊稱為「山上」地區的長亨邨開街站,派區報和做選民登記。Eric由組織成立開始,做了三年義工,笑言自己有份正職,就算有人出50元一小時給他站在街上派報,他也沒空,只是為了共同理念,他和其他街坊才會做義工「拋頭露面」。
「如果我行唔到去好前線嘅,咁會唔會喺我屋企前面,就係我嘅前線呢?我可以去做多啲呢?」這是Eric的想法。在自己所住的社區倡議民主規劃、公民覺醒等概念,Eric不無憂慮,因為社區就是一個人人都認得自己、都知自己住哪裏、甚至認得自己家人的地方,然而,在反送中的政治低氣壓裏,他卻更感受到社區參與只能二選一:要不就站在很前線,要不就用自己的身份實名為社區做事。
以市民身份走入社群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Eric仍是大學生,當時他已反覆自問,為公民抗命可承受多大法律風險?他實在恐懼於「一畢業就坐監」,心裏一份虧欠感,推動了他參與社區事務。一做三年,青衣島民facebook現有近30,000讚好,在20萬人口的青衣社區,青衣島民算是一個已扎根的社區組織,於是,去年6月初反送中遊行,他們最初會組織街坊一起遊行,希望有個照應,也消除街坊參與社運的孤獨感。然而,這場運動的文化是「去大台」,他們開始擔心自己不自覺做了「指揮」角色,於是非常低調地行事,也不再組織街坊一起遊行。
青衣的街坊不再用「青衣街坊」而是「香港市民」身份來到社運現場,但當他們回到社區裏,可以不用一下子回到像平行時空一樣、太平盛世似的社區嗎?Eric想,如果街坊回家時,會看見島民仍在社區裏擺街站,可能是呼籲街坊登記做選民,可能是關心社區議員,這未嘗不是一種打氣方法,令街坊明白「關心社會」並不孤單。
另一街坊組織「東涌人」同樣早於反送中運動成立,他們是五年前成立的傘後社區組織,現任主席鋼牙是創始成員之一。五年前,鋼牙仍是中學生,很希望大家關心社區,卻好像很少人理會他們。去年7月,他們擺街站招募新義工,意外獲得熱烈迴響,幾個現任幹事從前留意了「東涌人」幾年,可是沒有行動,但現在面對無能政府,終於決定落手落腳關心社區,這轉變令鋼牙非常感動。
將抗爭融入生活
東涌人的幾個年輕幹事,皆視「街坊組織」為另一種社會運動的手段,認為日常生活裏,街坊也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制度,所以他們關心反送中、區內武漢肺炎確診者,也同時關心路邊發現的蜜蜂巢、垃圾房發現的幼貓、社區車仔麵小店等,希望街坊通過明白生活就在大大小小的制度裏,因親身為社區事發聲而令生活變得更美好,更明白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前陣子,他們籌辦了一個「義剪」活動,服務街坊時,他們不會問街坊是黃是藍,但街坊有時會問他們的政治立場,成員黑人總會回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更多時候,黑人是在調節心理狀態,因為面對政見不同的街坊,她最初也有過不了心理關口的時刻,但她會記住自己希望連結東涌街坊的初衷,「唔應該爆咗感受出嚟先,你同一個街坊嘈,可能背後無咗廿幾三十個街坊,佢有自己朋友圈。」
黑人仍是大學生,反送中運動令她反思「你要幫到香港,首先要救我哋屋企」,因此全情投入參與社區組織,甚至連大學的畢業專題功課,也以「東涌人」為題材。為了增加東涌人facebook專頁的吸引力和親和力,她甚至經常拍攝影片介紹社區,而她常常是影片的主持人。同樣面對在社區「拋頭露臉」的安全憂慮,但黑人認為不應該因為害怕而不做正確的事。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新的社區組織湧現,例如「牛頭角大細路」和「長洲同行」。前者創立時,只有A小姐和Chaya兩個成員,Chaya說:「人數不是我們的限制。」後來因為派口罩活動而招募了十數個義工,其中兩個在派口罩後留下來,成為核心成員。四個「大細路」成員都是大學生,取名「大細路」,是因為很多大人眼中,他們仍是細路的年紀,但他們其實已成年,逐漸變成大人了。
A小姐在牛頭角土生土長,因反送中運動而很想為社區做些事,身邊卻沒有志同道合又有熱誠的人,去年11月,她的社區沒有在區選「光復」,令她頗感挫敗,想着如果自己早點行動,結果可能會不一樣?此時,她久未聯絡的中學同學Chaya突然聯絡她,說想為牛頭角做一些事,特別是看見區選民主派只輸很少票數,覺得這區有得救。本來,兩人想了不少大計,但在辦了一場電影放映會後,其他活動都因疫潮而擱置,她們改為派口罩,當公公婆婆因取不到口罩而責備她們時,她們要令對方明白造成今日局面的是政府,而不是不夠物資派的「牛頭角大細路」。
長洲變天 同路人歸位
「長洲同行」的成員因為反送中運動而慢慢認出了島上的「同路人」,在此之前,他們只覺得長洲有一種不談政治的冷漠感,隔了一個海,就是平行時空,這令他們非常壓抑。成員Tony一直以來關心政治,但對長洲死心,甚至有成員從前放棄登記做選民,因為不信長洲會變。
成員阿康表示,他在傘運後開始關心社會,反送中是他第一次參與遊行,長年在長洲生活,「即使我自己後生,都係對政治無咩觸覺,何況係長洲嗰啲阿婆、阿伯、阿叔?」然而一場反送中運動,他們先是目擊一船船的白衣人一起出港島,再來是一船船的黑衣人,令阿康忽然清醒,長洲變黃原來不是完全無可能。及後,部份成員一起於區選助選,長洲最終光復成為黃島,他們大為鼓舞,決定成為「長洲同行」,說是要「為反送中出發」而為社區服務。
小島生活猶如困獸鬥,拋頭露臉在街宣揚民主,很快就會所有島民都知自己是誰,住在哪裏。成員表示,這正是從前不站出來的憂慮,現在是豁了出去。也有成員並不擔憂,表示即使是深藍與深黃的街坊,「我同你識咗40年,你打我?唔係嘛?」
青衣島民成員王必敏表示:「我哋一跳就跳到去好遠,硬係喺自己屋企附近就無咩人care,一跳就跳到去立法會啊、金鐘啊,以前2014年就係咁。」她希望大家可從社區開始關心社會,這是她3年前成立島民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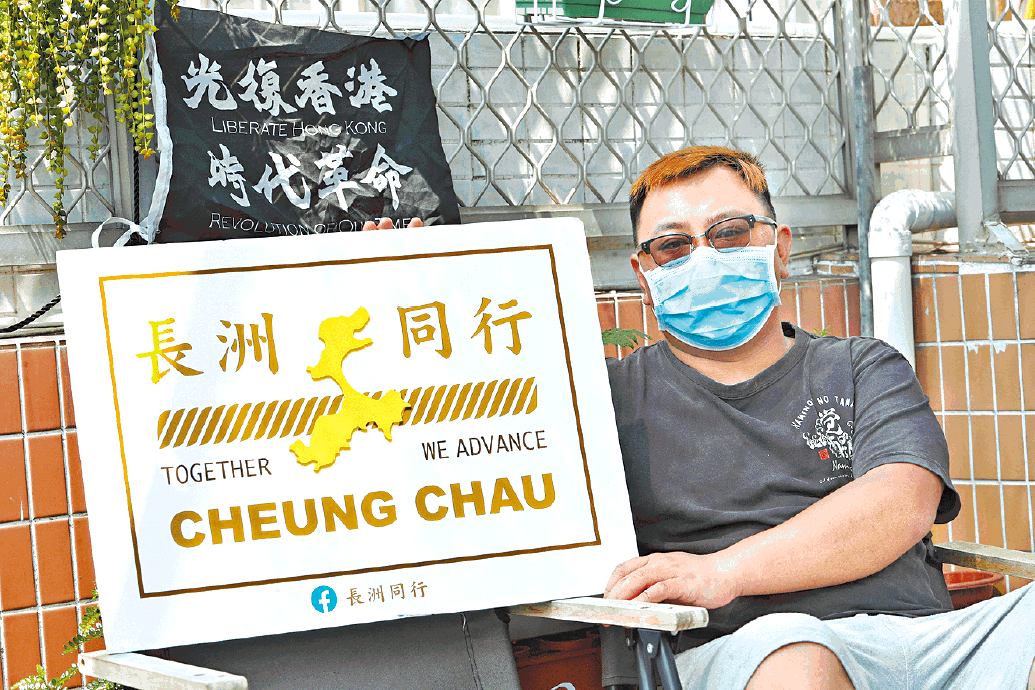
第二階段:光復區議會
去年11月的區選,是社區組織的大事。「牛頭角大細路」創始人因為區選落敗而成立,而「長洲同行」的不少成員因助選而第一次合作,因長洲「光復」而大受鼓舞,成員阿康說:「我哋呢個島真係可以行出民主第一步,證明喺長洲都係好多同路人。」
當日民主派梁國豪以5,142票擊敗3,229票的民建聯郭慧文,阿康回想,仍非常興奮:「估唔到贏票贏得咁犀利。」原來支持民主的長洲居民只是較少發聲、較少站出來,不是阿康等人從前認為的「長洲無得救」,這事令成員更堅定地以「服務社區」作為參與社運方式的決心,阿康說:「當𠵱家有希望時,如果你連呢一步都唔行出嚟,將來係點,無得怪。」
今年長洲區議會由兩席變一席,而梁國豪是素人區議員,這也是助選義工以街坊組織繼續服務社區的原因之一,「一席睇晒長洲民生係好辛苦,如果有人分擔佢嘅嘢,大家一齊輕鬆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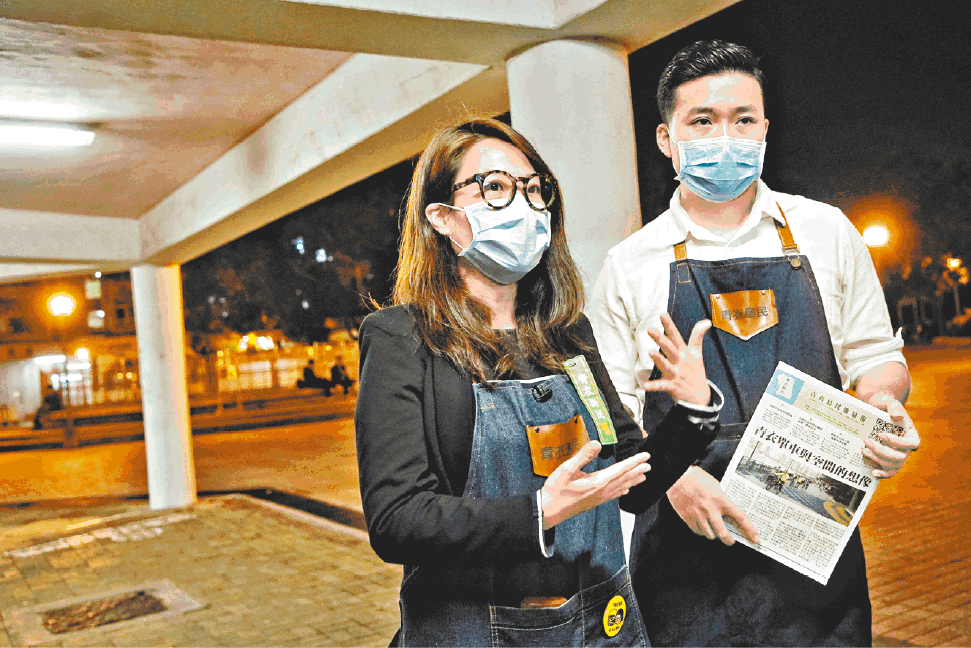
新成員注入衝勁
青衣島民的最大轉變,是組織召集人王必敏當選為青衣邨的區議員。早在去年年初,他們已決定參與,當時也不知道會有反送中運動,只是他們認為青衣島民用了三年時間不斷倡議社區要有甚麼改變,實在太像遊走在雲端的「鍵盤打手」,即使後來他們也不斷在社區籌辦活動,感覺也像是站在一旁不斷去踢體制裏的人去工作,「講到幾鍾意自己嘅地方,有機會係咪要落多啲水呢?」她認為不論輸贏,「青衣島民係必然要落呢個水嘅。」
王必敏希望通過參選,一方面是測試街坊對青衣島民這個組織有多大認同,所以她一直認為她只是代表青衣島民出選,街坊是投青衣島民而不是她本人一票,同時,她認為這是街坊組織的重要一步,參與區選是推動一個社區組織繼續努力的目標。當大家變成助選義工,會更明白自己為甚麼要付出這三年的努力,為何要做這些地區工作。島民的成員各有正職,這三年來,不時經歷大家都做到「有啲謝」,但當大家又有共同目標時,且因此吸納更多志同道合的新義工時,成員就會在周而復始的「謝」與「衝刺」之間,繼續走下去。
自製刊物分享不同聲音
「馬鞍山守護線」共有五名成員,其中四人於區選分別當選為馬鞍山市中心、利安、鞍泰及錦濤選區的區議員。許立燊是該組織的成員之一,同時是現任錦濤區議員,他表示,即使大部份成員都有公職在身,仍會把這個組織定位為街坊組織,「我哋唔係一個政黨,亦唔覺我一定要係一個政黨先做到一啲社區嘢。」
許立燊回想最初成立「馬鞍山守護線」,是因為反送中運動令他很想團結當區街坊,也想以組織名義為街坊做一些事,因為他過往服務社區的經驗,令他明白「孤掌難鳴」,最初鄭仲恒未加入,而他們四個最初的成員全是沙田、馬鞍山的街坊。及後計劃有變,大部份成員當選區議員,他們認為「區議員」身份於服務街坊時有好有壞,辦事必須小心為上,在效率上很難與其他街坊組織相比。不過,他們也可以為其他馬鞍山的街坊組織提供一些便利,訪問當日,他們主動向記者提及同區的街坊組織「馬鞍山社區前線」及社區報《馬聞》,而在鍾禮謙與許立燊的聯合議員辦事處,也擺放了該區中學生自發籌辦的社區刊物《沙燕》,許立燊認為中學生可以做到這個水平的刊物已很了不起,從事廣告業的鄭仲恒一看排版就知道這是一本業餘刊物,但業餘也有好處,因為知道這不是主流媒體的聲音。「其實無論咩活動都好,邊一個組織去做都唔重要,最主要係可以做到件事係幫到社區。」鄭仲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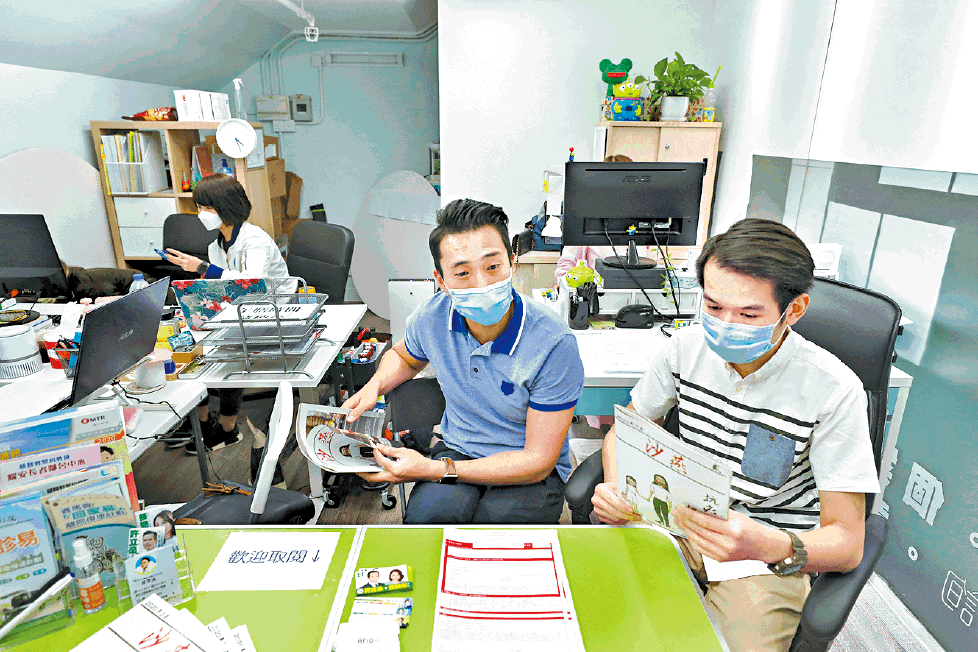
第三階段:製作社區報
訪問青衣島民那夜,他們正在派發社區報,報刊的封面故事關於青衣單車的社區規劃,成員山崎派報時,一個中年女士本來匆匆走過,瞥見報紙和單車有關,又停了下來問:「青衣有單車徑嗎?」「未有,但好多居民想要,我哋倡議緊搞單車徑嘅可能。」女士也是青衣街坊,從未聽說青衣島民,山崎便留下了島民facebook專頁作聯絡方法,鼓勵對方說說對「單車徑」的想法。
這是青衣島民兩年來的第四份社區報,今期出版2,000份,分三日在青衣不同地點派發。兩年前決定做實體報,是因為發現facebook不斷報道青衣的生態、歷史、社區規劃等內容,但即使有接近30,000人讚好專頁,仍有不少青衣街坊無法接觸這些資訊,如區內的老人家與小朋友。在擺街站時,他們會發現不少街坊仍未知道青衣島民,他們視面對面的接觸為認識街坊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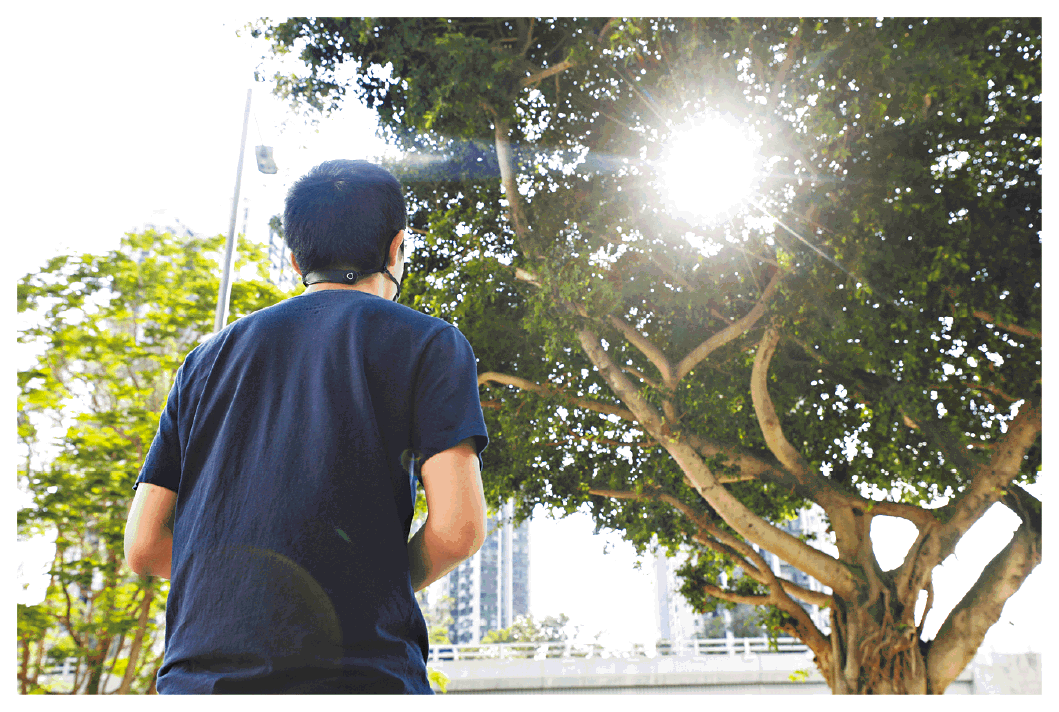
雜誌獲認同 贏街坊捐助支持
今年,沙田區也有一份社區刊物《沙燕》,共八個街坊參與,成年人街坊主要負責「給意見」,主筆和插畫都由中學生包辦。他們剛出版第二期《沙燕》,5,000本雜誌,由兩個中學生走遍區內的黃店與議員辦事處,商議可否放在店內供人取閱。他們不在街上派雜誌,因為「實畀廢老鬧」。
高中學生「光頭劉sir」是這本雜誌的創辦人和總編輯,最初創刊,是希望沙田居民記得這場運動,他特別希望在疫情期間為這場運動保溫。刊物有社區議題、沙田社運大事回顧、黃店介紹等欄目,而幾個中學生視這本刊物為反送中的文宣,是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之一。光頭劉sir憶述自己從前在天剛亮、上學前的時間,在區內貼文宣,午飯已發現被人撕光,無心機再貼,不如做雜誌,成員阿寶表示:「文宣從來都是很有用的。」
三個受訪中學生,相識於9月的區內聯校反送中運動,其中阿寶與光頭劉sir自6月開始全程投入反送中,Tiffany則是接近去年開學才留意這場運動,自覺很遲參與,有虧空感,就來《沙燕》做「打雜」。他們認為中學生在這場運動「談唔上中流砥柱,但都會佔一席位。」刊物出版後,他們主動來到沙田區的不同議員辦事處尋求幫助,其中包括「馬鞍山守護線」成員許立燊與鍾禮謙的聯合辦事處。他們答應把雜誌放在辦事處供街坊取閱,希望街坊可接觸不同資訊。區內另有區議員協助他們解決財政問題,在辦事處放一個非常細小的課金箱,幾天時間,籌了千多元,光頭劉sir興奮地說:「沙田人就係錢多!」
最初創刊只是個人興趣,現在卻有街坊課金和區議員幫助,光頭劉sir本來仍覺得「沒有壓力,快樂人生」,但在訪問當日,《沙燕》卻出現在《文匯報》頭版,新聞標題是「疑公帑出版宣暴.涉犯公職失當罪」,對此,他們一邊說是「黨的嘉許」、「與有榮焉」、「人生成就解鎖」,一邊又有點傷心於人生第一次上頭版是《文匯報》,且第一次憂慮成員的安全。從前是父母擔心他們的安全,阿寶總對父親說:「驚咩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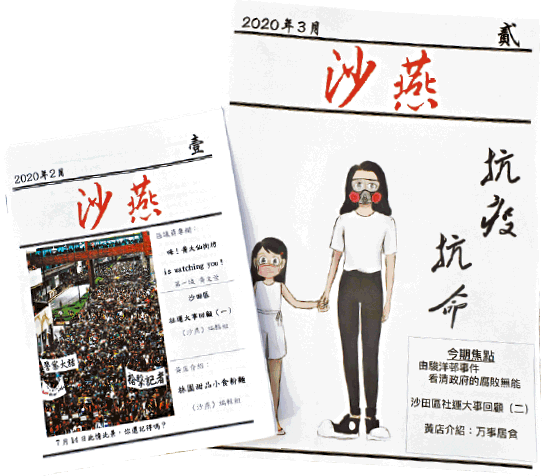
信變通能帶來希望
光頭劉sir形容自己是「被時代選中嘅細路」,阿寶立時搶白:「我哋幾慘,上學期打林鄭,下學期打肺炎。」雖然他們努力反抗,希望爭取屬於自己的將來,卻同時認定:「一國兩制完喇,中英聯合聲明完喇,50年不變完喇。」也認定留在香港沒有將來,「𠵱家都搞到咁喇」。
咁無希望,為何仍辦《沙燕》?「無希望咪創造希望,唔係有希望先堅持,係堅持咗先有希望。」光頭劉sir表示,即使聽過一些說法是香港的命運要交上天決定,但他覺得人定勝天,香港命運不應由上天決定,「制度裏抗爭唔得嘅,可以試下勇敢啲,勇武唔得再試,再諗辦法,香港人最識變通」。
反送中運動也促使了屯門街坊創辦社區報《屯敘》,「敘」取「記敘」的意思及「凝聚」的諧音,成員希望通過報道社區議題及撰寫屯門歷史的文章等,增強屯門人對社區的歸屬感。
成員阿聰於運動期間思考自己於社區的角色:「一個人除咗喺學校、工作地方、家庭之外,喺社區位置都好緊要,社區嘅出現其實係保障緊每個人嘅權益。」同時,他希望通過社區報消除外界對當區的誤解:「屯門係咪真係有牛?係咪真係有動物喺度行?呢個澄清番,屯門一早已經發展。」另一成員阿丁則表示,他的朋友大多住在其他地區,運動初期,他在屯門區沒有理念相同的人,卻因為主動報名參與社區報,認識了理念相同的街坊,就想一起為屯門「做返少少嘢」。
為社區報出外採訪時,有人跟阿聰說:「如果停留喺一係出去,出去就危險,一係就唔出,唔出就內疚,你無第三種方法呢,你就喺困局裏面。」而參與社區報,親身在社區派發自己撰寫的報紙,正是阿聰的「第三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