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修士Thomas Merton說,你越怕受苦就會越痛苦:「The more you try to avoid suffering, the more you suffer, because smaller and more insignificant things begin to torture you, in proportion to your fear of being hurt.」肇峰幾次自殺不成,去年投入時代革命,跟上述說法其理共通,不怕死的人似乎總是不死。
他與警察幾度交手陷入絕境都化險為夷,別說被殺,莫講捱打,制服在地也沒一次。我們知道這理論很危險,尤其運動似已過了瓶頸。有言在先,頭盔放在前面,以下故事純屬受訪者一人經歷,別人命運未必相同。撰文:陳勝藍
攝影:許頌明、何家達
世間竟有肇峰這等奇人,住所狹小不設廚房,祭壇倒有一個,供奉反送中死者梁凌杰、陳彥霖、周梓樂,據說梓樂愛龜,壇上木龜守護。別人死在政權手上,他錐心泣血,每月15號翻看自己為凌杰剪的片;為了梓樂,臂上多了個紋身;自身性命反而不放在心上。


以肉身之痛 解失敗之苦
荃灣街坊稱呼他Ricky,行年三十八,不怕死的故事要從20年前說起,18歲便在銅鑼灣開酒吧,拒交保護費,他說:「成條駱克道都要畀,但我從來冇畀過,有(陀地)上過嚟問我攞,我話我唔會畀。」陀地上來喝酒,打了客人一巴掌,又不埋單,吹雞找所屬社團大佬撐腰。肇峰也不是省油的燈,找那大佬的妻子,結果兩夫妻同來講數,卻代表不同當事人,最後社團大嫂命令陀地埋單。
本文主角憶述:「我一個死𡃁仔,18、9歲,可以拍枱指住話事人X,我講道理,話之你係蠱惑仔大哥定係某間差館話事人。」全盛時期擁有三間酒吧,以及別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我18歲開第一間酒吧,做咗十幾年,我每日起身返公司飲酒,飲完酒打牌、跳舞,咁樣過咗十幾年。」好景不常,之後被騙,失去整盤生意,「嗰陣我點過生活?吸毒、飲酒、一樽一樽安眠藥係咁啪。」
貓有九命,肇峰可能不止,當時醫生問:「食咗幾多粒安眠藥?」他答:「個樽有幾多粒就食咗幾多粒。」醫生驚叫:「你食咗一百粒安眠藥?」除了畏高沒跳樓,他用盡所有方法自殺,「我試過燒炭、鎅手、飲到胃出血,嘔到一屋係血。」兒時曠課逃避打針,可知他多麼怕痛,生意失敗心中苦痛不能解,卻用紋身大挪移,下針時大叫大哭,以皮肉之苦排遣心痛。本文無意對紋身或褒或貶,這是他的道,下針當晚睡得特別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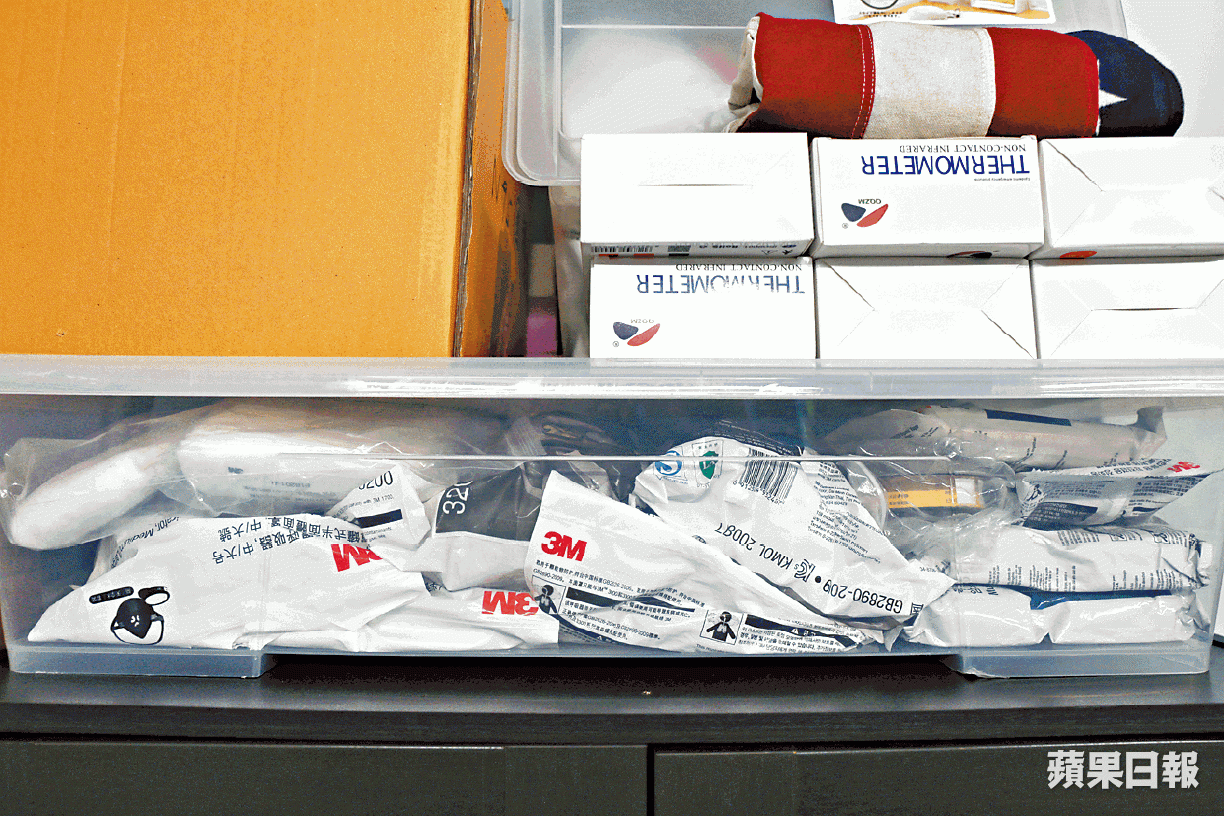
條路自己揀 出事唔會怨
死不去就要戒毒,右腕多了個梵文圖案,每當拿起毒品,看見這刺青便放下。自言傘運時期仍是花生友,去年6月15號梁凌杰命喪金鐘,從此不一樣,「我絕對唔係因為當日大家所講嘅《逃犯條例》走出嚟,我係因為Marco(梁)過身走出嚟,我係因為警暴仍然存在,所以我仍然堅持。我唔識政治,太繁複嘅嘢我處理唔到,但我承諾過我會行落去。」
抗爭運動改變了這個人,不再想死,沒再喝酒,只是繼續紋身,半邊狼面圖案為梓樂而設,「我唔知可以用乜嘢途徑釋放我嘅負能量!」半邊面也代表爆眼女義士。他就在那時展開刀口上舔血的日子,去年10月荃灣眾安街防暴推進,衝過來盤問:「你係咪記者?你係乜嘢人?」肇峰答:「街坊!」「街坊要戴口罩(豬嘴)?」「你放TG我梗係要戴口罩啦!」對方竟然拋下一句「快啲返屋企喇」,繼續往前衝。
荃灣手足們、一眾黃先生黃師奶都認識Ricky,有事找他,有物資交給他。中大事件之初,校內急需繃帶、冰包,「當日全個荃灣冇晒冰包,繃帶冇晒,電筒冇晒,佢哋(同路街坊)mark低邊間日本城去過,掃晒貨畀我。」物資齊集荃灣連儂牆,紅白藍袋過百,內裏泳鏡過千,鐵甲威龍頭盔逾20個,雷射筆無數。萬事俱備,十幾個防暴殺到,百般挑釁,他情知不妙,推開在場百多個街坊,自己一夫當關。
「2019年6月前我係好暴戾嘅人,我認為唔公義就訴諸暴力,試過喺荃灣見到『城管』票控阿婆,我可以走過去打佢,打得好勁。」連儂牆那次他卻以大局為重,「我咁耐以嚟堅持我自己條命係我自己選擇,如果當日我俾人拉,甚至俾人打死,都係我個人嘅事。我可以為自己做嘅嘢犧牲,但我唔可以令街坊為我做嘅嘢犧牲,我寧願佢哋欠我好過我欠佢哋,我好自私。」方仲賢因10支雷射筆被捕,當時肇峰有一整箱,反而沒事,警察搜完查完叫他搬走。
昔日賺錢享樂,如今服務別人,抗爭期間他每天在連儂牆耗八個鐘,有若上班,「你唔企喺條街,又點知邊個𡃁仔冇飯食,點知佢屋企有家暴?」他說:「其實連儂牆有啲手足好X憎和理非行過嚟講加油,加乜X嘢油箒?你哋淨係識返屋企睇X住個電視機,就話抗爭。我唔係攻擊黃店,我最嬲大家企喺黃店門口排隊食餐晚飯,就覺得好幫助,不如你行入去叫杯凍檸茶,放低200蚊,然後上連儂牆貼一張紙,功用會唔會大好多?」
死好彩過後 留命睇清算
有手足代他去連儂牆便即出事,還未貼文宣就被捕、搜屋,「點解手足話我好運?如果我喺上面貼文宣應該拉咗我。」從沒吃過警「民」的虧,一次見五人拆牆,單人匹馬趕他們去荃灣警署,其間對方跳上的士,他充當人肉路障,終於迫令眾人入差館,控告刑事毀壞。街坊在連儂牆附近設了閉路電視,拍到差人徘徊,「開頭以為佢攞走啲文宣做證據,X你原來唔係,喺度揀邊包memo紙未開封,袋X埋落衫袋!」
今年初遮打花園15萬人集會,警方腰斬,群眾四散,他坐在天橋上,依手足所言跳下,跌不死他,再往山頂方向跑,兩名防暴截停搜袋,發現1,000張文宣,問:「你哋為乜出嚟,五大訴求呀?」Ricky反問:「你係咪要我講?」「你講。」「我就係要停止警暴!」對方竟沒即場施以警暴,留下他的「九命」,還說:「下次見到面再傾。」
大難不死必有下文,當晚行到置地對出,一名陌生男子提供義載,他沒上車,「返到屋企我搵呢個人張相,畀我搵到,佢係一個喬裝警員!」他曾向鄭松泰訴說上述經歷,「佢話我今時今日未俾人拉,未俾人打死係好彩,我又覺得自己真係好彩。」肇峰訴說:「所以佢同我講:『你下次真係唔好咁衝動,今時今日你留返一個適當時間去清算呢班仆街好過啦!』」
還曾置身旺角衝突,防暴向他直衝,「我預咗畀佢哋𡁻,但結果𡁻隔籬嗰個,我都係企喺隔籬冇事。」肇峰承認:「我有諗過鄭松泰講嘅嘢,我應該係好彩。」不怕死便死不去?他也說不準,這個人不怕死卻可斷言,「死嗰一刻可能一秒,你一槍射死我,你兜槍打落我個頭度,都係一秒,但你唔好射爆我個腎,要我喺醫院捱一個禮拜。我唔驚死,我驚個過程。」
人生可以隨時終結,性命可以留在戰場,他說:「我唔係自大,要玩玩過晒,要做做過晒,唯一想做係去南非。我(以前與朋友)可以喺大陸玩一個禮拜,使20、30萬,去泰國又使20、30萬一個禮拜。」每年感受泰國潑水節,今年當然除外,「一個人可以使十幾萬,唔知點樣使,過到去攞住叠錢派,好似賑災。」

後記:我想講乜X嘢就講!
今次訪問本來講抗疫,肇峰挨家挨戶派口罩給基層,包括青衣康美樓。也只有他,早前到一間生產商買了200個口罩,但第二日再去,對方已拒絕出售,他名副其實跪求五小時後,對方感動到送他100個。記者不料得到上述故事,疫情只好輕輕帶過,一切都是選擇,而這兩個字正是他一生訴求,這個圍村人幾代單傳,竟然改名又改姓,就讓原名留在過去。
離經叛道的他說:「我唔想由政府安排我條路點行,我選擇食煙,我生肺癌係我嘅事,我唔想你因為關心我健康而幫我選擇條路,我寧願喺有生之年呼吸一路以嚟嚮往嘅自由空氣。」如果最後那句太堂皇,下一句比較貼地:「我想講乜X嘢就講,想做乜嘢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