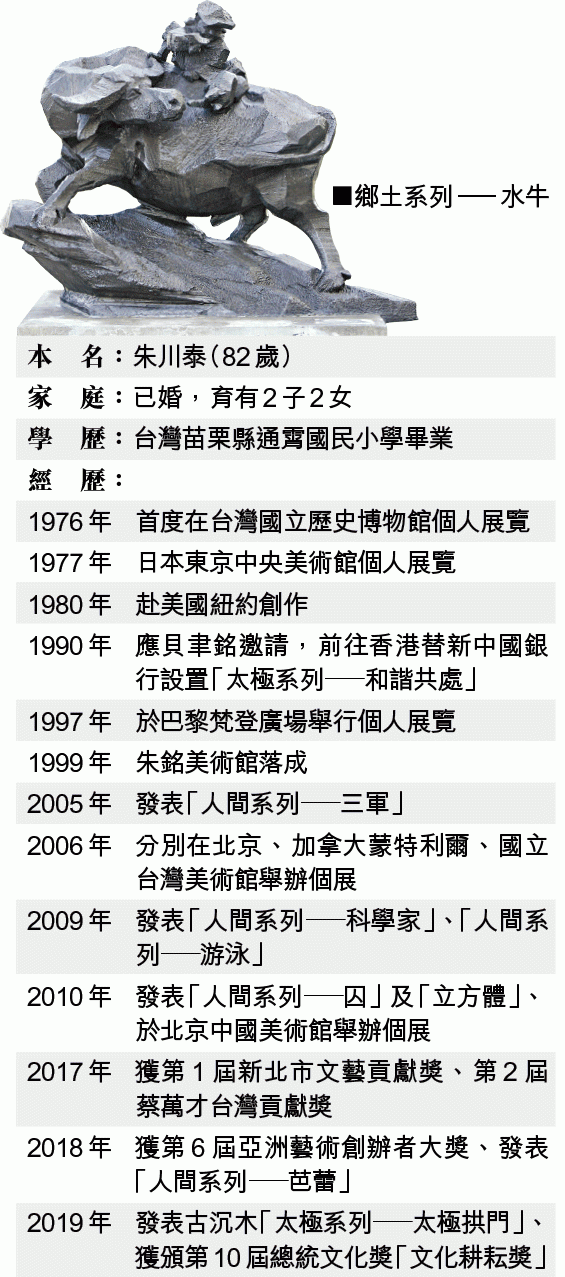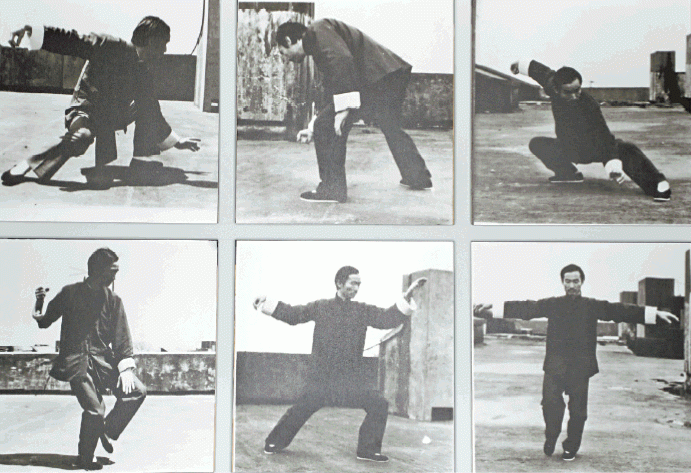
在武漢肺炎疫情緊張時,我與國際雕塑大師朱銘相約在台灣金山朱銘美術館,時間沒有在82歲的朱銘身上留下太多刻痕,戴着棒球帽、穿着綠色夾棉外套跟運動鞋,朱銘樸實低調,脫下口罩拍照的他依舊精神飽滿,行動利落。
我們請朱銘在著名的「十字手」雕塑前拍照,遊客看到本尊驚喜誇讚:「老師!我覺得您很了不起。」朱銘笑回:「是可以活到現在很了不起嗎?」接着自顧自說起笑話:「有一次我來美術館,剛好遇到一群小朋友來參觀,老師跟大家介紹我,結果小朋友嚇一跳說:吓?朱銘還活着喔?」話音一落,大家笑成一團,笑得最開心的就是朱銘。
記者:宋汝萍 攝影:沈君帆、梁建裕
朱銘能夠躍上國際舞台、在世界藝術殿堂大放異彩至今,除了憑藉風格獨具的「朱式」藝術作品引人目光外,蘊含在他身軀內,猶如岩漿般滾燙綿延的豐沛創作能量,及從不停止的自我挑戰更是兩大關鍵。從38歲那一年竄紅至今,朱銘幾乎沒有一天停止工作過,且創作素材包羅萬象,從石頭、木頭、海綿、發泡膠、不銹鋼、青銅,只要經過他大刀闊斧或揑揉扭轉後,就能幻化出一個個正宗「朱銘製造」的藝術大作。
他的最新作品古沉木「太極系列─太極拱門」,在去年朱銘美術館20周年慶時強勢登場,創作素材是一塊有5,000多年歷史的古茄苳沉木,「想想黃帝可能爬過這棵樹,我就很開心。」朱銘透過細膩的觀察,在保留樹體原有氣韻及質感前提下,順着木頭造型去做雕鑿切割,「除了刻太極拱門,其他做法都會破壞原貌。」他對作品非常滿意,「但不是我厲害,是木頭本來就長這樣。」朱銘說,過去的太極系列都沒有順着木頭刻,這件算是最成功最完美的。
朱銘把玩各種素材,而在創作時,都要聽到「材料開口講話」。「綑海綿綑出來它講的話,木頭它講不出來;綑不銹鋼講的話,海綿也講不出來。所以每一樣材料,我都會花5到6年時間,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它開口講話,我才放手。」他透露,之前有位哈佛副教授參觀他的工作坊,看到他把3厘米厚的100多噸不銹鋼反覆綑綁加壓,現場不但發出巨大聲響,還一直在冒煙,副教授看得非常震撼,頻頻跟他說,你做的不銹鋼有爆炸性。朱銘樂呵呵地說:「科學家說我有爆炸性耶。」老先生講到興起時,開心得像個頑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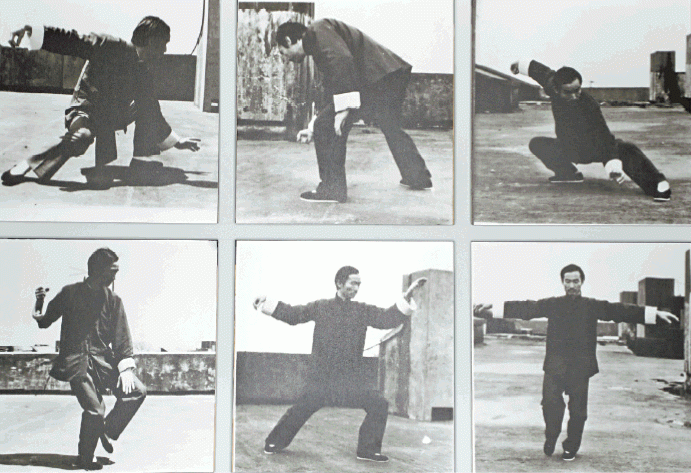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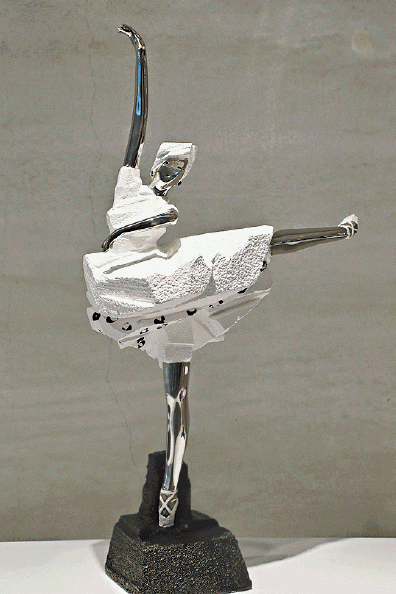
啟發藝術之眼 首要條件勿跟風
朱銘成長在台灣社會動盪不安的戰爭年代,在朱銘之前,家中已有10個兄弟姊妹,父母生下朱銘時,2人的年紀加起來已92歲了,所以朱銘小名就叫「九二」。
身為家中么兒,朱銘非常受到疼愛,通霄國小畢業後,先在雜貨店當店員,父親希望兒子能有一技之長,於是帶着15歲的朱銘向木雕師傅李金川拜師。朱銘學了3年多,技術逐漸純熟後開了雕刻社,隨着作品越來越多,有了一點名氣,但他心裏清楚,他想要的不止如此。
朱銘非常仰慕雕塑大師楊英風,渴望拜他為師,可是,二人素不相識,朱銘想了很久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最後決定直接帶著作品登門求師,而且準備好3年生活費。朱銘的堅強意念跟細膩的作品感動楊英風,楊英風答應收他為徒,並將他的名字從「朱川泰」改為「朱銘」。
如果說李金川教會朱銘技術之手,楊英風就是打開朱銘的藝術之眼。
朱銘說:「碰到好老師,注定了命運。」進入楊英風旗下後,滿心期待的朱銘猶如乾枯已久的海綿遇到湧泉,恨不得把楊英風的一切全學起來。沒想到拜師第一課,楊英風只教了他4個字:「不要學我。」朱銘起初不懂,只好把它記在心裏,後來才慢慢體會。
「技術可以靠學習,但藝術要有風格,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哪裏是學得來的?」那時楊英風認為朱銘的技術已臻成熟,需要的是破繭而出,所以楊英風從一開始就斬斷朱銘想「模仿」的念頭,「滿腦子都是別人的東西,是創作的障礙。」回想起老師苦心,朱銘非常感恩:「我很幸運碰到這個老師,老師把我帶到對的路上,所以我學的藝術是活的,自己去想,自己去創新,所以靈感源源不絕。」
在楊英風指導下,朱銘逐漸摸索出自己的雕刻心法,1976年3月,朱銘在歷史博物館舉辦生平第一次個人展覽「鄉土系列」,作品包括關公、包青天、李鐵拐等傳奇人物及充滿鄉土風味的民間雕刻,展出後轟動台灣藝文界,朱銘甚至被標榜為當時台灣鄉土運動的象徵!
不過朱銘沒有被瞬間湧來的名利沖昏頭腦,他知道,「鄉土系列」的水牛、關公走不出台灣,所以開始轉向雕刻已經學出心得的太極。「我的個頭小,抵抗力不好,老師就叫我去打太極,學會整套拳法後手就癢了。」
很多人並不看好朱銘的太極雕刻,甚至冷嘲熱諷,但朱銘不畏人言:「我第一次展出關公、水牛,一夜就成名了,改變刻太極,很多人都說不對,但是我知道,必須要到國外去看看,驗證我的想法,所以就把過去的那一套統統放掉,開始刻太極。」
勇於突破舒適圈,從頭挑戰的朱銘,果然靠着充滿禪意的「太極創作」贏得世界目光,而朱銘的太極作品,也從一開始有手有腳有動作的「象形」,轉化為沒有五官與動作的「會意」,就連完全不懂中國文化跟武術的老外都讚不絕口。朱銘很得意說:「太極在國外展出那麼多年,從沒有一位外國人問我說甚麼叫太極,我要的就是這個造型、這個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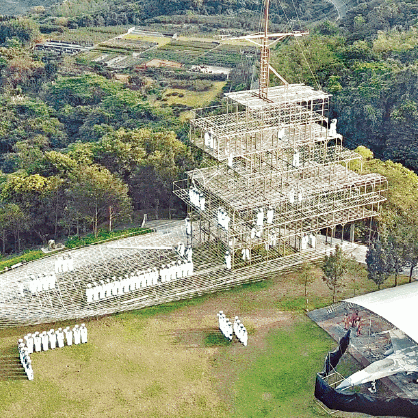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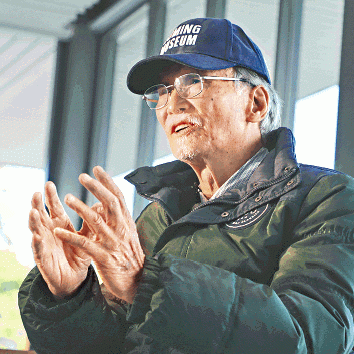
把作品留在當下
石破天驚的「太極系列」廣受好評,但朱銘心中的創作火燄還在熊熊燃燒,他勇於挑戰的性格再次爆發。1980年朱銘毫不猶豫再度拋下盛名光環,跑到美國紐約去「看看世界」,他不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好,也不懼怕回台灣後丟掉名氣,而是一心一意過着白天逛藝廊、晚上練習雕刻的時光,還常常持續工作12個小時以上。朱銘還曾開玩笑說自己是:「50c.c.的車身、90c.c.的引擎。」靠着這股燃燒生命的氣勢與努力,隔年他在美國漢查森藝廊的展覽叫好叫座,此後,朱銘的創作更勢如破竹,強襲進歐洲,1997年他在法國巴黎梵登廣場舉行個展,成為第一位在梵登廣場舉行展覽的華人雕刻家。
此時可說是朱銘的創作巔𥧌,他的「太極系列」已臻圓滿,同步創作的「人間系列」正燦爛盛開。如果說「太極」靠着神韻向世界證明了朱銘,那「人間」展現出的樣貌就是讓朱銘找回了自己,不管是軍容壯盛的「人間系列─三軍」、討好趣味的「人間系列─科學家」、意涵深遠的「人間系列─囚」,都反映出朱銘對大千世界的關照。
朱銘說,創作是一種過程,每一個階段的作品,都有當時的意義跟精神,但有人不懂,「還跟我說,他買的『人間』已好老了,想拿舊的作品給我維修。我告訴他不要修,老就讓它老啊,這才是代表那時候我刻的人間,為甚麼要讓它變成今天的更新版呢?」
現在朱銘隨便一件作品要價可能成千上億,但朱銘淡然地說,他只管創作,「創作沒有叫好不叫好,也沒有管能不能賣,都跟我無關。」
能夠一再顛覆自己,持續在每個階段推出讓人驚豔讚嘆的作品,朱銘的創作靈感都從哪裡來?「創新事實上是很簡單的事,因為只要習慣用自己的態度創作,一切都會水到渠成非常自然。」
他舉例,「你刷牙吃飯要想嗎?統統不用,只要用平常的生活態度創作,就會與眾不同了。反過來若要去學別人,才難!你叫我去學趙無極、張大千,我沒辦法,但做我自己的東西,太簡單了吧!創作也是這樣,沒有例外。」
我問朱銘未來有新創作嗎?老先生馬上回答不知道,「我怎會知道我未來的計劃呢?」他在意的是現在,「我在玩小孩子的樹脂土,用樹脂土來做雕塑。」
82歲的朱銘日日創作,支撐他如此有元氣的就是運動,「我每天運動30分鐘,從不間斷,運動比吃補品還有效。」他還自己開車上梨山工作室,「不過是慢慢開。」
細細走逛一遍朱銘美術館,彷彿坐上時光機,體驗朱銘的創作人生。當初要蓋美術館時,朱銘的好友、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笑他:「蓋那麼大,還要養那麼多人,簡直是瘋子。」現在看著美術館走過20個年頭,朱銘自嘲:「我們這種事業叫花錢機構,不可能賺錢,連要打平都很難,20年來總算搞清楚這一點。」
我問他考慮退休嗎?「好像沒有一個藝術家退休的,我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創作是一種享受,不是一種負擔。」
臨走前,朱銘調皮地問我:「你真的喜歡『三軍』嗎?」我秒答:「非常喜歡。」老先生笑了,在午後陽光映照下,朱銘身影與他背後的太極融為一體,而我看到的是一幅人間好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