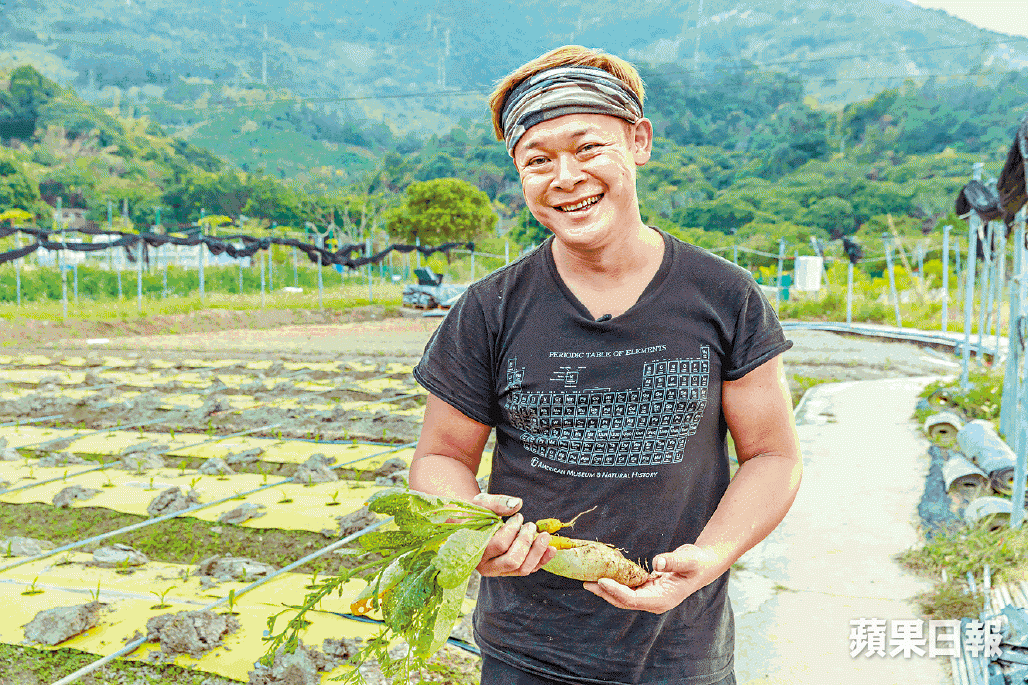梁祖堯是舞台劇演員,是風車草劇團的台柱,現在也是半個農夫。
疫情關係,舞台劇界幾乎停擺,風車草劇團原定3月上演的劇目《新聞小花的告白 2》延期至8月。梁把空出來的時間,投放在耽擱已久的夢想——耕田。他來新興農場幫忙,開班教學製作蕎麥麵,收費過千,他一毫子都不袋,全用來支持農場營運。他的收穫在別處。
初下田,他錯用蠻力,弄壞了三支鋤頭,才逐漸發現適合土地和自己的力道。他看着播下的種子,思索着,應該保護好它們,還是該讓小鳥吃掉?畢竟這裏原來是牠們的家。他的思考模式在改變,他的生存模式也在改變。
「我來到田野,我係搵返一種生活。」在這裏,他有一塊「實驗田」,種滿了蘿蔔和香草。吃過田裏的新鮮蔬菜,他的味蕾被重新開發。
撰文:黃珍盈 攝影:Fred Cheung

梁祖堯捲起衣袖,赤着胳膊,戴上頭巾。這是他近來的每日裝束。記者來到的時候,他在搓揉剛做好的蕎麥粉麵糰,分出一塊給農場主人的兒子揑在手裏。農場主人的妻子笑了,「屋企都有泥膠,但佢唔係好鍾意。泥膠太黏。」
那種溫馨像濕泥裏的甜菜一樣,沉實地紮在空氣裏。這種日常,令香港對他來說有了全新的意義。梁深受感動,「我都不知道,自己原來咁鍾意呢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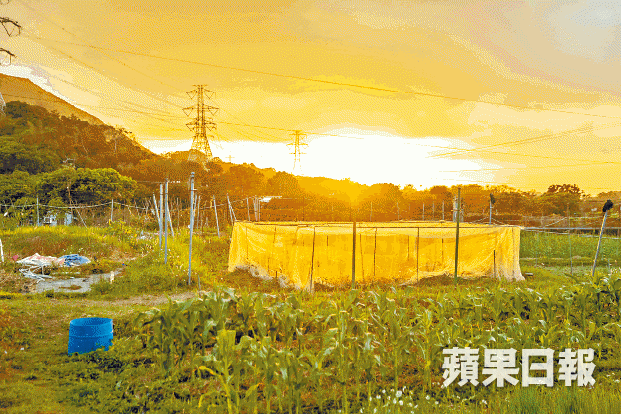


離地農夫 從頭學起
說起耕種的挑戰,他覺得心虛,因為他不是「生產型農夫」。這段對他來說如獲至寶的另類生活,是很多人的唯一生活。「有一群好努力好用心的人默默地為我們付出了好多好多,但是他們得不到一個啱的回報。」
這種心虛、喜悅和驚奇緊緊交織,轉化成動力,驅使他着手努力推動本地農業。「我好希望香港人可以有機會試到香港自己的農作物。因為真係好好味。」
梁做了10多年天台農夫,種過米、香蕉,一年甚至可以種出80個熱情果。可是下了田,梁才驚覺對農務的認知少得可憐。「我發覺我原來係乜都唔識——係乜Q嘢都唔識。揸個鋤頭都唔識揸。以前所有覺得自己種得幾好的知識,在這裏全都要由頭學過。」
攢養起來的泥土和土地是不一樣的。
梁來到農田裏第一件做的事是收割,但讓他最感到滿足的卻是開荒。他向我們展示手臂上累累傷痕,都是除草時留下的。翻開土地,會看見10多年前用來裝載蔬菜的箱、生銹的鐮刀。他心裏感動:現在願意開始的話,一切都不算太遲。
原始的體力勞動讓梁體會良多。「我一心只是想要快點犁開那些土,快點開始種嘢,但原來有些事真是急不來。操之過急,我便弄壞了三支鋤頭。但那並不代表我很大力,只代表我用錯力。做每一樣嘢都有它的方法。有沒有更有效的方式,是保護到你自己,又保護到鋤頭?」
開荒以後,他便去打理一塊屬於自己的實驗田:翻泥、做堆肥、搭棚架、灌水。對梁來說,這樣才是耕種。每個禮拜只來一次,只參與收割,是「無恥」。這也是為何肺炎疫情發生後,梁才有時間真正下田。務農的根本,就是土地和人的相處。
一口原味 尋回味覺
和一些老農夫聊天,他們跟梁說:「你們吃大陸菜的人,根本不會知道那些菜原本是甚麼味道。」香港人愛吃、嘴刁,對食材來源卻從來沒有太大考究。「我們由細到大都未吃過他們所謂『啱味』的蔬菜,又怎麼會有這個味覺去作區分呢?」梁有種植經驗,大概明白農夫的意思。「如果你吃過一個樹上熟的番茄,你就會知道番茄不是這樣(街市裏賣的那些)的味道。
「我們香港人一年四季都吃芥蘭菜心,但是原來香港要在冬天才種到的。」所以其他時分,我們都在吃來自大陸北方的芥蘭菜心。「這樣下來,我們每天都吃的,其實沒有一樣是來自我們屋企的。
「那怪不得我們沒有自己的意識,我們每一天被餵的都是不同國家的嘢。」一邊廂,日本人吃日本米。另一邊廂,香港的農產品自給率只有大約2%,整體糧食自給率也只有大概一成。依賴進口貿易的結果是,大部份食材一年四季唾手可得;人們忘記了,自己大可以跟隨着土地的生育節奏,吃當造的農作物,品嚐最鮮。
香港的農產品,例如是剛磨好的新米、在香氣最濃郁時摘下的士多啤梨,都讓梁大為驚艷。他如數家珍般介紹着,一邊舔嘴咂舌地讚嘆說,「哇,真係好食到不得了。」對梁來說,「自給自足」的意義不是一種恢宏的願景,而是一種覺醒。「我們如果想要保護我們種出來的食物,或是我們的土地,我們就要從我們的飲食習慣開始,我們就要開始去想『不時不食』這件事,我們要習慣在不同的時節,吃當造的食物,這樣我們香港農業才會有機會,才會有希望。」
有些事情無法回頭,難免讓梁覺得悲傷。例如是失傳的元朗絲苗,例如是被用來作非農業發展的耕地。但戲劇告訴他,傷感必定要化為行動才有價值。「(但)我努力去耕種不是要展示傷感,而是我很想告訴我自己和身邊的人,我們是有得揀去食啲乜嘢。」他以身作則,開始土炮製作完全香港製造的三餐。訪問前一天,他用香港的臘腸、大澳曬的魷魚乾、八鄉小隊種的米做午飯。「今天就有香港養的魚……蔬菜就在外面的田裏拔。
「我會努力地推廣。」他真誠地說。「我好希望香港人可以有機會試到香港自己的農作物。」香港農業固然面對很多問題,如銷售問題,如耕地問題。但更多時,更是一種心態問題。要香港人做到「不時不食」、多吃多買本地菜,為何如此困難?
「因為他們不知道(本地菜那麼好吃)。他們不是不想。」梁笑言,「我們未受精那一刻,都已經是夏天吃菜心大的啦!」疫情爆發初期,香港出現「搶菜潮」。市民預期大陸進口的蔬菜將因疫情供應不穩,於是恐慌搶菜,大陸蔬菜價格上升,不少人轉買本地蔬菜,香港農場的銷售量大增。但過了不久,一切回復原狀。香港人的三分鐘熱度,並沒有讓梁感到氣餒。他覺得,遲早大家會知道「香港的菜是好好味的」,並建立起吃本地菜的習慣。
守護士地 也是抗爭
「對上這八個月告訴我,沒有事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唐吉訶德的故事。想法好像很浪漫、很天真,但其實只要事情是對的,而你能繼續堅持下去,你是會改變得到甚麼的。」過去大半年,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了保衞家園的決心。現在運動步向沉寂,梁祖堯來到田園間,盼望守護土地,是不是這場保衞戰的延續?是不是一條新戰線?
「我不能夠代表所有的農耕者去講這句說話,但對於我自己來說,它是。」同時,他也急着對「運動沉寂」表示不贊同。「因為我覺得它沒有沉寂到,我冇,身邊每一個人都冇。只是方式不同了,而我覺得這個方式的轉型是會令這件事更加堅固,或者更加成熟。」
他又說起朋友近日跟他聊到的墨家遊俠,眼中有種嚮往:他們會到處去幫人開田,教人種田,教人如何保護自己,很溫柔,很有愛。梁也想以自己的方式回應這個社會。「我們保護返自己的食物來源……認識多一點自己的土地,多認識這裏土生土長的食物、植物、動物,然後你和這個地方的情感會不同。這些對我來說是些很實質的能量。」
然而,這個地方在他心裏的價值,似乎和一般人賦予它的價值有很大落差。「一講到公平貿易,大部份人只是想到南美咖啡、非洲的巧克力……其實不是的,香港的農夫才最需要公平貿易。這個議題其實好近。」他難以置信地比劃着,「他們種的白蘿蔔試過8毫子一斤賣出去。8毫子一斤啊!一個白蘿蔔那麼大,種得那麼漂亮,有機生產……最後還要賣不完,送去堆填區,公平咩?」
進口菜很便宜,但梁強調進食有代價。「你每吃一條大陸菜,香港就會少緊一塊農地。」對於本地菜價格偏貴,梁覺得,人們要理解當中每一分錢的意義。那個和一般街市菜的差價,是為了保護這個土地、為了不用化肥、為了艱難的銷售、為了井水的電泵而付的。「這些錢我們給得起有餘。你吃過的話就返唔到轉頭。」
無法回頭的,還有他對香港的感情。以前工作最艱辛的時候,梁會想,存夠錢就移民京都,不夠錢就去高雄。但現在,移民的想法已蕩然無存。「尤其是對上這八個月後,我點都會喺呢度同大家一齊行落去。有些事情我要健健康康地睇到。好的要看的,不好的也要看到,因為呢個係我屋企。」
【半農半演但願到老】
訪問結束後,梁帶我們去看他的實驗田。他隨手拔了幾根小蘿蔔說:「這就是我的晚餐啦。」回到棚裏,他把訪問前搓好的蕎麥粉麵糰切成麵條下鍋。夕陽下,農夫的一天將盡。鍍了一層粉光的栗米葉還是那麼高,生命力在看不到的地方流動。
這是梁祖堯找到的生活。
「香港人需要生活,我哋無生活咗好耐啦。每天上班下班。就算去消費,去休息,都是暴力式消費,暴力的休息……對我來說,那都不是生活。」但現在,梁終於找到了一種平衡。演員和農夫的生涯,互相成全。「藝術的作用就是用來提問,但是每個人就要在生活裏找你自己的答案。」
梁選擇讓大自然調息自己的身心。他發現,身體會回應土地的節奏。夏天自然想吃盛產的瓜、豆類,秋天就渴求番薯、南瓜,冬天就想吃葉菜。「我想生活咋,我對搵大錢冇興趣。」四十年來從來沒有買過股票,因為這不是他的心性所向。「半農半演的狀態讓我覺得好開心……兩樣都是可以做到老的事情。」
他雖然擁抱農地,卻從未想過放棄舞台。「唯一會令我放棄任何事情的原因,只能是我對它沒有興趣。我是不怕辛苦的,一樣事情辛苦和困難是不會令我止步的。」所以是想維持半農半演的生活?他看着很遠的地方說,「我好想。」
突然安靜了一會,梁解釋說,「我在想我還有沒有嘢想做。例如我會想應不應該多關心這個社會。但創作和耕種都是在關心社會,都在做。」
或許一切很單純,只像書寫自然的台灣作家吳明益所說的,「我還是覺得,自己能有一塊田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