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富華facebook形容自己「不停蹄的馬」,還加上日文片假名60マイナス4ノート(60減4碌)。別人扮細29+1,他卻56歲認老,絃外之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但馬不停蹄也就是字面意思,袁富華家住元朗村屋,愛天天踩單車,裝備直逼運動員,與《翠絲》裏的打令哥、《叔‧叔》裏的阿海大相逕庭。這才叫好戲!若他現實本亦娘娘腔,演回自己,便談不上技藝了。
袁富華,近期備受矚目,大器晚成,虛名不用多提,實際地,是疫市中仍難得有工開的幸運兒。
他驅着雙輪,呼嘯而過,像要追回那沒被留意的青春。
時空都不等人,這天的南生圍,很快又話要收回發展喎,惟有頂──硬上。

歸園田居
何止,Ben哥有時還挺兇的。家住偏遠村屋,不能沒私家車,他習慣自駕至西鐵站轉乘。每逢出村口,單線雙程遇着外來貨van不肯讓,他會(這天也幫我們司機)大喝:「走開啦!」逼人家退。其實袁富華並非原居民,此舉頗有拋浪頭意味,他苦笑說:「狹路相逢,往往不講道理的一方便獲勝。」
理想世界,溫文爾雅。「為甚麼會搬來?才兩年,只因之前隨舞台劇界朋友遊歷歐洲一個月,生活習慣咗,回港,頓覺市區太壓迫,困不下去了。另一朋友住村屋二樓,叫我來看看,我一看就鍾意。除了做運動,還周圍影吓雀仔,以前不會的。」
兩年前,即是演《翠絲》男花旦竄紅的同時?寫慣娛樂新聞,筆者馬上聯想富起來買磚頭那一套。袁富華說:「這裏租的,原本在港島山道的單位放租,已經夠畀這裏,地方更大。人呢,肯改變想法,便很容易滿足。山道租給個德國人,最近因疫情回國。」
他的心靈故鄉何嘗不是歐洲?續道:「那次2015年,我們於倫敦劇院演《Macbeth》,我覺得很夢幻,流下眼淚,黃皮膚在莎士比亞地頭,竟也有人識欣賞。」筆者打趣:「你扮馬克白夫人都得啦!」袁富華答:「英國古代,的確一樣用男人反串的,不過我未得。」
就別笑,隨口爛gag,認真考慮地回應,他正是如此嚴謹。回頭說,該有預感《翠絲》打令哥能夠跑出吧(後更奪金像最佳男配角)?「哪有此心思諗住怎成功?心思不如放在角色上。舞台劇比打令哥更凌厲的都有。電影圈就係咁,一特別少少就……」

演到老
這句可圈可點了。袁富華不算電影人,他較靠近舞台劇界,但又非演藝學院畢業。簡單講,為何早年沒受訓加入電視台出身?「簡單講,因為無人請囉,又要搵食。我中學半工讀,開始參加西營盤業餘劇社,然後沙田劇團,慢慢學。」
特立獨行,證明並不一定要埋堆,他走一條與別不同的路。正如與多年女友不結婚不同居,本屬正常,世人以為奇怪而已。
延續剛才話題:「我喜歡Tom Hanks,他《Saving Private Ryan》只心事重重,淡淡然的,並不一定要像阿甘或者流落荒島自言自語,可以在平淡中見功夫。」
無論如何,吐氣揚眉,飄飄然嗎?「無。來到這年紀。已不是第一次,20年前,我演《人間有情》,個個讚我得,於是我離開劇團,點知原來我未得,在屋企呆坐足幾月,跌到好慘。恃才傲物,根本無才,傲咩物?演戲這回事,可以到死那天都未得的。」
娛樂圈豈非紅咗就乜都得嗎?「所以我不是說紅,是說演戲。」
究竟靠識做戲抑或識做人?「那時兩樣都未識。2018年,我已經攞咗金馬獎,知道舞台劇《好人不義》劇本好,制度上要遴選,我便自行交表格,主辦單位話唔敢casting我,我話照去啦,要放下身段,我想做囉,就係咁單純。所以,我怎會飄飄然?」
他演《翠絲》易服癖老漢,先化老妝底再扮女,裏裏外外多重層次;現實中的他依然有火:「踩單車係,可能毋須keep fit做動作場面了,但永遠要保持身體靈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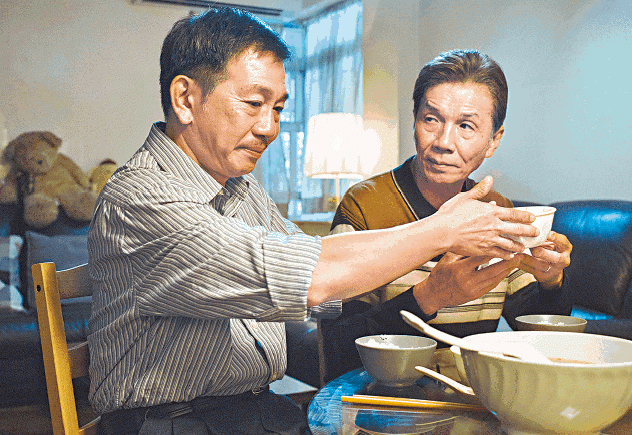
生而不平等
《叔‧叔》阿海則屬於內斂同志。剛過去的2月,袁富華為此片赴德國柏林影展。「又係5年前,遊覽經過影展場地,有些導演椅放着,我心想有朝一日在這裏放映便好,估唔到5年後願望成真。」出席四個答問會。「主要講解文化差異,外國觀眾未必明,點解咁多包袱?他們覺得唔開心即刻離婚,沒我們咁重家庭觀念。這也是演員作用,更有意義。作品拍完就拍完,無得為獎項加油的。
「我始終中國人,當然我不太傳統,但希望從中尋找平衡。」
擅演性小眾角色,Ben哥是平權主義者嗎?
「我並非平權主義者,我沒去爭取,但我支持所有ask for平等的事情。人,生而不平等,正因為不平等,要改善制度令到它平等。」
多得袁富華,分別演活打令哥的transexual和阿海的homosexual,形神各異,科普眾生,功德無量;換轉想當然耳的爛片膠劇,一律卡通醜化交貨。「要有改變,是裏面的東西。」他說。
卻想深一層,苦心孤詣幾十年,到頭來,憑這種特定戲路才廣受注意,能無一點感慨?「我做《喜劇之王》歹徒嗌『你唔係外賣仔』都好多人記得吖,還有《樹大招風》鹹濕佬……」筆者搖搖頭,坦白講,那時叫不出他名字。
袁富華說:「演員咁已經好滿足,被記得個角色,不必知道係我。」
觀眾會否出於獵奇心態?「不能要求觀眾用甚麼角度,吸引咗人先,係第一步。有人睇演技,有人睇劇情,講到尾,娛樂箒。」
袁富華客席教演藝學院,談及圈中青黃不接,他說:「每年生力軍入行,看製作人夠唔夠膽嘗試箒,宗旨在培養新人的話,給機會,何來青黃不接?根本有雞先抑或有蛋先的問題。」
不偏不倚,為學生也為自己發聲,不亢不卑,因為,他是其中一匹搶閘登場之新舊馬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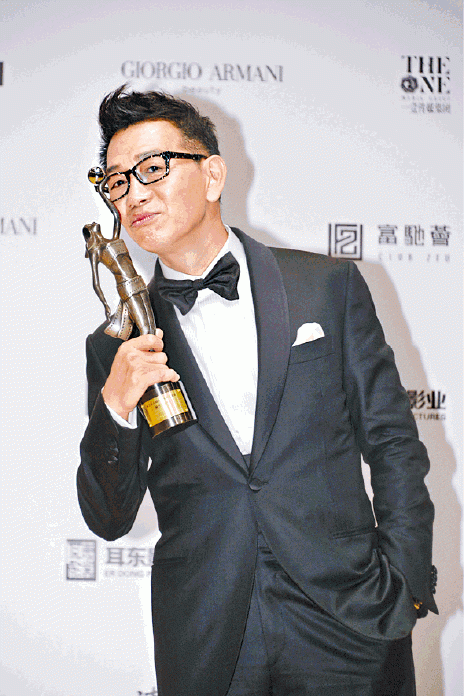
後記
訪問中,袁富華不只一次提及「人物小傳」,就是劇本沒交代的前因後果,他自行想像捕捉。打令哥有人物小傳──他應該從沒變性戀的partner,憑學做男花旦得到滿足,所以他性格樂觀;阿海有人物小傳──他清楚自己取向,間中遇上同性戀partner,但家庭責任感重,所以性格內斂;連僅出場一次的「你唔係外賣仔」的《喜劇之王》歹徒也有人物小傳──為何惟獨他看穿周星馳假扮?嗯,一定是這歹徒閱歷較豐富、戒心較重……Ben哥自嘲,若非這樣做筆記,他資質魯鈍,根本演不來。
雖然,角色登場往往只現在進行式,但怎會沒歷史?壞蛋也有變壞的理由,真實裏,更加無人認命是茄喱啡,誰的故事都精采,誰都值得立一篇人物小傳,而非小人物傳。
豈不很似專訪?與被訪者相處雖三數小時,談天說地,不只聽他/她講甚麼,更觀察他/她做甚麼,瞻前顧後,希望寫出來呈現較完整的圖卷。
甚至,在看本文的讀者,何嘗不是以偶然的時間,意圖理解全體,然後像袁富華般趕赴另一場人生如戲?
原來,我們都是行家。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