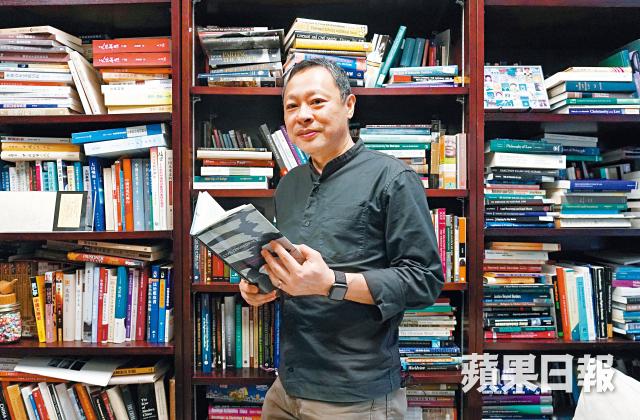
【六年蛻變】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遠在發起佔中之前,戴耀廷其實是香港法治的代言人。每年他都會帶領港大學生舉辦講座宣揚法治,其提出的「法治四層論」亦廣獲中小學教科書採用。這位名副其實的「法治膠」,近期卻意外地包容暴力,沒有譴責在法院縱火的示威者,早前甚至宣佈法治已成喪屍,將「法治已死」之論推向新層次,網民都高呼:「戴耀廷黐咗線呀!」
戴耀廷說,他沒有黐線,只是大家不理解其理論本來的彈性,「社會環境唔同咗,抗爭嘅道德原則自然不再一樣」。當年堅持和平瞓馬路的他,今天不再反對暴力抗爭,連武裝革命都能接受,直指是否組軍只屬策略問題,「好坦白講,我冇膽吖嘛,所以咪去搞選舉囉」。至於主流學術界對法治及公民抗命的理解,戴亦以批判角度看待,「西方文明社會早已過咗(獨裁政權)嘅階段,以佢哋嘅標準套落去非西方社會,係咪適合?」
世界上有兩個戴耀廷,本報專訪了2020年的那個,且聽他如何解讀2014年的自己。
記者:陳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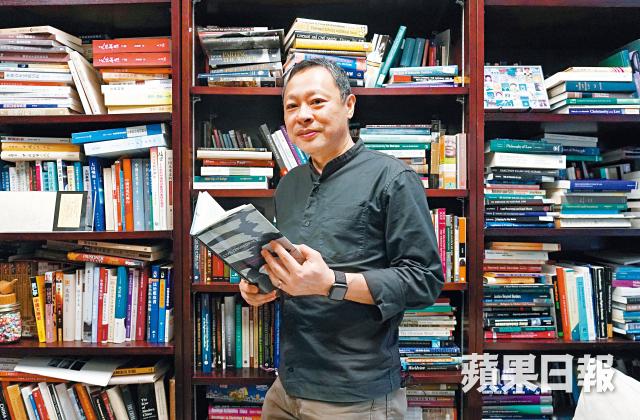
記:本報記者
戴:戴耀廷
記: 當年你強調佔中不會破壞法治,因為參加者會保持非暴力及承擔罪責,但今次反送中恰恰相反,示威者使用暴力及逃避法律責任,這樣是破壞法治嗎?
戴:社會環境改變了,所以道德原則也不再一樣。我當時發起佔中,主要是引用學者John Rawls的理論。Rawls認為,公民抗命適用於一個near just society(接近公義的社會)。2013年的香港社會勉強算是一個near just society,我們的國際法治排名很高,有民主發展的時間表,只是未能實踐,所以我發起一場公民抗命去推動它。何況當年香港的法律文化保守,如果我們提出一個更進取的行動,根本是不可能。
到了2017年黃之鋒判刑,楊振權法官說「有股歪風」的時候,你可以話我後知後覺,從那時起我認為香港已進入一個半威權時代。直到去年反送中運動,警暴力度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稱香港為near just society嗎?香港已是另一個社會形態,變成unjust society,我形容是一個authoritarianizing(正在專制化)的香港,它只是在「食老本」,令自己看似還有一點法治而已,所以我們不能夠再用同一把尺去看待整件事。

記:所以你現在是支持暴力革命嗎?
戴:是否必然一定要走向更激進,甚至組軍、游擊隊?這個就是策略問題,不同人有不同的代價及判斷。至於我嘗試用選舉去對抗一個專制政權,在國際上也不是新鮮事,很多地方也是暴力抗爭和參與選舉並軌而行,兩者並非互相排斥。
記: 你還未回答,示威者使用暴力、逃避罪責,甚至在法院塗鴉及扔汽油彈,本質上是否破壞法治?
戴:你把法治視為「一嚿嘢」,但其實法治是一個multi-dimension(多面向)的東西,示威者的行動可能是損害了一個dimension,但同時目的是改善另一個dimension,即使客觀的效果你認為只屬破壞,但你不可否認他的主觀目的是守衞法治。我們要問的是,怎樣的「破壞法治」才是真正的破壞,如果你說法治只是守法和司法獨立,那麼示威者就是破壞法治了;但如果法治的核心是制衡權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記: 問題是示威者如何說服公眾,破壞法院有助捍衞法治?
戴:關鍵是示威者對法院的公正性提出了疑問。我們必須明白,真正能損害法治的人是掌權者,當中包括法官。有時候我都覺得法律界人士過度將法院神聖化,我其實不太完全認同。現實上,根據外國的學術研究,在專制政權下的法庭,不是每個法官都企得好硬淨,他們會用各種方法去迴避問題,其實就係醒目仔咋嘛,唔會上身、唔會影響自己。所以你不能怪責港人質疑法院。
記: 即使示威者的動機值得同情,不等於其行為必然值得支持。凡事總有對錯之分,為何你不去作出一個判斷?
戴:一個人犯法了,法庭判刑時也會考慮其處境及動機。我有時候反而想問,是否一定要跌入「對或錯」這個判斷當中?為何我必須作出判斷呢?法律制度上我沒有權力去做,若說我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就更加不應隨便去作一個我也不肯定的判斷。正如港大校長張翔一開始就譴責示威者,我會問「你憑甚麼這樣做?你有足夠的資料去譴責嗎?」

記:按照你這個說法,藍絲一樣可以說,由於不清楚警察當時打人的理據,所以不作評論。
戴:對呀,他們也可以這樣說,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記:你這樣不是雙重標準嗎?警察暴力你譴責,示威者行為你就說無足夠資料判斷。
戴:在某些情況下,我覺得有足夠證據作出道德譴責,我就譴責,若你不認同,你可以反過來譴責我;但有些情況下,我覺得不敢作出道德判斷,就不作判斷。我不覺得這是雙重標準,因為我始終有一個(道德)標準去審視每件事。
例如火燒人事件(去年11月11日馬鞍山衝突),如果放火者真是示威者,我相信是可以譴責的。甚至乎,假設我們確認有人真的發起恐怖活動,傷害無辜了,這也是可以譴責的。我在文章中也說過,就算你要私了,當中也有道德界線,只是這條界線不需要像near just society般高,但你始終應該僅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而使用武力,過了這條線就可以譴責。20世紀初英國人爭取女性平權,一樣有透過恐怖活動放炸彈,但他們會確保附近沒有平民才引爆,這就是道德界線。
記:今次反送中運動,是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
戴:好多人覺得公民抗命必須是非暴力及承擔罪責,但其實這不是主流看法,只不過提出這個論述的John Rawls很有影響力,其理論亦被英國法庭採納為公民抗命的定義,所以傳來香港法庭。的確,Rawls的理論在near just society是正確的,但英國社會和香港專制化社會,根本已是兩個不同世界。
不少學者都指出,非暴力和認罪只是justifying factor,用來說服民眾這是一場合乎公義的運動,但這些因素並非運動的本質。另外我想指出,即使是今次反送中,參與非暴力行動的人(例如非法遊行和貼連儂牆)也是遠多於使用暴力的人,而且非暴力其實是暴力的支持基礎,好像一個金字塔一樣。

記: 回到法治喪屍論,很多網民都問你,既然法治已死,為何我們還要參與制度內的選舉?何不將精力留來搞武裝革命?
戴:法治喪屍論只是擬人法,它不是一個學術上嚴謹的論述,所以不可作為所有行動的基礎。坦白說,我是在打一場宣傳戰,政府有4.5億元資金宣揚「法治」,但我一元也沒有,惟有在語言上突破,攞啲爆啲嘅詞語。香港的法治未必是完全消失,但它已被利用來打壓公民權利。
沒錯,選舉的用途可能不大,但這是一個低代價、低成本的行動,不需流血,最多只是流汗。無論其帶來的進展多麼微小,但nothing to lose,something to gain,為何不去做?既然對方全天候打壓,我們便需要全天候反抗。選舉是低風險、低回報的行動,買軍火則是高風險、(或許)高回報的行動,就像投資一樣,不同人會有不同選擇。坦白說,像鍾耀華說的一樣,我唔夠膽(參與暴力革命)吖嘛,所以就選擇了選舉。
再者,我思考的不僅是抗爭成功,而是抗爭成功後如何重修社會。我作個比喻,在一個海洋中,深層的current(水流)持續在運行,水面則是時而平靜、時而大風大浪,但current永遠都在走,而非暴力就是current。你看2014年後社會很平靜,去年反送中突然風雨飄搖,但水底的current一直都在持續流動,而我的角色,就是去維繫這個current的運作。

記:很多人覺得你黐咗線,你是真的黐了嗎?
戴:其實我的理論從來沒有改變,只是社會環境不同,切入點就會不同。反送中的確令我很深化地思考,令我發現自己的理論可以accommodate(適用)到不同的局勢,原來有這樣的潛力。好像入獄之前,我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300下掌上壓,不過結果我做到,原來我身體有這樣的潛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