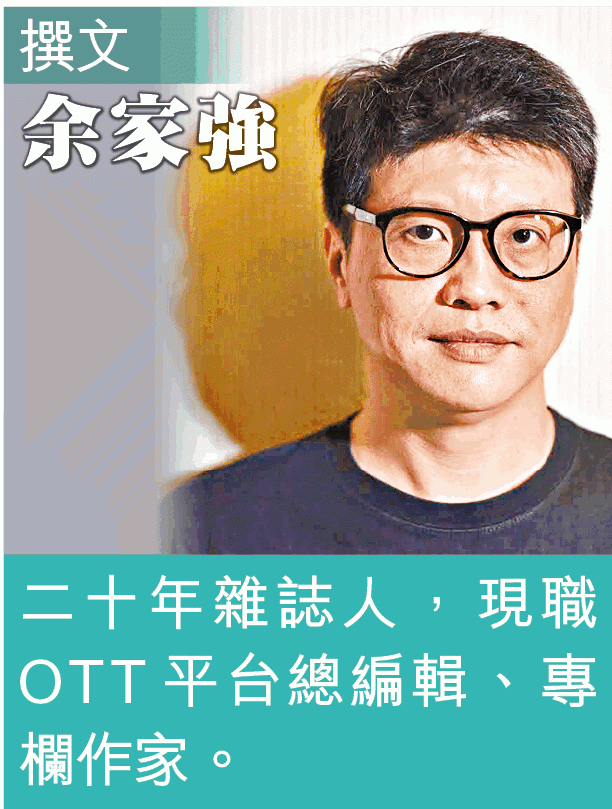
鄭丹瑞彷彿跳過了中年,由早期新進編劇、唱片騎師,到長期主持《勁歌金曲》等音樂節目,到千禧後仍在拍《六樓後座》、《分手一百次》等青春電影,正如阿旦這外號永遠年輕。然後,像突然,這天說:「11月我就65歲嘞,可以兩蚊搭小巴。」
沒中年有沒中年的好處,不用經歷那種進退維谷自怨自艾的尷尬,燃燒盡小宇宙,至今安心扶掖後浪,不要去羨慕,不要去妒忌。
可惜,「兩蚊小巴都唔敢坐了。」他續道。
何去何從?廣播人出道40年,從未如此「大時代」過,自家的工作室,亦坦言所有project被暫停。鄭丹瑞說:「人生,果然不能留在comfort zone。」於是他出山,為愛也為責任,主持健康節目,不再大台金牌司儀,不再商台營運總裁,搞上網。現況是:「曾經抗拒,希望進入。」他說。
正如一切挑戰。
攝影:羅錦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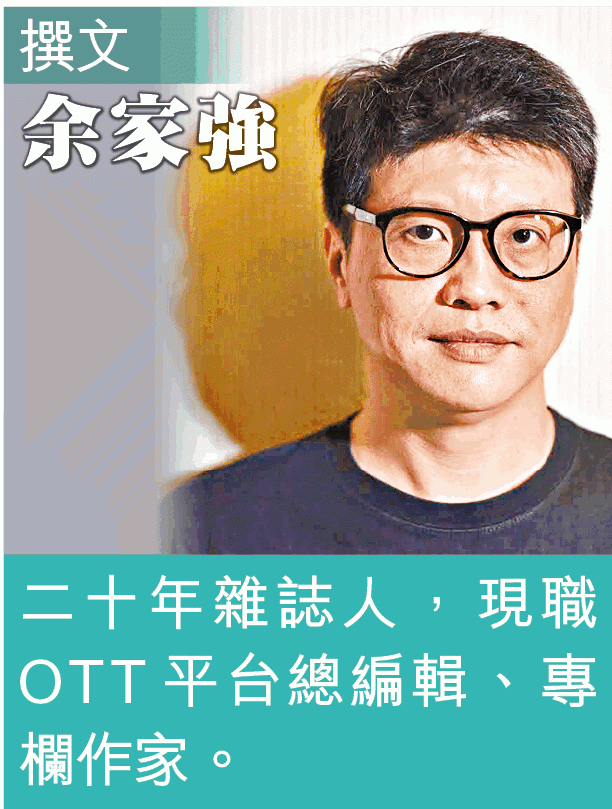
不是KOL
阿旦在啃着蛋牛治。他戒牛20年,非關宗教理由,就是想鍛煉心志,類似斷捨離,又想起生肖屬羊,遂連羊肉也不吃,但最近都一一破戒,看透了,凡事怎由人控制得來?
「這是我懂事以來最大的大事,後生時,覺得世界美好,七、八十年代,距離戰爭已遙遠。晃眼幾十載,餘生很貴,來日不長。進入倒數階段,做自己想做的事便好。發夢都估唔到……正因吸取過沙士經驗,沙士只學校停一陣課,今次就大家home office甚至乾脆失業。我像一副engine,撻着不能停。每天facebook send來種種傳聞,作為廣播人,我首先想到fact check──飲25公升水真能預防嗎?原來,讀過書的成熟朋友都驚惶失措,我要冷靜。」
農曆年初三,鄭丹瑞和波友蕭潮順、羅燦等踢完足球,一看門口通告,跑馬地場地宣告封閉,今後無得玩。鄭丹瑞說:「唔得,我們點都要做啲嘢。」蕭潮順是監製,說:「好吖,你主持,我出crew。」羅燦現職搞大數據,說:「要做就要有紀律,每日出片上YouTube。」
還有要快。沒試過這玩法,阿旦坦言到現在斗零酬勞未收,待點擊達標才有望廣告分賬。「等call齊sponsor才拍?便不會三日就開鏡,隔周就出街啦。真不能計較太多。
「一看醫生名單,例如許樹昌,不乏我聖保羅師弟們。其他嘉賓,更加一呼百應,如果我借力他們去剪綵開舖,一定無咁齊心,我亦慶幸以前沒濫用人情卡。
「我不是『大家唱首歌先』那種,有人唱,唔重要,佢用佢方法,我用我的know how。KOL話:『使乜咁辛苦?你棟部機自己talk就得。』其實我唔識做KOL,要我做就這樣做──訪問、求證、保健繼而介紹做運動。每周一至兩日幾乎full day拍,一小時剪剩兩條10分鐘。是我廣播人責任。」
健康的旦
節目名順手拈來《健康旦》,鄭丹瑞自嘲:「同我瀨過嘢有關嘛。當年成日捱夜,食無定時,患上胃酸倒流,不能打平瞓,要45度斜挨着睡。狀態極差之下,去和梅小惠拍碧桂園廣告,扮跑步,跑了一天,奇怪,返酒店反而睡得好好。於是我知道,最緊要運動。後來我開工作室,每朝和朋友踢完波沖完涼,好整以暇等編劇們返工,編劇晏起床嘛,十二至六度橋,那幾粒鐘連廁所都少去,重質不重量,傍晚我便回家吃飯,10點一定瞓,第二朝又一早去踢波,如是者才養好身體。我是過來人,夠資格講吧。」
另一半,應該關形象健康事。初戀情人就係老婆──有點似某婦科病宣傳片,究竟神話抑或遺憾?尤其作為擅長愛情題材者,驀然回首,算否白過了?
「所以我叫陳慶嘉寫《小男人週記》我演,每個男人都有得不到的夢中情人。播得歌多,知道什麼叫saving all my love。我慶幸自己在03年,50歲仍拍得出《六樓後座》。愛情之於我,像《恐怖醫學》,睇症睇得多,仲敢亂試咩?
「電影是我情人,不用賺大錢,近年連攞香港金像獎導演的都比我年輕得多了。我喜歡Woody Allen,運用自己方式表達吓啫。」

有名無利
這句可圈可點了。鄭丹瑞out咗未?他不是應該退休了嗎?如果留在港台轉職公務員,夠期攞長俸。如果留在商台,「位高權重,出門口有司機。朋友話齋:『俞琤之後到你啦。』但我坐唔定,我計過,由做麗的開始,每份工不超過六年,直至自己開公司。我不迷命理,但睇相佬個個都批得準我呢世人有名無利。
「今時今日說退休,不實際。退休第一件事係搵新工作。做創作呢行,年輕時無人信,到終於有了些江湖地位,同一條橋,說服力會大咗。例如《分手一百次》條橋,我曾敲遍各大電影公司門,累積一定年資,人家才認真考慮。就算無人要亦唔緊要,我可以自己拍。我不以年紀大為負累,反而以它為資本,以前做不到的,現在再提煉,或給機會年輕人。
「我的工作從不離開年輕人。我的編劇們,多數IVE畢業就跟我,寫稿錯別字連篇,但他們有的,我沒有。《分手一百次》結局那場戲,行內無人敢咁處理──鄭伊健每次過馬路都拖着周秀娜,終於最後一次,不拖,便交代了分手,好淡淡然地慘。我一個小女孩諗的,我度不出來。要相信新一代。」

沒有中產
但無論如何,新一代生不逢時,不及他那輩幸運。
「係。」阿旦衝口而答。
鄭丹瑞1978年畢業於浸會傳理系,當時很潮的一科,至今收生成績高企,卻眾所周知,出來做記者、廣告或影視製作都今非昔比。中產不再,阿旦本人及他飾演的小男人阿寬從事廣告界乃至Woody Allen,正正曾經是中產代表。
「五、六十年代,大家攞住飯壺返工,沒品味享樂可言,只求生存。到七、八十年代,變身國際都市,賣東西不只一味『平霸啦』,要brand building,於是帶旺廣告公司,由攞住飯壺到打條呔返中環,型咗喎。我心目中的中產,就係型,不用諗得太複雜。
「世界繼續變,越來越兩極化,貧或富,漸漸沒中產立足之地。以廣告為例,不再需要精緻,目標為本,要有就得,於是像倒退回『平霸啦』。我是否落伍了?我唔識,但仍能學,每一年代自會發明突圍方法。
「我們以前,加入大機構,由低做起,但現在,畢業生找不到長工,我便不講『只要肯捱唔好怕蝕底』之類的勸勉了,太老氣橫秋,太廉價,年輕人想專心效忠都難。又或者,我們愛瓣數多多,總帶點關連,例如DJ去拍電影;現在的Slash斜槓族,乾脆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憐憫他們撈散炒散,卻可能這是他們主流呢,他們樂在其中殺出新血路也說不定。
「我唯一能講無錯的是:『做囉。我幾十歲仲做,何況你們後生?』怎敢說教人?我去訓練班,我帶給他們經驗,他們帶給我energy,我還賺了學費。」
後 記
訪問中,鄭丹瑞提及替商台客串《有誰共鳴》,即是八段獨白串起八首歌,典型電台玩法,駕輕就熟。他說,錄完,思前想後,成晚囉囉攣,自愧欠水準,致電叫商台hold住,今天忍不住借老友蕭潮順的studio補飛。
「我反而這科最衰唔得,本行呀,播音人呀。應該度定草稿的。」
筆者以為他講吓,但拍照等set燈時,見他拿紙筆填呀填,果然在逐句斟酌。我卻還是不感冒,覺得扮嘢──就算真心不是扮嘢,後生仔都會認為你扮給他們看呀,太廉價,等如「唔好怕蝕底」那套,嘥氣。
鄭丹瑞說:「我並非要教大家甚麼,係唔這樣做的話,我根本撈唔到落去。」
聽得筆者悚然一驚,感同身受。年紀大,記性差,我何嘗不是由初出茅廬打天才波,到近年越寫越慢?沒啥誇口,亦沒啥慨嘆。
本篇,還是起草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