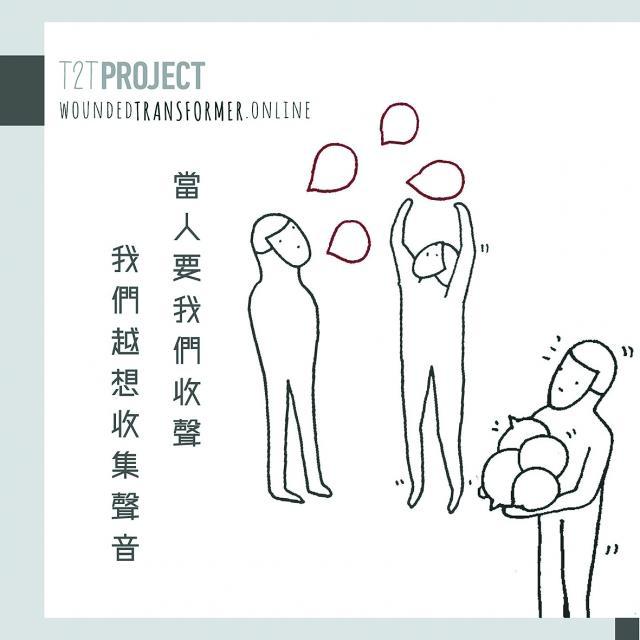
憤怒、悲痛、驚慌、失望,超過七個月抗爭,香港人心情經歷無限次高低輪迴,政府繼續裝聾扮啞,警謊一再遮掩真相。去年11月,一個名為「創傷同學會」的組織成立,提供免費網上情緒支援,有別於尋找心理醫生一對一的輔導,他們更想壯大同路人互相治癒的能力。
創辦人之一曹文傑(小曹)在中大任職性別研究課程講師,他看見情緒與政治的關係,發現一旦抗爭者身心透支,自然會退出運動,「獨裁體制最常用威嚇手段,另一手段係用恐懼,你麻木自己,有咩好得過班人自己放棄自己,佢覺得自己冇路行就自己會熄滅」。
記者:陳詠恩
攝影:董立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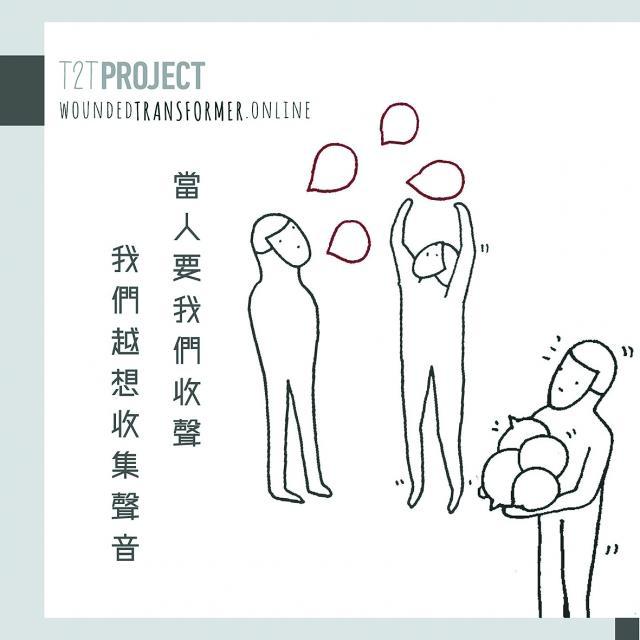


免費線上課程 盡訴心中情
創傷同學會的英文名字是From Trauma to Transformation(由創傷到轉化),初時他們拍攝了多條短片,由關注情緒健康的插畫家「含蓄」畫了一套動畫,呈現面無表情的白色人兒經歷催淚彈放題到勇武抗爭,請獨立唱作組合My Little Airport的主音Nicole旁白,反問「個世界係咪癲咗」。他們還訪問了社運人士周諾恆、何潔泓等被捕過來人,分享被捕須知及情緒變化,引起網民討論。
同學會成員有前傳媒人、心理治療專家、插畫師、製作人等,當中還包含由「非暴力溝通」實踐者池衍昌(阿池)和小曹。非暴力溝通聽來陌生,其實是一種對話方式,不用抱怨、對別人指摘或攻擊對方來回應對方。
他們早前開辦多場免費線上課程,由阿池和小曹作「聲音導航」,例如早前的「和你聆聽」班,有十多人參與,先邀請其中一位學員分享心情,其後再以分組討論對談,聆聽別人同時抒發心情。臨近農曆新年,他們推出「非同溫層對話」工作坊,分享與政見不同的親友談話如何不被「撻着」,撻着了又如何撲火,相當實用。
過程中,學員可以自行選擇開咪、開鏡頭與否,或只用文字發言,確保私隱。另一位創辦人兼《Breakazine》雜誌前總編李玉霞(山地)說,她曾收過有人來訊詢問如何以短訊方式開解戰友,由於前線抗爭者為保障個人資料,以往習慣以短訊聯絡,線上課程正好派得上用場。「非暴力溝通強調成班人一齊做,多於一對一輔導。線上就係一個群體,就算匿名都可以一班人傾到。」
儘管創傷同學會有臨床心理學家,不過小曹提醒,每人都有關心和聆聽別人的能力,課程只是重現這種能力,「我哋有專業人士當然重要,但我哋照顧另一個人嘅心,唔一定要讀一個PhD或專業證明先做到」。

出現集體創傷 港人不孤獨
香港人經歷過6.12、7.21、8.31、10.1等數之不盡的血色日子,越來越多人關注心理創傷議題。1月10日,港大研究於醫學期刊《刺針》發表報告,指去年9至11月調查發現有31.6%的香港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症狀,研究人員認為稱相關患病率與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相似。
小曹指出,創傷壓力的光譜廣闊,PTSD是其中一種嚴重情況,「另外大部份人唔係完全冇事,都有壓力,但日常生活中朋友學過某啲技巧都可回應到」,他認為若將所有情緒都交予專業人士,也是自我削權,亦沒理由上街、看新聞都要請心理治療師陪伴左右,學會照顧他人和自己的技巧才能走遠路。但若然情況嚴重者,他們還是會協助轉介予心理治療師。阿池補充,他們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集體情緒支援的力量,「創傷就係減弱緊我哋應付處境嘅能力,例如物理上我哋起唔到身,冇精力集中唔到精神,或者個事件仲縈擾住我,我好嬲好驚等,仲好易諗返嗰啲事」。
小曹說解釋,「好多社群都經歷過呢種集體創傷,香港人並不孤獨」。他指,創傷同學會的非暴力溝通主張來自美國社運學者Joanna Macy,Joanna Macy在七、八十年代與志同道合者一同反核,甚至用身體阻擋核電廠興建卻不果,她身邊的同伴一個個透支,甚至有人自殺,她便開始研究美國原住民在18世紀時,遭受到外界入侵、被騙去土地權後,族群如何自我開解,漸漸演化出她自己的非暴力溝通方式,讓人走下去。

強權下被打成broken glass
聽小曹、阿池與山地三人冷靜地談着創傷,其實在此之前,他們也曾親睹各種的痛。
時間回撥到去年11月,理大被警方催淚彈圍攻,小曹以中大教師身份與同事進入理大,當時他陪同三位留守者步向警方哨站離開,有人問對方「其實你叫咩名」,「我問佢哋本身唔識㗎咩?佢哋話『識,但喺入面唔知邊個係鬼』,因為好多謠傳,都幾sure有警察入咗去,雖然佢哋(留守者)合作但高度警覺,呢種感覺得讓人好唔舒服,去到真係等被捕個刻先可放下面具,嗰種隔膜好觸動我」。
小曹憶述理大一條被戰火蹂躪的樓梯上,有留守者向正欲離開的中學生高聲質問「唔係齊上齊落咩?」他看見有兩個黑衣人不斷行走、茫然地拐圈,有人打電話跟家人談判,有一批人討論如何攻出去,有人責罵曾鈺成「點解唔make個好啲嘅deal,爭取多啲人冇事?」飯堂有人獨自手執正充電的手機發呆,「我哋入到去已感受到嗰種絕望,原來絕望係聞得到㗎。我感受到運動中嘅情緒好重要,好左右到你行唔行到落去」。這種無力感令他想起傘後情緒,發現一旦無法走出情緒低谷,會令人漸漸想放棄、不再抗爭,但這正中獨裁體制下懷,故此必須憑群體力量互相扶持。
山地早前訪問了數位反送中運動的受襲人士,包括7.21元朗恐襲中,被白衣人在街上襲擊的一位廚師,「佢同我講,『我被打過,同你哋經歷唔同,你可能覺得唔開心就唔睇(新聞),我唔可以唔睇,或者我冇法唔記得』。我聽到個心幾痛,佢究竟可以點處理,真係創傷」。這種椎心刺骨的創傷,令她回想2013年為《Breakazine》曾做關於創傷的專題報道,當時她為尋找六四後歷史創傷,先後到訪柬埔寨、台灣等受極權摧毀的國家,探討人們如何處理歷史傷口。
柬埔寨在1976至79年三年間經歷了「紅色高棉大屠殺」,每當山地向當地人問及此事,他們都會無法自已,流淚滿面,其中一人告訴她,「佢話『我哋呢代都係broken glass,唔能夠contain到自己』,當時我唔明,點解係broken glass。佢答『因為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同埋係強權底下被人打,係好深傷痛』」直至8月回港,她再跟香港人訪問,擔心香港會好像台灣、柬埔寨那樣,覺得香港需要處理此歷史傷口,甚至兩代人都要面對。
集體傷口能否療癒尚未可知,不過多少紓解了手足的心情。山地說,曾有前線抗爭者參與線上討論中訴說心聲,因為現實中要保障手足私隱,「發夢」過程無法向人傾訴,難得在創傷同學會中可以說出來,山地沒透露內容,只道這位前線抗爭者說感覺舒服很多。另一位參加者Jackie接受記者電話訪問,她自言情緒未算太受困擾,但身邊有朋友走得頗前,「我想裝備自己有技巧聽佢哋講嘢」,她曾上「和你聆聽」線上課程,課堂教人用同理心去聆聽,別急於給建議,多留意對方感受,於分組討論過程中,她傾聽另一位同學的問題後發現自己能幫助同路人,「我聽佢問題已神奇地放鬆咗,面對嘅嘢有少少似,去關注人哋問題,唔會將自己問題放到咁大」。她發現,人與人之間問題很多時是溝通問題,即使是黃、藍絲分歧也沒想像般大,「人類嘅需要好接近,只係無法有效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