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沖廁時,請蓋上廁板,以減少細菌傳播」,武漢肺炎肆虐,防疫成了港人頭號大事,搶口罩、勤洗手,公廁都貼上溫馨提示,人稱「廁所博士」的熊志權,大抵最感觸。2003年沙士掀起一場公共衞生風暴,U型排水口被指成散毒元凶,觸發他與一眾熱心的廁所專家成立「香港廁所協會」,不但自掏腰包參加國際會議,發表涉公廁設施與衞生的學術論文,更親身巡視公廁,查找衞生情況,無懼惡臭公廁「遍地黃金」,選出全港最差/最佳公廁。「皇帝都要去廁所,無論你幾有錢定幾窮,人人都一樣要去方便」。
記者:呂麗嬋
攝影:夏家朗



這天,記者跟隨熊志權突擊檢查中環三個公廁,第一站是位於大會堂停車場公廁,只是,記者來到公廁門外不禁誠惶誠恐:「博士,公廁影嘢怕唔怕㗎?」熊志權面無懼色,見無人出入,即一個箭步趨前,和清潔阿姐打交道,語氣誠懇道明來意,竟暫准清場,成功達陣。「呢個公廁之前封咗半年大維修,開番幾個月,就七個廁格三個壞,剩四格點會唔排長龍吖!清潔阿姐先慘,你睇個電飯煲?仲要喺度開飯,連個位坐都冇」。身處小廁格仍能靈活走位一眼關七,熊志權邊說邊指手劃腳解釋。
「我哋係民間組織,你話巡公廁,好多時唔單止睇男廁,都想睇埋女廁,通常要搵廁所清潔阿叔或阿嬸開路,清咗場先入,不過都試過出現尷尬場面,有次睇睇吓,突然有女士撞入嚟大叫:呢度係女廁,點解有個男人喺度?我立即道歉,解釋只係代表廁所協會,想睇吓啲公廁設施乾唔乾淨」。
預先通知食環署一定執到靚無料到,突擊檢查最反映現實,但要碰運氣,好在大多有驚無險,熊笑說如一開始大興問罪之師的女士,當一聽到「乾唔乾淨」,一秒間便把他視作「冤情大使」,投訴無水沖廁兼好臭:「真係有需要去公廁嘅人,都一定會有意見,只係人有三急冇得揀,先逼於無奈要用,大家都想有要求呀。」「好似鴨寮街公廁,圍封一年翻新,𠵱家改善咗好多,以前尿兜一半用黑色垃圾袋包住唔用得,用得嗰啲又有煙頭同痰,好恐怖」。使用量高到爆燈的鴨寮街公廁,一度位列「最需改善公廁」前列;同樣位於深水埗北河街公廁,一樣「臭名遠播」,「試過去睇,大卷廁紙塞死,糞便滿瀉,放幾嚿磚喺地下就繼續用,真係好核突」。
公廁企理 大家會錫住用
今日疫潮肆虐,防疫專家都呼籲市民保持廁所衞生,包括定時用稀釋漂白水清潔,倒水入排水口免阻塞,更要時刻緊記先蓋好廁板先冲水,凡此種種,只為與糞便保持安全距離。
只是高高在上的官員,能否理解清潔工為慳錢公廁煲飯,以致為何滿地屎,升斗市民仍得硬着頭皮,自製磚頭獨木橋頗成疑問。個別公廁的衞生問題固然極待改善,就是食環署一度計劃全面使用的空氣清新劑,熊志權一樣有意見:「定時噴防臭,只係將原本的臭味蓋過,為何不找出源頭解決佢?呢種化學原料對臭氧層有害,糞便阿摩尼亞,再加清新劑係好怪味,做好空氣過濾先係治本。」
那些年理大畢業即投身水務工程且一做半世紀,做過水務署然後自立門戶,熊謂由渠道結構到爆糞渠緊急維修,都是他的工作,見慣大場面,無畏無懼「遍地黃金」。
熊志權表示,一般人去公廁速戰速決,但公廁水平高低,其實亦有認可標準,包括舒適、暢通、安全和衞生,英文簡稱就是CASH,符合四大要求,等於位列廁所米芝蓮:「有樣嘢好得意,如果個廁所乾淨企理,使用嘅人基本上係唔忍心整污糟佢,但當好污糟,唔想用但被迫用,就會快用,連沖廁都唔想,係惡性循環,亦好人性,如青嶼幹線嘅公廁就係最好例子,大部份用都是國內同胞,佢哋對公共衞生概念比較差,但你以為一定好污糟咩,原來又唔係,協會試過針對來港內地旅客做問卷調查,佢哋都話好滿意,因為唔想整污糟佢,證明如果廁所本身環境好,得人欣賞,正常係唔會想破壞佢。」
好就越好、差就越差,熊志權說如廁習慣往往反映人性,與文化背景有關,自小接受的衞生教育,亦至為關鍵。「喺日本同新加坡,就算係車站嘅廁所,大部份好乾淨,入到去唔覺得係廁所,好似森林,冇臭味,綠化又做得好,用嘅人自小教育係要有公德心,唔好要其他人幫你執手尾」。大扺都是老生常談,但熊說希望香港公廁,有朝一日亦達到這樣的高水平:「𠵱家唔係冇,不過數量係好少,青嶼幹線、大埔林村嘅公廁,好多盆栽,又空氣流通,要多謝負責清潔嘅人用心去維護。好似林村,每個人如廁出嚟,負責清潔的姐姐都會再打開門,睇吓有冇沖水,如果冲得唔乾淨跟手再沖,公廁清潔都係外判,好唔好同管理有關,唔係乜都批評,如果做得好,值得表揚。」


沙士過後 關注公共衞生
在世界各地搜羅古董絕版馬桶廁板,就連到外國公幹旅遊,廁所仍然是他必遊的景點。熊志權自言出身基層,由農村茅廁到七層大廈的「屎坑」,他都曾是用家。「細個父母務農,用嘅係茅廁,顧名思義就係茅草搭建嘅廁所,下面有個氹,去完,排泄物就會咚一聲跌落去,𠵱家睇係幾核突,有時會見到蟲蟲,務農嘅人唔會嘥嘢,用嚟施肥,細個見到唔會識驚」。小孩嘛,最愛屎尿屁,正是這份好奇,讓他投身行業。
「有啲人覺得講屎講尿好核突,但其實係每個人都要面對嘅日常,我唔怕俾人取笑係逐臭之夫,任何行業都係一種專業,好多人叫我廁所博士,我都唔mind」。那些年,以半工讀方式,在仍未升格做大學的理工學院修讀衞生工程,研究排水系統,其後進修至博士,對於與生活密不可分的廁所,由設計到衞生,他一直事事關心。但觸發他與一眾專家成立「香港廁所協會」的,卻是造成近300死的沙士,那些年,淘大花園是重災區,居民強制隔離,亦因疫情揭露本港大廈排水系統弊端。
「03年沙士係好恐怖,恐怖在每日都有人死,好多人連握手都驚」,那些年,他與世衞人員一齊到淘大花園實地調查,那種瀰漫在空氣中,濃得化不開的集體焦慮,就似今天。「E座嘅排水系統結構,到𠵱家仍係我喺大學教學生嘅教材」。疫潮過後,北京剛好舉辦世界廁所高峯會,討論關於公共衞生及廁所的問題,他就自掏腰包出席,在展場遇上當年主力研究公共設計的理大教授邵健偉,以及現時出任協會秘書長的崔妙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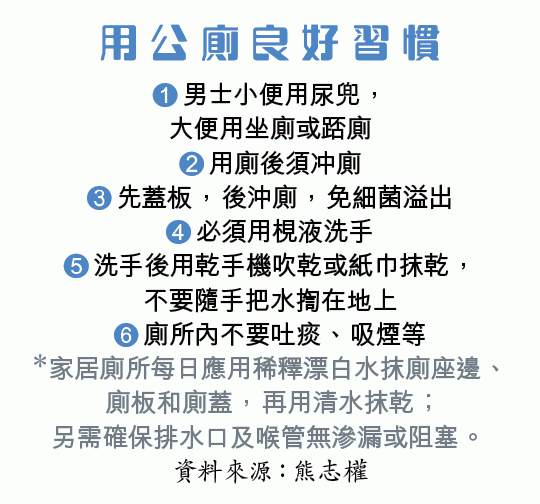
成立協會 各界交流改革
2001年成立、總部設於新加坡的世界廁所組織(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由來自77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會員組成,每年都會在不同地方舉行高峯會。「大家之前完全唔識,傾落先知係香港人,約定回港再聚,當時大家有共同目標,希望成立壓力團體,改善香港公廁形象」。沙士一役,一講廁所公共衞生,就必定涉病菌病毒,有成員認識當時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勞永樂,邀請加入一拍即合,還成為好朋友。
「佢係好有衝勁嘅人,後來仲做埋第二屆廁所協會會長,嗰段時間好多交流改革,𠵱家大部份市區公廁有個清潔阿叔或阿嬸長駐,都係嗰時開始」。協會成員來自五湖四海,既有醫生,又有大學教授和旅遊業界人士,也有如他一樣從事水務工程的專業人士,協會成立之初四出考察,又大搞公廁選舉和調查,引起不少迴響,可惜其後因為勞永樂醫生患癌,群龍無首,協會的運作亦半停頓。
「勞醫生係我哋大佬,有一段時間佢嘅病情起落好大,我哋陪住佢直到佢離開,當時大家都好唔開心,個會沉寂咗好耐,直至近呢一兩年,大家聚埋話不如做番啲嘢,改善公廁衞生一直都係勞醫生嘅遺志,於是又搵番啲基本成員重組」。物換星移,有人走,也有新成員加入,「有新成員嚟自教育界,提起話細個去公廁,嚇到喊住出番嚟」。這樣的「童年陰影」,熊笑說其實不算太罕有。政府早前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承諾撥款翻新四分之一的公廁,改善情況。
「六億用五年時間翻新240個廁所,即每年要翻新50個廁所,但全港有798個公廁,如全部翻新,需要16年,仲未計翻新完又爛嗰啲,永遠都追唔上」。他苦笑。重組協會後,熊志權說今年的目標是將巡查範圍擴大,希望加設網民評分,增加互動。
此外,他計劃在一年一度的花展設女性尿兜專廁,讓女士試用:「喺歐美,呢種尿兜好普及,尤其大型公眾活動。不過真係要試過先知好唔好,不如我畀個你拎返去試吓」。拿着三角紙尿兜,落力向記者推介,這個達人,何止無廁不歡,簡直充滿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