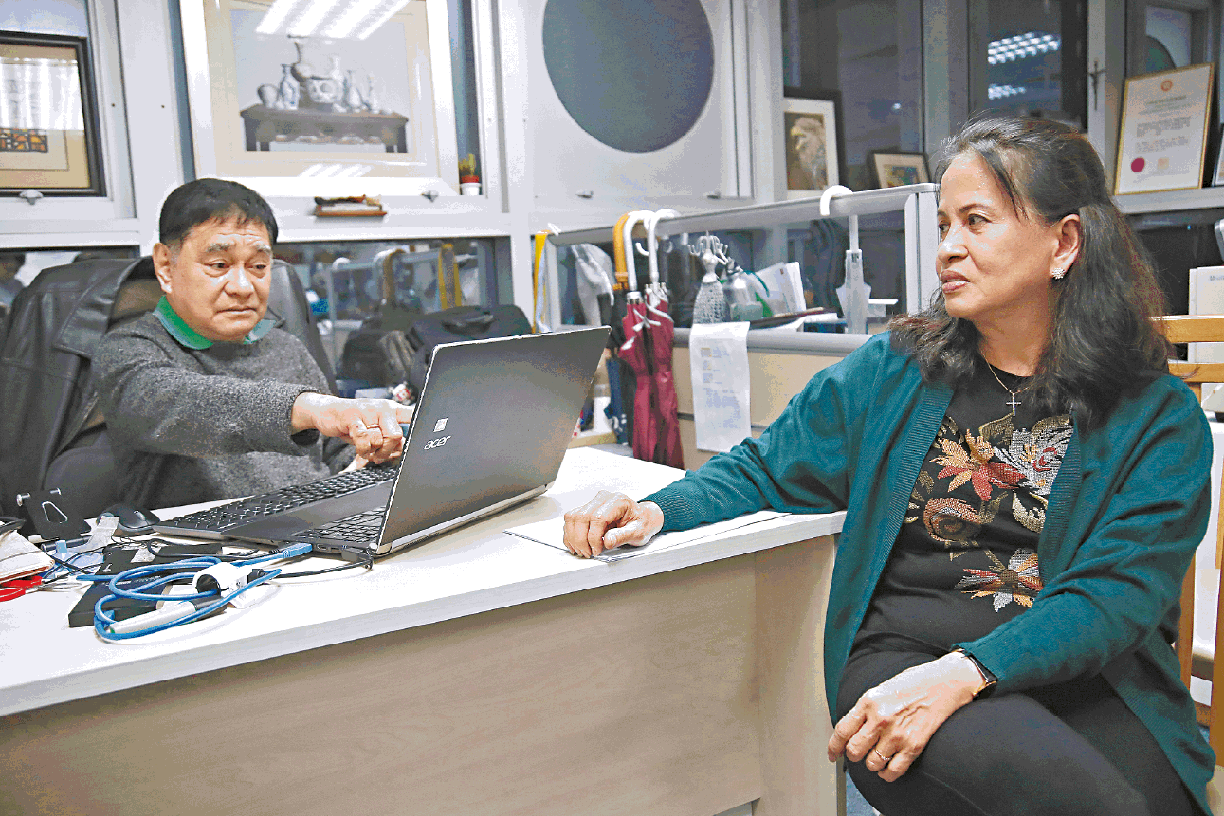
夜幕低垂,《The Sun Hong Kong》這份以菲傭為讀者的雙周報,位於北角的辦公室中,仍然燈火通明。
相比下一代移民融入社區而漸被邊緣化的族裔媒體,移工媒體仍保有活力。25年來,他們鬥志不減,被稱為「第二個領事館」,菲傭遇上難題,總先facebook報料給他們。主編Daisy Mandap與Leo A. Deocadiz是一對夫妻,他們是記者,也是維權者。
屢遇不公義 望為同鄉維權
提到不公義個案,Daisy一口氣說了半個多小時,也大力批評警察無所作為。一宗非法僱傭案中,500名菲傭遭黑心公司詐騙,付錢換取假工作機會,牽涉超過500萬,初初警察不理,Daisy帶同100人到警署,據理力爭,才報案成功,但至今無人被起訴,沒有賠償。警方有次打發眾受害者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她與同事擔任原訴人,一連勝出21宗索償案,審裁處將200宗案件轉回區域法院後,兩年後仍未提堂。有七名菲傭遭黑心中介踢出臨時收容所,流落街頭,夫妻二人甚至收容他們,一同度過新年,還自掏腰包買回程機票……她以印傭Erwiana為例,遭虐後獲判約80萬賠償,至今一毛錢也未收到,「這就是不公義!」
「作為記者,倡議工作不一樣之處在於即使有菲律賓人犯罪也好,不代表我們會用取巧角度掩飾,但若我們看見菲傭被佔便宜,那麼我們就會為他們戰鬥。」
維權基因在她的骨血內,80年代二人任職菲媒報館,Daisy一邊任助理編輯,一邊半工讀取得律師資格。當時攝製部的同事比編採部的薪金少一大截,欲爭取同工同酬,請Daisy成為工會領袖,她一口答應,後來發起長達一年的罷工,遭抹黑成共產黨員,被解僱不止,老闆更索性結束報館。適逢1987年《The Standard》來菲招聘記者,夫妻雙雙獲聘來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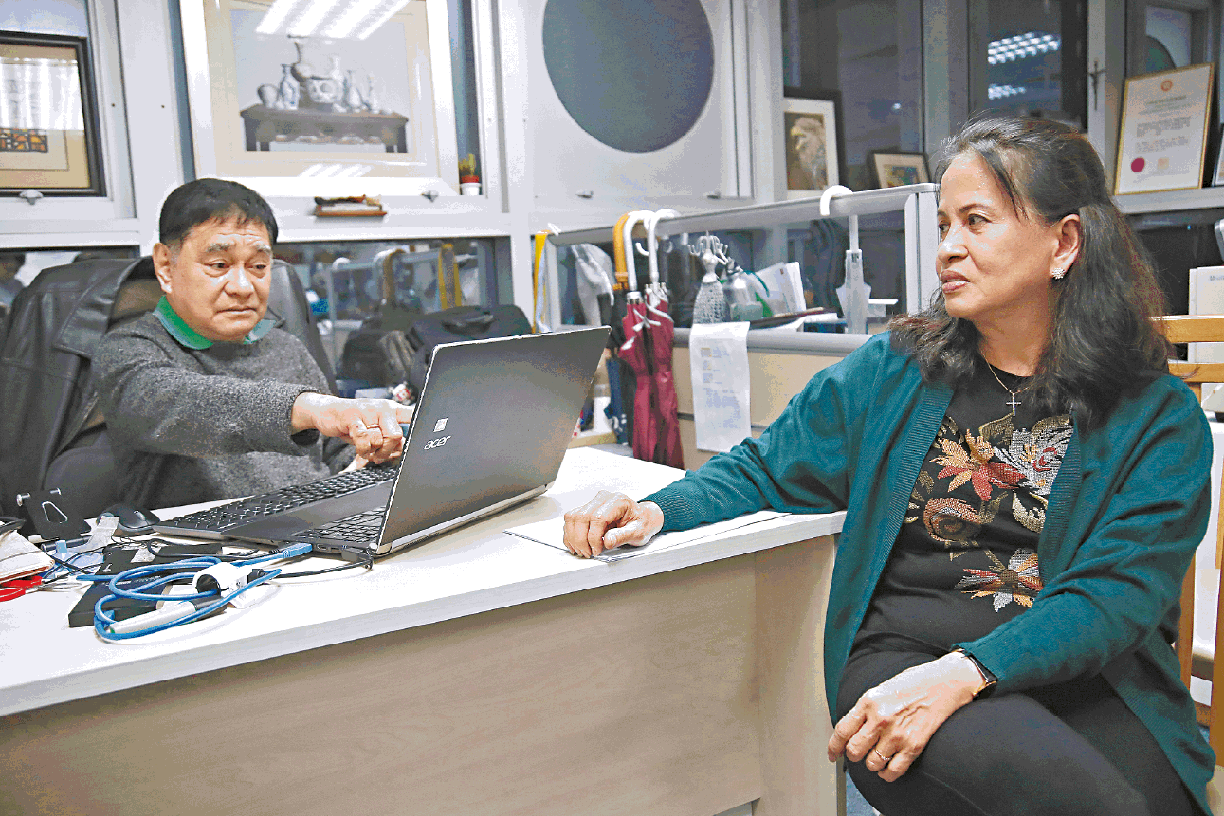
辦報為探討外傭潮問題
1982年,香港尚只有兩萬多名外傭,1995年已攀升至超過15萬人,八成來自菲律賓。
她任職法庭記者的首篇報道,便是外傭挑戰上訴解僱後14天離港的時限,樞密院頒下敗訴判詞。「主流媒體有整個香港公眾去憂慮,所以專注菲律賓社群的考慮就很少。」
夫妻立即意識到,菲傭在香港面對一籃子問題,急需深入報道,菲律賓是世上唯一沒有離婚法的國家、衍生種種家庭問題、外傭潮致菲國教師短缺、非法僱傭等等。
Leo儲夠三萬元,便籌備辦報。1995年12月3日,《The Sun Hong Kong》創刊號出爐,頭版標題為「香港回歸中國 外傭不會遭送回家」,除了港菲兩地的英語及他加祿語新聞,還刊連載小說、廣告,在環球大廈等菲傭聚腳地免費派發,印刷量才一萬。
翌年,印量增加,廣告找上門。2003年沙士,電訊公司在低潮中發現外傭市場,廣告便蜂擁而至,Daisy笑說:「這應是為何超過九成菲傭有電話Plan的原因。」
Daisy則在主流媒體打滾,先後任職亞視及CNN,但晚上回家,夫妻會清空餐桌,便繼續工作,直至1999年Daisy才全職任主編,Leo主理印刷。
人手不足,他們辦了The Sun Writers’Club,舉辦新聞寫作講座,再從中招募義務撰稿人,現時有七位。她把撰稿人派到周日的各項社區活動,採訪領事,鍛煉出一身本領,「給他們自信,這就是(充權)開始」。

着重菲律賓社群資訊
撰稿人寫社區見聞,《The Sun》的專業記者負責嚴肅新聞,依靠菲傭報料。撰稿人Gina舉例,WhatsApp和facebook加起來,也有數十個群組,不少是按鄉下分類。十多萬人中,誰自殺了,誰遭人口販賣,誰遭強姦,靠社區網絡就找到。Daisy必定先轉介個案給領事館,而後續工作盡量交給移工組織:「我們嘗試做到最好,但寫報道本身已經很難,遑論再做其他。」
平日忙於法庭案件,跟進勞工議題,《The Sun》僅有四人,Daisy清楚必須在示威與維持日常報道間作出取捨。因菲律賓人英語程度高,能讀英文媒體,「本地媒體已經廣泛報道(示威)」,Daisy選擇少作報道。《The Sun》僅兩次拍攝示威遊行,如6.16二百萬人大遊行,也會拍攝各自在橋上休憩的菲傭,形容「看似沒注意到(seemingly oblivious)周遭發生的事」。
但《The Sun》會在示威牽涉到菲律賓人時作報道,比方說蒙面法,早前亦專訪在現場遭拘捕的迪士尼菲籍舞蹈員。平日則在facebook轉發菲律賓領事館的抗爭時間表。
不過,示威常突如其來出現,領事館的資訊便過時,撰稿人George Manalansan認為社群需要更新的資訊,《The Sun》有責任,「為了安全理由,我們需要更警戒,但為政治理由,則不必要」。但George不會落場採訪示威,「我們是撰稿人,不是記者」。
望能求存 計劃轉型網媒
領事館曾警告傭工不要接近示威區。如果有人自願落場採訪,Daisy不會阻止,但不鼓勵,「他們其實選擇遠離示威……傭工如在場被捕,非常危險,他們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提到Yuli Riswati辦媒體遭遣返,被打壓,Daisy亦流露無力感,早前《金融時報》編輯被拒入境,「連外國記者會也無能為力。你覺得如果有觸犯簽證條件、後遭遣返的外傭,剛好也批評了政府,(政府)又會在乎(反對聲音)嗎?」
她今年62歲,30年住菲律賓,32年在香港,日子更長,「但他們令你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地方,否則我早就進了政府」。她曾為菲律賓政府擔任顧問,只覺回歸後香港加速中國化,政府職位對不諳中文的人關上大門,然後越來越多消息以中文發放,記者工作要求通曉中英文。
身份上,「我很左右為難(I’m torn),但我的孩子在這裏出生,但內心裝着香港,許多孩子身在國外,但心繫香港去抗爭」。她平靜又無奈:「他們很愛香港,但沒有公平機會。」她還是意難平,選擇全心報道新聞,「本地應該夠(報道)了,應夠人幫忙。至於家傭,又會有多少人願意全力幫他們?」
兩夫妻都已經年逾六十,每晚仍工作到凌晨一兩點才吃飯。臨走前,Daisy在電梯口,還一臉憂心忡忡,說雖然從未虧蝕,但廣告收入下跌,對撰稿人的待遇也差了,還在盤算走向網媒之路。
25年過去了,《The Sun Hong Kong》仍然老馬有火,這個菲律賓第二駐港領事館仍要為自己的社群運轉,繼續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