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一個時代走到盡頭,成為集體回憶是唯一的出路?屹立逾半世紀的「中國冰室」,保留了六十年代「舊香港」的寫照,曾幾何時是多齣港產電影拍攝場地,由《新不了情》、《PTU》、《江湖告急》到《迷離夜》,每一套電影均承載香港回憶,見證港產片的輝煌時代。奈何政府漠視文化保育,冰室最終難逃被時代淘汰的宿命。上月底正式光榮結業,告別五十五載歷史。結業前,迎來最後一位座上客──本地著名電影導演杜琪峯(杜sir),細說自己與冰室的情懷故事。
撰文:余琬瑩 攝影:傅俊偉、梁正平
大隱於街市的明星小店
「中國冰室」起初屹立於旺角上海街422號,至1964年遷至廣東道現址,隱藏於連串深綠鐵皮帳篷街市排檔背後,毫不起眼。每天清晨6時,玻璃櫥窗會擺放新鮮出爐的蛋撻,櫃檯上亦放着報紙寄賣。上世紀流行的「奶水蛋」、「唂咕」及「鴛鴦治」等也可在這兒可尋獲。懷舊的裝潢格局,亦令冰室時空宛如凝結在六十年代,由彩色格仔紙皮石牆、古舊搖晃吊扇、泛黃的閣樓,以至白綠相間的菱格地板,均完整保留了「老香港」味道。
往事只能回味,杜sir與中國冰室的緣份由2003年執導的警匪電影《PTU》說起。凌晨時分,一眾機動部隊成員在樓上雅座吃消夜,利用冰室空間的氣氛,電影營造出一個「蛇竇」的感覺。劇情編排由反黑組警長「肥沙」(林雪飾)失槍後相約PTU警長「展」(任達華飾)談判情節,推起高潮。
重臨冰室,沒改變的裝潢很快勾起愁緒。杜sir憶述當年選擇冰室作拍攝場地,原因是「好多人都鍾意呢間『舊』餐廳,我所講的『舊』係傳統。但𠵱家好多舊餐廳都未必有呢種紙皮石,有啲未必有閣樓。」
「每樣事會有靈魂自然走出來,夾硬係出唔到。」他稱電影靈感源自於小時候,看見警察經常匿藏在茶餐廳一角休息聊天。潛移默化,拍攝時便選擇一個比較鬼祟的位置,故以閣樓的隱蔽,配合周邊紙皮石的襯托,在環境上打造一個壓迫的空間。「適逢2003年,香港警察開始慢慢更換制服。這些傳統PTU的制服是好英式、好型。在一個這樣舊的場景配合舊制服,一個好香港傳統的事,配合年代記憶還有氣氛,有一種過去的感覺。」


茶餐廳不是那一回事
它雖舊,卻揮發着老香港的餘香──人情味。
冰室的興起,可追溯至五十年代二戰結束後,當時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受西方飲食文化影響,中產階層開始流行英國人「歎下午茶」的習慣。當時主要是售賣冷飲、雪糕及沙冰等冷凍輕食。
杜sir笑言:「當時是新的東西,舊一代香港人,生活上面未見過冰,於是產生冰室。你未入已感到少少寒意,在當時有一種吸引力。」
以往的冰室多只持有小食牌照,食品的種類不多,除了售賣飲品外,還會供應三文治、麵包和糕餅等。食物是配襯,去冰室最重要還是杯「茶」。 「一般是奶茶咖啡。最多是柯華田,朱古力對於我小時候來說已是新鮮。吃的東西都是菠蘿包、蛋撻、麥皮,不像現在的多樣化。」
販賣的食品款式單一,看似日常簡單的「飲啖茶,食個包」。那種不提供中餐,主要是西餐的專注,純粹的堅持賦予食物靈魂。
隨時代轉變,冰室於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式微,大部份改領食肆牌照,兼賣粥粉麵飯維持經營。現時以「冰室」名義經營的食肆,以懷舊的裝潢作招徠,運作模式上與茶餐廳無異難以界定分辨。對於這種時代變遷,杜sir嘆言:「現在叫冰室是沒意義的,只是用名字來包裝說是傳統。但一進去未必是傳統,因為已經做不了以前冰室應有的內涵。」
政府活化失靈魂
先保留而後活化,在沒有「法定古蹟」的身份保護下,冰室很可能逃不過重建清拆的命運。過去十年,政府口口聲聲說重視文化保育,但擁有五十五年歷史的中國冰室,卻屬「夾心層」,未被列入歷史評級建築。市建局活化計劃借「保育」口實變成高檔商場的營運模式, 進駐各式樣的復古店販賣情懷,欠缺本土氣息之餘,真正缺乏的是靈魂。
杜sir以普通市民去看保育,他直言:「如果在每一個的時代變遷留一點痕迹,對於香港只有加分。個人喜歡以前香港的一些建築,譬如:皇后碼頭,天星小輪的鐘聲。那些消失是無奈,即使新建也沒有那味道。舊加新,我個人係不認同。以為加咗好靚,實質上對保育係無。我着重一樣嘢,自己形成自己的風格。如果我們太刻意改變,係咪真係改變成為你所想,而又可以保存落嚟?」
談及保育的實踐,兩者之間所涉及的持續發展(經濟)和文物保育元素,當中如何取得平衡是一個重大問題。
「香港每一位市民都盡力去保留,政府有責任……不只是中國冰室,這類私人經營,保存不夠好,慢慢開始陳舊。陳舊之後,變成消失的原因之一。」中國冰室現為一例,其餘數之不盡,牽涉複雜的業權問題成保育最大阻力,除了靠民間團體奮力爭取和市民的自覺,保育的主導權和責任仍然屬於政府。最真實的保育是盡量保留而非改變,新舊交替顯得突兀,深層意義是失去舊時的靈魂氣息。正如杜sir所言:「大家來到這裏是否可以享受這份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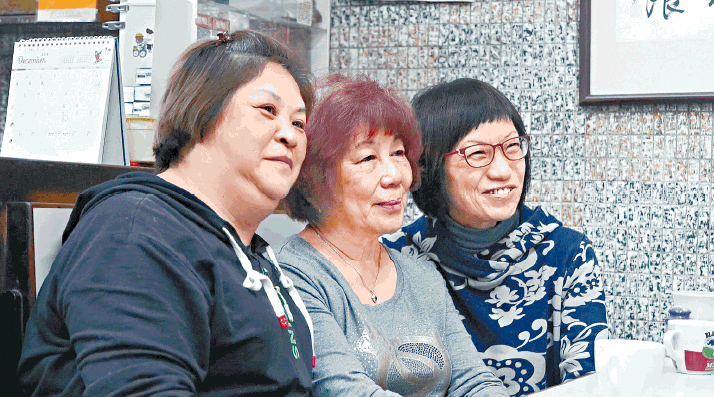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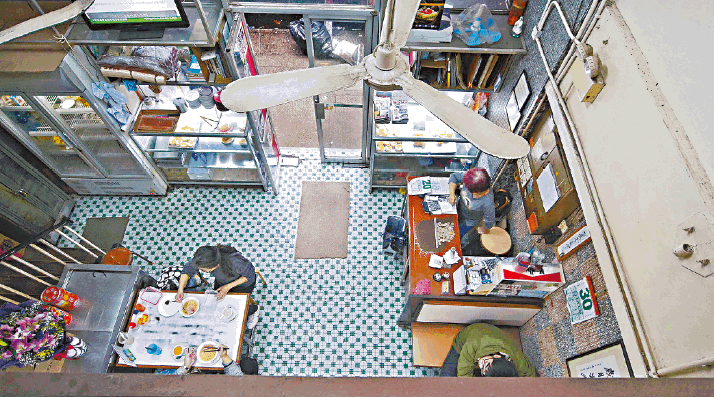
用光影傳遞記憶
「電影的責任和特色是將真真正正的事情,用肉眼就可看到,當時是原汁原味(來記載)。對劃時代的記憶,有責任帶給未來的觀眾……從很多電影看回香港很多轉變。就如電影《七十二家房客》,當中的居住問題,直至今天仍沒有改變。現在都是板間房,同以前沒有分別,這是很遲鈍。」杜sir的電影出現不少舊餐廳場景,也有旅客到香港追尋這些拍攝地。有些觀眾以往在畫面看到,形成情意結,有幸親身體驗,不同人對過去的事作出一些探索,有些會取回痕迹,過程中是跨文化的傳遞。



逝之可惜
「歲月留痕,茶香景緻」是中國冰室一幅字畫,訴說五十五載的情愫。
光顧廿多年的C姐感不捨說:「以後沒有地方『飲茶』,平時6點來食早餐,7點去返工,放工有時到這裏聚會。這裏不趕客,光顧的都是老街坊。以前還會自家製麵包,現在都沒有了。華哥(任達華)都是熟客仔經常見到。」問道現實中,冰室跟《PTU》一樣是警察「蛇竇」,C小姐透露:「以前真是見過軍裝警察在冰室用膳,匿埋一角。」
保育是一種文化傳承,意義在於讓下一代得到認知。假如讓你去保育中國冰室?食客鄭先生表示會將冰室變成展覽館作非牟利用途,「從冰室引伸去認識一個社區,附近環境相關的發展變化,附近居民的文化,多年來的角色位置。」
對於中國冰室終選擇結業,鄭先生感到可惜,「香港人對於時代產物有一種希望保留的心態。如果單靠市民能力相當有限。政府要掌握一個平衡點。」
下午3時,中國冰室拉閘。
若然,無法避免陳舊。逝之可惜,但歷史終須告別,或許走到時代的盡頭成為集體回憶,是另一種最美的保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