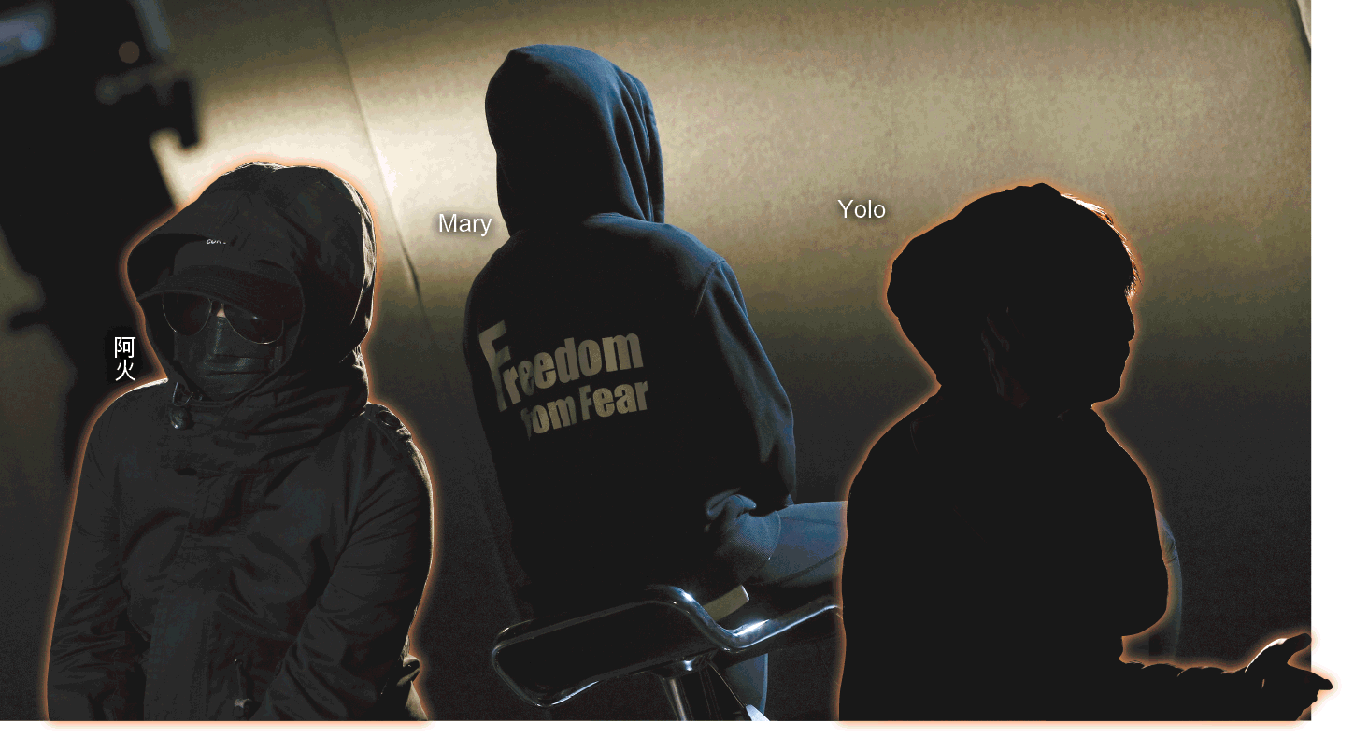
【陰影猶在】各大專院校本月陸續復課,曾經淪為戰場的中大與理大,雖然烽煙消散,但對於目擊整件事及被圍困學生而言,陰影恐怕伴隨餘生。學生與外來增援的手足亦有不少磨擦,割席與否,他們都有不同看法。一個多月過去,冷靜下來後,是時候反思手足之間的矛盾。他們重新踏進傷痕纍纍的校園,草木牆垣縱能修復,但心裏的痛、精神的壓抑,卻是永不能磨滅。
記者:梁嘉麗
攝影:馬泉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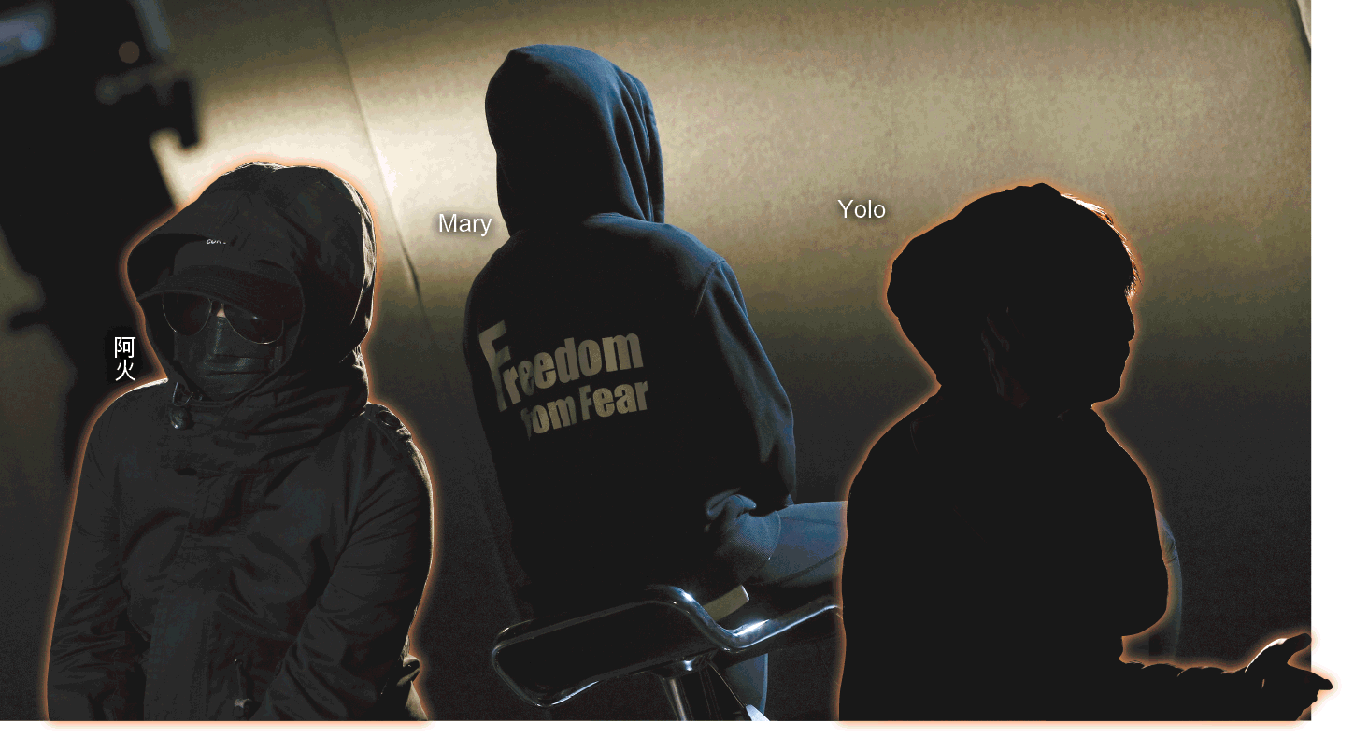
理大女生:「分化」過後 手足依然互助
阿火在理工大學被困時,嘗試用陸路離開,她跟着手足走到草叢旁,正想爬過草叢跨越路軌時,迎面而來的卻是一道強光,有人大叫附近有防暴警,她立即回頭,拔足狂奔,重回理大時,她舒一口氣,卻立即感到絕望,經已四天了,根本無法離開。
「防暴根本唔會畀我哋安全離開,而係想拉晒我哋。」
那天聽到理大被警方圍攻,阿火連忙從宿舍帶來食水、乾糧、杯麵,她不是第一天帶物資入校園了,之前幾天來去自如,「我帶啲物資入去畀同學,支持吓佢哋,我係做後勤,幫手清潔同煮嘢食」。星期日傍晚,她抱着一些食物,走進理大校園,卻沒料到自己未來五天會被困校內,成為被圍困、被射擊的對象。
在理工度過了三個年頭,對學校的一切早已非常熟悉,阿火從沒想過自己的大學竟會成為戰場,她還記那個晚上,正在食堂內清潔時,傳來學校已完全被警方包圍的消息,若不在10時前離開,所有校內人士都會被控暴動,「睇住朋友走,點知出咗馬路唔夠10分鐘,就被防暴直接拘捕,佢哋根本唔會畀我哋安全離開,而係想拉晒我哋」。
第二天早上,校內不時傳來叫聲:「有冇Poly人啊?」幾十人當中,只有一、兩人跑出來。她不知道當時有多少理大學生在校園內,亦無意如此劃分;到了第三天,再沒有人找理大學生了,大家都已了解學校的地理環境,一些甚至連理大生也未必知道的地方,他們都探索過。
在大樓的牆身,寫着「各位手足:今次Poly準備不足,帶到好多麻煩,對唔住,辛苦大家」的字句,圍城前幾天,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事件,有前線趕到理大增援,最後卻與理大學生不歡而散。據阿火所知,理大學生會的同學在處理物資和分配崗位工作上,做了「大台」,亦有「捉鬼」的情況,「係有出現分化嘅,現場亦有爭執,但最後經過討論,理大學生冇繼續主導,所以牆上先出咗呢啲講對唔住嘅字」。
即使自己是理大學生,幾天的圍城戰中,阿火根本不覺得自己是大台,「大家都係同一信念,被困喺同一個地方」,在人群中,她無法分辨哪些是同學。到了後來,她跟不認識的手足,試着以各種方式離開,「無論係入嚟探同學、溫書,定係入嚟幫手嘅前線,都係同一目標,雖然被困,但人同人之間嘅互助令我感到溫暖」。
「咁樣包圍學校,真係好唔人道,製造白色恐怖……」
玻璃被打破、圖書館滿地積水、A Core被焚燒、牆壁被塗鴉,阿火把死物與人命分得很開,物件被漽,與被困人士的情緒壓抑,兩者根本無可比擬。圖書館的玻璃窗被漽,因在圍困第二天早上他們想從紅磡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離開,卻受到防暴警從高處對準學生頭部射催淚彈,他們瘋狂逃命打爆玻璃窗爬入圖書館,多少人被打傷滴着血跑回理大、在爬入圖書館時被玻璃割傷,她覺得校園死物總有被修復的一天,但人命和傷痕卻是一輩子的事。
「咁多人被困,心靈創傷真係好大,喺裏面幾日真係好崩潰,外面嘅提供路線,但唔明裏面情況,行到中途已有警方佈防,佢哋仲要喺外面播歌,皮肉之傷都算,更想我哋心靈受創」。外界以為理大校園變成頹垣敗瓦,阿火說其實沒有那麼嚴重,例如有同學會在圖書館貼上字條,說珍惜書籍,又或在賽馬會創新大樓外貼不要塗污的字條,「因為大家都知道大樓係已故建築大師Zaha Hadid嘅遺作,所以都唔會去破壞,我哋都好感謝所有手足嘅愛護」。
個多月前還是天天上課的地方,今天卻是夢魘中揮之不去的場景,問她會否害怕返校上課,她目光放空了,良久,才能說出話來,「咁樣包圍學校,真係好唔人道,製造白色恐怖,太過火喇,我哋唔會忘記!」
中大男孩:記得絕望中 糯米雞的美味
香港人不能忘記的事,實在太多。理大圍城的前幾天,激戰就在中文大學發生,催淚彈於運動場從天而降、學生以圓桌抵擋子彈的場面,任何人都沒法忘記,今年9月才成為中文大學學生的Yolo,對校園已有強烈歸屬感,「中大係屬於我哋嘅,警察唔應該入嚟,呢度係一個和平安靜嘅地方,我要趕佢哋走」。他率性,甚至帶點莽撞,「保衞中大」四字在訪問中不斷出現,幾天留守校園出於赤子之心,對於中大人與非中大人的合作與磨擦,他亦有自己的看法。同學被防暴警按在地上動彈不得,催淚彈在身邊橫飛,當時他身上沒任何裝備,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同學被捉上警車。
「冇意義又傷害校園嘅行為,我覺得冇必要。」
那天晚上,校外手足來到中大增援,他們坐在運動場內,那時候物資相當短缺,他們啃着同一塊麵包,喝着同一支水,入夜後,有校友送來熱騰騰的糯米雞,「大家都食到差啲喊,點解可以咁好食,嗰種味道我都仲記得」。在同一個星空下,Yolo一夜無眠,時刻戒備害怕防暴警突襲,他問那個坐在身旁全副裝備的男生是哪間大學,男孩聲音青澀,竟是一個中五男生,Yolo非常感動,中學生竟遠道而來幫忙,他心存感激。但後來發生的事,卻讓他耿耿於懷。
經歷兩天激戰,第三天的中大雖在和平中度過,卻偶爾傳來有人塗污校巴、在校內開小型卡車等事,「點解要喺校巴上噴漆、喺運動場內開小型卡車?如果為咗逃生我覺得絕對冇問題,但如果冇效益,破壞就冇意義」。兩日之間,Yolo由感激變成疑惑,但以中大學生身份說出這番話,難道不怕被人說「割席」嗎?不是說好了「不分化、不篤灰」嗎?他深知自己的想法也許跟一般人不同,對「手足」的概念亦有自己的原則,認為在校園內吸煙、高速開車差點撞倒人,甚至破壞校園並非為鼓舞士氣或支援大家,「唔可以因為係手足而合理化所有舉動,例如第一日因為阻擋防暴入校,有手足鋸樹做路障,我覺得絕對冇問題」。即使被人罵割席,Yolo覺得有些原則還是要堅守的,「不割席唔應該被濫用,對準手足我一定不割,但冇意義又傷害校園嘅行為,我就覺得冇必要」。
「呢個山頭唔只係死物,係培育一代又一代學生嘅地方。」
在中大度過三個年頭的Mary,對校園的感情更深,當天前線有中大同學,亦有不少外援,防暴從二號橋硬闖學校時,大家一起兵來將擋,沒大台亦無人指揮,大家只是盡自己能力保衞這個地方。「我遇到一個中學生,佢話想入嚟中大讀,所以入嚟幫手」,由初時共同奮勇抗敵,到後來跟入校支援的手足意見漸見分歧,她覺得因為中大這個地方的意義,對每個人都有所不同。
也許不應把前線分為中大人或非中大人,大家有着同樣的目標,就是手足,但似乎這場陣地戰引起的分歧,正因目標不一致。「呢個地方對你嚟講有咩意義?站在抗爭大業上,外面嚟嘅手足認為可以從中大堵塞吐露港公路,地理位置有戰略價值,但中大師生、校友就會覺得呢個山頭唔只係死物,係培育一代又一代學生、係生活嘅地方。」關於大台問題,Mary憶述當時中大同學想做大台亦不能,因二號橋和四條柱的控制權早就落在入校增援的手足手上。但這種分歧,不只出現於中大或理大兩場陣地戰中,「打仗冇指揮,就算前線自己都會嗌交,退唔退,幾時退,次次都有分歧,小隊都傾向各自行動」,陣地戰再次凸顯意見分化的問題,即使經歷了半年抗爭,但這仍是難以解決的,意見不合時有發生,每次經驗都有討論空間,一句「不割席」實在沒法迴避當中的矛盾。
快將開學,對於Mary來說,再次踏足運動場和二號橋一帶,心裏猶有餘悸,催淚彈從天而降的影像不斷在腦內重演,彈藥的氣味彷彿從未散去,回憶一再被勾起,同學們滿身鮮血被抬進體育館的情境,更是永遠烙印於心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