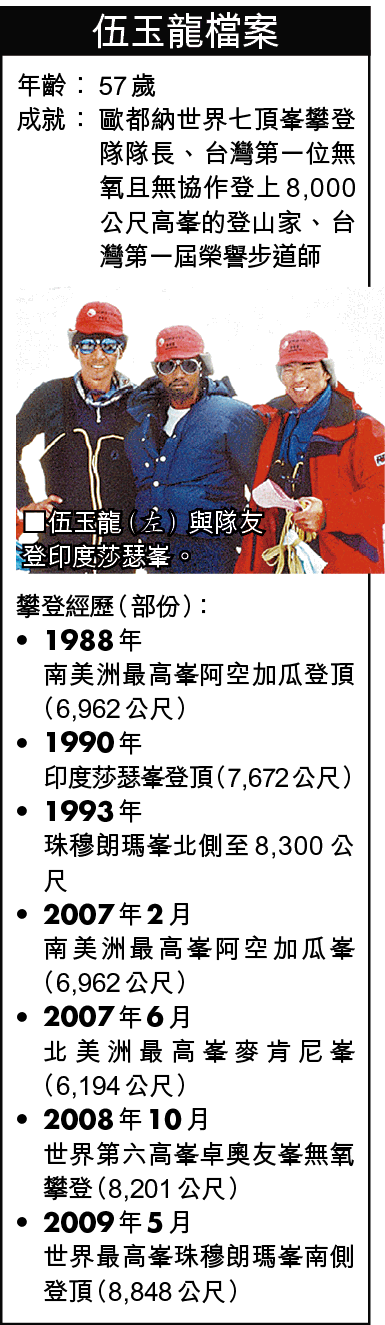北台灣被沙塵暴侵襲的那天,玉山天氣晴。
早晨7點半,一輛載滿細沙、鋼架的貨車停在塔塔加的玉山登山口前,伍玉龍下了貨車,卸下車上的磅秤,候在一旁的幾位背工圍了過來,幫忙秤出幾包70公斤重的沙,然後各自將麻袋綁在鋁架上,鋁架上肩,就往步道邁去,目標是1.7公里外的孟祿亭,那裏有工程需要這些建材。
伍玉龍自己也背了70公斤的沙子,「我沒做事就吃不下飯。」他搶在「當老闆也要這麼辛苦?」這個問題前,先給了我答案。我們跟在他身後,走在一人寬的步道上,沒多久就氣喘吁吁,難以想像已過半百的他怎麼背得動跟他一樣重的行囊,在這海拔將近3,000公尺的地方。但是他說:「我以前甚至可以背體重二、三倍的重物呢!現在老了,老了……。」
撰文︰楊語芸
攝影︰賴文忠
(部份圖片由歐都納Atunas、伍玉龍提供)
老了嗎?我在網路上看過伍玉龍年輕時的照片,除了多些白髮外,現在的樣子和年輕時沒太多差別,當年是少年老成,現在反而有種風霜後顯露的純真。因為是山的孩子,講到山時眼神會發光,就像孩子聊到母親一樣。
許多登山家都說,登山「就像」回家;對伍玉龍而言,登山「就是」回家。身為台灣東埔的布農族,山在伍玉龍的手裏、腳底、呼吸裏。國小三年級起,他就不時跟着同學爬玉山。「我們帶着兩餐乾糧就出發了,對我們來說,玉山就是後院。」國中時每天得4點起床,因為到學校要步行8公里,路上還得經過兩段斷崖。
背下山遺體超過60具
第一次當背工是14歲,「當時被同村的伍萬生(綽號山羊的布農族背工,論輩份是伍玉龍的堂叔)騙了,說帶我們去花蓮玩」,奇萊東稜走了八天到花蓮,一天工資280元。「騙」這個字,我聽來不像抱怨。因為第一次去花蓮、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領到白花花的一叠鈔票,都是跟着前輩當背工而來,半世紀後再回想第一次,伍玉龍有種「被騙也甘心」的表情。
那是70年代的盛世,台灣經濟景氣大好,登山者眾,需要的背工自然多,整個東埔的青壯年靠着頭帶把山背在肩上,背出了布農族的另類經濟。因為需工甚多,伍萬生才會把腦筋動到不過十來歲的國中生頭上。在那之後,伍玉龍的履歷越寫越長,除了背工外,他還做過高山嚮導、山難搜救、巡山員、步道整建,並創下許多國外攀登的紀錄,山是他的臍帶,也是他的榮冠。
刻在山頭的履歷太長了,我只能撿幾則來報道。就說國內登山者的基本功百岳山頭好了,伍玉龍曾經陪着四位登山客(其中一對是夫妻)各走了一趟百岳,幾年間就有200多個山頭入袋,這還不算那些零星的嚮導經驗。再說山搜吧,因為對山的了解,伍玉龍的山搜能力屢屢讓人稱奇。他雖然成功救援過許多意外,但不是所有山難都能有幸運的結局,伍玉龍計算過自己背下山的大體,可能超過60具。或許正因為這些經歷,讓他贏得「台灣雪巴」的稱號。
然而,對於「台灣雪巴」這個響亮的稱號,伍玉龍說:「我認為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

8,000米孤絕一身「很享受」
因為擔任背工,服務過許多外國登山客。伍玉龍常聽他們稱讚自己的體力,還有日本登山客要仲介他到富士山去背水,他們說「保證可以賺大錢」。一個東埔部落長大的孩子就這樣在耳朵裏長出世界地圖,地圖上是許多聳立的山頭,他想把那些標高,存進人生的存摺裏。
第一次出國攀登高山的機會,在伍玉龍26歲時。當時他是玉山國家公園首批巡山員,管理處處長葉世文認為應該增加巡山員的登山經驗,於是湊了些經費,送伍玉龍、方良和歐陽台生三位到阿根廷攀登南美洲最高峯阿空加瓜峯。那是台灣人首度登上6,000公尺的高山,伍玉龍說:「登頂後,我和方良兩個人抱頭痛哭。」眼淚結冰「咚咚」地掉落雪地,人生哪有多少成就值得這樣的配音。
阿空加瓜峯後,伍玉龍、方良和方有水又去攀登印度的莎瑟峯,並且成功登頂。只是下山時方良產生高山症狀,不只無法行走,甚至進入瀕死前語無倫次的狀態。伍玉龍和方有水輪流背着兄弟下山,一邊走還一邊聽方良交代後事。還好下到4,000公尺左右,方良就被直升機載送就醫,平安撿回一命。
至於伍玉龍自己離死亡最近的經驗,是攀登世界第六高峯卓奧友峯。在無氧、無協作、零下30℃的惡劣環境下,隊上只剩他有能力攻頂。半夜12點出發,他以一分鐘走一公尺的緩慢速度,成為台灣登頂卓奧友峯第一人。但在登頂過程中,因為GPS對講機故障,他和基地營完全失聯。也就是說,萬一有任何意外,他能夠倚靠的只有上帝和自己。「不怕嗎?」我問他。像是花了點時間讓記憶回到那天地蒼茫、孤絕一身的8,000公尺,伍玉龍想了幾秒後篤定地告訴我:「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我很享受。」
他甚至否定「離死亡最近的經驗」這樣的說法,因為他有知識、技術和膽識,高山上的一切他都能夠掌控,相較來說,他認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其實離死亡更近」。
伍玉龍也聊到他第一次挑戰珠穆朗瑪峯的故事。出發那天,伍玉龍找不到平時隨身的《聖經》,他父親又因為兒子要遠遊而生悶氣,出門前就沒有好兆頭。他和中國聯攀隊到了7,028公尺的北坳營地後,接連下了11天大雪。伍玉龍遭遇第一頂帳篷被火燒、第二頂帳篷被狂風吹走的厄運後,心頭有種「時機未到」的感覺。就在8,300公尺的前進基地營、就在珠穆朗瑪峯頂舉目可望的550公尺外,伍玉龍決定將登頂機會讓給隊友吳錦雄,吳錦雄也就接收了「台灣首攀」的頭銜。

不求征服快感 登山是回家
16年後,伍玉龍從珠穆朗瑪峯南側順利攻頂,也達成七頂峯(7大洲的最高峯)完攀紀錄。雖然自1993年由北側攀登珠峯失敗後,伍玉龍就不再進行海外攀登,但是聽聞歐都納戶外用品贊助3,000萬元的「尋找台灣探險王~挑戰世界七大洲最高峯圓夢計劃」開始甄選,伍玉龍又心癢難耐。經過龍洞攀岩技術考驗及雪山漏夜登頂體能測試後,伍玉龍獲選成為七頂峯攀登隊的隊長。他們花了三年時間,刷新台灣的攀登紀錄。
讓我不解的是,這七頂峯完攀的豐功偉業,伍玉龍就這樣輕輕帶過,反倒是第一次珠峯失敗以及其他幾次海外攀登,他說得欲罷不能。「因為經費充足,所以七頂峯請了嚮導和背工,我感覺不是那麼有趣。」他這樣解釋。山巔吸引他的不是征服的快感,而是挑戰的歷程,那種從「可望」到「可及」的召喚,最是勾魂攝魄。
台灣的高山背工除了服務登山客外,也協助學術研究及高山工程。直升機無法空投的地方,建材得靠背工背負。長期配合施工單位後,伍玉龍也慢慢掌握施工設計圖的判讀方式。他知道背工、嚮導或是巡山員,都有體力與年齡的限制。為了養活未來的自己,他成立了恆熠營造公司,專事政府的高山工程案,負責山區步道修復與避難山屋建造。多年來,他利用充滿布農族傳統智慧的工法技術,營造友善環境的高山工程,也提供許多工作機會。
可貴的是,伍玉龍不會端「老闆架子」,他以身作則,親力親為,一年難能有一個月睡在家裏。事實上,在玉山採訪的前一天,我們才跟他在八仙山森林園區碰過面。那裏的沿溪木棧道腐朽不堪,伍玉龍帶着工班爬高探低,在架空的鋼結構來回奔走,為的就是重建一條安全的步道,讓喜愛自然的人親近自然。
伍玉龍說,步道會因所在位置及遊客密度而分等級。森林遊樂區的親民性是首要考慮,鋼鐵和木棧板是「必要之惡」。然而如果可以由伍玉龍作主,他必只採用傳統工法,只選用在地素材。有一次到觀光局開會,得知某步道有崩壁狀況,伍玉龍很自然地說:「你們就放一段時間,讓動物去走,步道的軌迹就出來了。」這個建議來自他長期與大自然互動的經驗,但有關單位不懂得重視,只把珍貴的「原住民知識」當成玩笑。
伍玉龍對於自然步道的認知,和「台灣千里步道協會」的理念一致,珍惜他的原民知識,協會頒了第一屆榮譽步道師的頭銜給他。在台灣「手作步道」的熱潮中,伍玉龍欣見更多朋友體認手作的可貴,循着這些掌紋,走進山的肌理。
登山就是回家。伍玉龍送客前對我們這些訪客下了這樣的結論:「山是我的老師、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醫生。」在他身後,幾片二葉松針落地,松下有金翼白眉覓食,山嵐緩緩散去,玉山依舊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