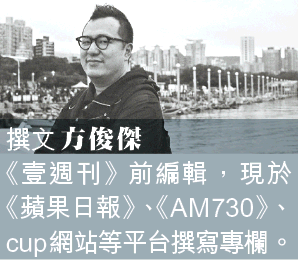
在香港,有沒有人看紀錄片?有。關於壽司之神小野二郎的,關於藝術家草間彌生的,甚至關於名導演Quentin Tarantino的,反應不太差。有沒有關香港事的作品?十年前,有齣《音樂人生》,紀錄本地音樂天才的成長,獲提名金像獎最佳電影;近一年半載,以梁天琦作主角的《地厚天高》,應該很多人看過。Well,沒有其他?
香港導演卓翔執導的《戲棚》,以大戲作主題,獲提名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好像沒太多人關心,大家比較關心有甚麼香港明星怕到不敢出席。紀錄片本身不是主流,還要一拍拍三齣拍足十年都以冷門的戲曲作題材,卓翔簡直是異類中的異類中的異類。「我絕對會被主流歸為異類。不過,社會上,真有人具備權力標籤另一批人作為異類?」
撰文:方俊傑
攝影:郭永強
場地提供:東南樓藝術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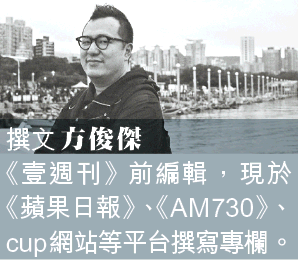
電影救了我一命
卓翔是真實姓名,很有武俠小說角色的味道。他在香港土生土長。「小學升中學,轉到比較好的學校,無論運動還是學業成績,我突然變成全校最弱的一班,個人形象好低落。」
那是未有Netflix未有Apple TV+的年代,想看電影,除了購票入戲院,只有影碟店。卓翔的媽媽給兒子帶來一張金獅的會員卡,租周星馳的《審死官》來笑餐死,很合理,好奇到租黑澤明黑白片,租《感官世界》租《巴黎的最後探戈》,比較大膽。
同學往後談起電影的話,卓翔可以搭訕,介紹導演之前拍過甚麼作品。一時之間,好像化身半個電影專家,終於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於是更加留意電影資訊,看電影之前,一定先看介紹看影評。整個青春期,我也被孤立,心情低落,電影是我最大的夥伴,可以說是電影救回我,讓我覺得自己有價值。」
特別喜歡日本電影。因為日本電影專以異類人物作主角,他可以從中學習,研究如何轉變心態,找一條作為異類也可在社會好好生存的方法。自此立志投身電影行業。「好想為電影出一分力,好希望拍出來的電影,可以影響到他人。如果有人透過我的電影,尋回生存力量,就夠。哪怕只有一個人。」
心存大志,進入演藝學院電影系就讀,是正路選擇,不異類。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做實習生,在《色,戒》負責為群眾演員試鏡。「導演要求好高,找人扮演香港大學的學生,不找演員,要找真正大學生。我們聯絡幾間大學的學生會,集合了四、五百個學生來試鏡。即使鏡頭前根本見不到那個臨時演員,每一個被選中的人也被安排去剪髮,才可以拍攝。」個導演,是李安呀。
畢業後,正式入行,當然明白《色,戒》是千年難得一遇。「製作費少得多,工作時間好壓縮。尤其文藝片,製作周期特別短。」終於發現,完成夢想,不是想像中容易。


我不是天才
跟現今大部份中年人或年輕人一樣,關於戲曲,卓翔只不過在每年的《歡樂滿東華》被迫看一看,談不上了解。在演藝第二年,人生第一次現場欣賞,驚為天人。「我不斷反問自己:『為甚麼有這一種屬於自己的美好文化,我會太遲認知?我能否利用自己的專長去為戲曲做一點工作?』」
如果是我,坐定定看一場折子戲,大概只會睡,或者直接離場。「戲曲其實將華人的多方面文化結合,無論文學、音樂、舞蹈、表演形式。透過戲曲,可以了解過去。戲曲不單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表演藝術,它其實跟我們的生活、宗教掛鈎,很值得被重視。幾百年歷史,跟莎士比亞作品差不多,為甚麼西方社會重視自己的傳統,到今日莎劇還會被尊重,我們偏偏不把戲曲放在同一位置?」
現實一點,卓翔也明白要觀眾入戲院看三小時演出,難如登天。不如引導他們入戲院看齣電影,電影拍得好的話,自自然然會讓他們對戲曲產生興趣。一開始的時候,卓翔其實想拍一齣《霸王別姬》,拍一齣《虎度門》。「《虎度門》都已經是1994年的事。」
過去十年,資深大導演開戲,才有資源。新晉導演想拍小市民的生活?困難。做了好幾年副導演,卓翔已經興起拍攝以戲曲演員作內容的劇情長片的盤算。為追夢,甚至毅然放下工作。「手腕,是越來越純熟;內涵,原地踏步。」參加過鮮浪潮短片比賽,明明經驗比其他參賽者豐富,也敗北,讓卓翔開始反省:如果實實在在想當導演,繼續留在行業,會否反而累事?適逢台灣金馬獎辦了一個電影學院,廣招全球華人導演交流學習,卓翔去到,像頓悟。
「香港太急。三十歲要買樓,三十歲要拍到第一齣電影。你去一去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年紀比我大的,剛剛起步,一點也不遲,根本不用心急。我不是天才,步伐是很慢,就按照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行。」


用普通人感動普通人
拍電影,事先要做大量資料搜集。「做準備的時候,某程度上也能夠同步進行另一份作品。」即是類似製作特輯。結果,有關戲曲的劇情長片至今未動工,三齣同步進行的紀錄電影順利完成。
功利一點,拍紀錄片的門檻畢竟低得多。「一開始,未有資源,只需單拖,最多找個老死,做一些基本訪問,便可以利用拍下的片段,再去找人投資。紀錄片容許這種階段性工作流程。最基本,自己拍攝自己剪接自己混音,作品也可以出街。對新導演來說,是比較容易起步。」
可惜,香港根本沒有紀錄片市場。「你可以這樣說。在台灣,每一年,在戲院看到的本地製作紀錄片,超過十五齣;在香港,不足五齣。不過,如果連其他國家的製作也計算在內,每年也有超過二十齣紀錄片在香港上畫,紀錄片文化正在慢慢建立,比以前健康得多。不少觀眾其實願意花費一百元看一齣紀錄片。」
如果有戲院敢播《地厚天高》,說不定真會票房鼎盛。卓翔關注的,是戲曲,不是社運明星。「對,選材,最好拍名人,或者很特別的人,或者極端的弱勢。戲曲?三樣也不是。為甚麼要拍天才的故事呢?在社會內,最大的一班人,是普通人。我好想透過普通人的故事感動普羅大眾。」
卓翔說,活在中間階層的,往往被認定最不值得關注,往往最沒有人紀錄,他最關心。戲棚之內,他留意的,未必是站在台上表演的明星,反而是幕後籌辦的平民百姓。果然是偏門中的偏門。「每個紀錄片導演都有自己的角色,有屬於自己的題目。有些題目,有人做了;戲曲,沒人關心,但我覺得它是讓很多人連結的寶庫。」
初初製作紀錄片,以為只不過過渡,最大功能是為拍攝劇情長片作藍本。事隔十年,心態畢竟改變。「對我來說,紀錄片不再是單純為劇情片服務。兩者形式不同,但目標一致,都是希望為觀眾帶來改變。我喜歡的導演,例如是枝裕和,例如奇斯洛夫斯基,都是拍紀錄片起家。有紀錄片的背景,或者可以填補我需要發展內涵的狀況。」
越不脗合越要留低
既然明知在香港當個紀錄片導演,路難行,何不轉投市場完整得多的台灣?「在香港,跟中學同學小學同學聚會,他們第一時間問:『點搵食呀?』不是他們個人問題,是社會給我們太大壓力。在台灣,即使普通朋友,也會關心我有甚麼題材,想怎樣做。大家容許一個人用多一點時做同一件事。」
「第一次去台灣,已經有種好大的感覺:我更加適合當地。我跟香港好像不脗合,香港不需要我。香港普遍性喜歡用標籤分類,因為容易理解。以前,被視為異類,我會不快;現在,不介意了,你覺得我邊緣,我就是邊緣吧。我更加應該留低,更加應該為異類留下一些紀錄,更加需要發出另類的聲音,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存在過。」
「本地人拍本地題材,觀察會更加深入,會更加了解細節。既然自己做得到,應該盡量做,不用倚賴外國人為香港人留紀錄,把香港人的故事說出來。」
說到底,從未被重視過的紀錄片,在香港真有用途?「好重要。香港的劇情電影,跟我們的生活越隔越遠;要找一齣跟我們生活有關的,越來越難。紀錄片可以作為補充,至少,入戲院,見得到跟自己有關的東西,不再是一味查案、英雄,而是見到普羅大眾。」把香港人的真實生活紀錄下來,真有片商夠膽識供出映期?當講述台灣戒嚴時代的虛構鬼怪片,也彷彿變成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