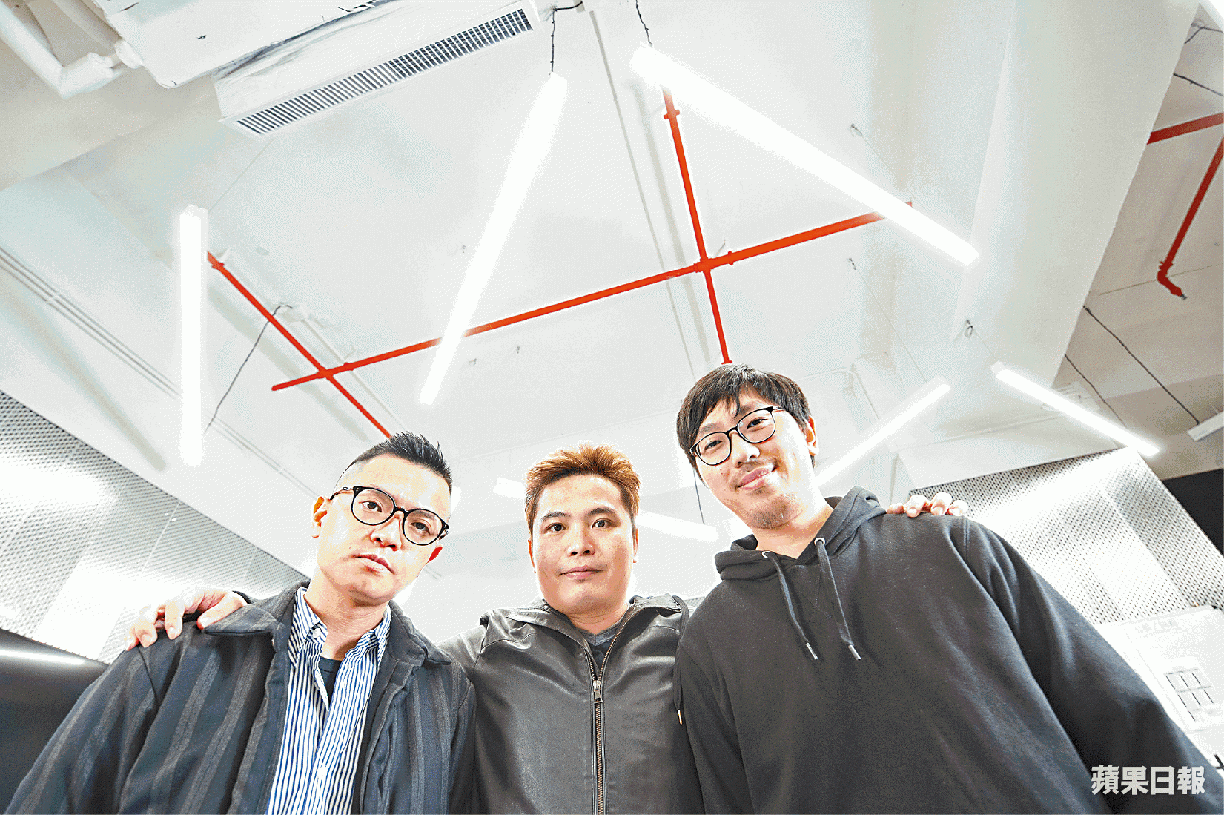
歐文傑是《十年》和《樹大招風》其中一位導演,伍嘉良是《十年》其中一位監製,伍奇偉是《樹大招風》其中一位編劇,完全是金像組合。其他較醒目的金像級電影人,返大陸,票房動不動十數億。他們留在香港,搞網上平台一丁目,專拍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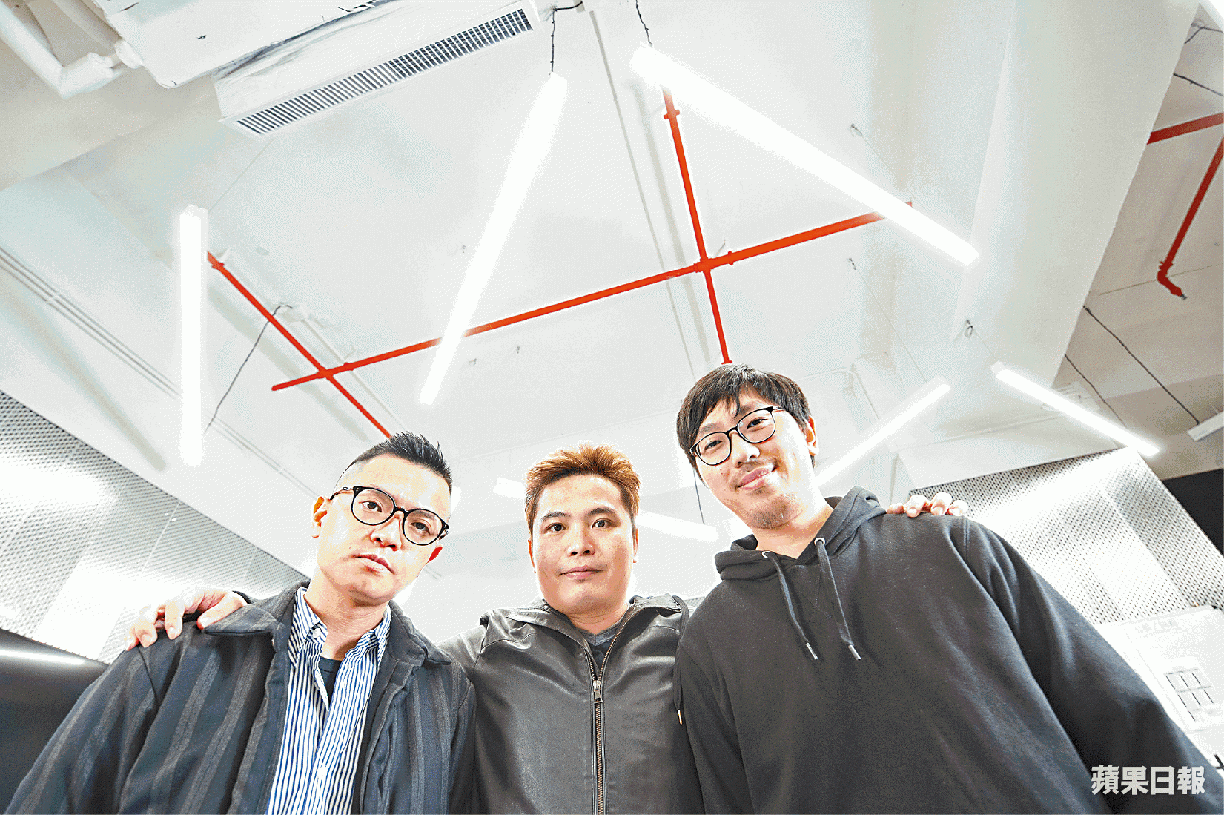
「我像橋樑,希望製造出一個空間,讓更加多年輕創作者勇於發聲。得我發聲的話,言論自由只會不斷被收窄。要有好多人出現,空間才會變大。」反送中抗爭以來,一丁目推出過好幾條一針見血的短片,題材敏感。「在今日,大概提出『敏感』兩個字,已經很敏感。」當行政會議連封鎖互聯網都考慮過,香港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恐怕已岌岌可危,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隨時降落。「經過這次社會活動,香港人會珍惜我們這個平台。」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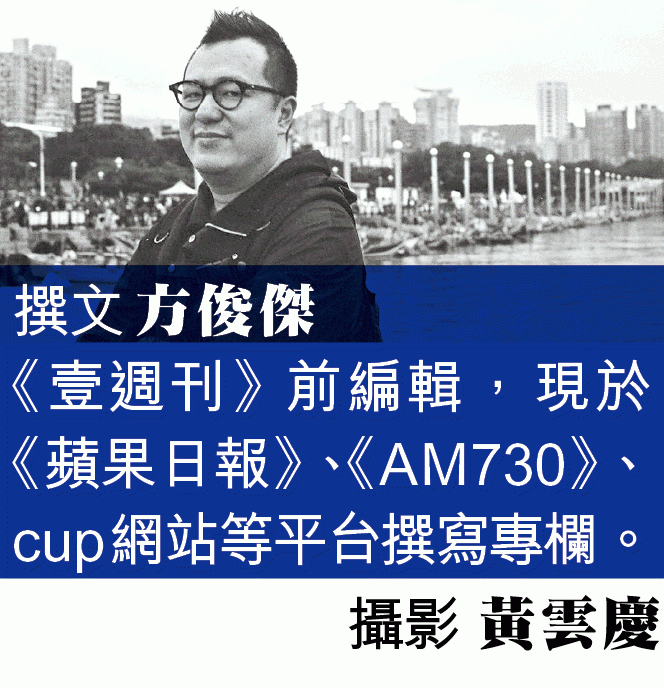
跟香港人的連接點
歐文傑拍過《十年》後,《樹大招風》上畫,據聞因為題材敏感無法通過大陸審查。兩齣電影,皆成為金像獎最佳。之後再拍題材健康的《非同凡響》,一樣被大陸打壓。噢,對人,不對事。
「我經歷過《十年》場場爆滿也被迫落畫,知道香港的發聲空間其實所餘無幾。我自己希望發到聲,也希望大眾的聲音能夠被聽見,力量才會出現。」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找歐文傑合作,他二話不說找最佳拍檔伍嘉良及伍奇偉埋班。「這裏最好的地方,是乜都得。環顧香港任何公司,想拍片的話,總有些審查,總有些題材限制。要完全沒有掣肘?我們是唯一。」
原意是設立一個網上平台,播放談論香港人的故事,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我打開電視,入戲院,看的故事,原來跟我的生活沒有關係,我找不到連接點。我覺得觀眾總需要找到這個連接點,即使未必完全反映到自己的想法,至少有少少關係。市場有需求,沒有供應,我們想去填補。《十年》,好多人看,我們的內容,會否一樣?」
蘋果的好處是本身有龐大讀者群,壞處是立場鮮明。說得坦白一點,是很多行內人應該一聽到蘋果兩個字,已經腳軟。伍嘉良同意:「要找資深的創作人,是困難;可能因為製作上的規模、限制,他們拍開長片,又未必想拍短片。有演員甚至完成拍攝後,出錢買回製成品,怕影響其他工作。」《十年》是2015年的事,氣氛每下愈況。「自我審查越來越強,不只幕前演員,幕後工作人員也一樣。」找素人演出嗎?要花心機慢慢調教,又是時間成本。「有演員覺得講反送中講選舉,很敏感;總有演員相反,慢慢積聚到同一批人。是個問題,也可以看成一項挑戰。」
何況,一丁目本沒說過只限跟政治議題有關,部份短片,輕輕鬆鬆搞搞笑笑飲飲食食,與政治相隔九千公里。「其實,是想有點似Netflix。」歐文傑的目標很遠大。
由菲林到數碼
Netflix發展到今日,會購買其他公司出品的播放權,也有無數自家製作。金球獎戲劇組最佳電影五強,Netflix佔三。恐怖在,每月花費六十幾元港幣,已經可以合法收看。基本上是頂爛市。「以我們的人手、資源、能力,不可能立即變到Netflix。Netflix主攻電影、電視劇,我們擅長短片。大家針對的市場不同,我們不是競爭對手。」
歐文傑說,短片,是一場革命。「大家的睇片習慣正在不斷改變,用手機,在車程中間看,會喜歡片長再短一點。在香港,短片好像永遠是踏腳石,一個導演上位拍長片前的第一步。在外國,短片創作者,不少是一生也拍短片。是否一定要拍到長片才算終點?只要建構到一個平台,有老闆願意持續支持,有廣告收入,生存到,甚至得到肯定,短片肯定有市場需求。」
現實是,奧斯卡有最佳短片獎,香港電影金像獎,沒有。「《十年》,五套短片合輯,成為一齣電影。為何不可以肯定短片的價值?很少人會在網上分享一齣片長三個半小時的《愛爾蘭人》,好多人分享我們的《逃犯條例》三部曲。在接觸觀眾的層面上,傳統電影也去不到同樣效果。」
「電影獎項?攞過啦,咪又係咁?馬田史高西斯也拍Netflix,還有《羅馬》,還是否必定要上大銀幕?剛剛看過一條短片:一個Youtuber在街頭訪問幾位荷李活A級大明星,路過的行人,只認得Youtuber,不認識大明星。網絡的影響力,隨時比電影更大。未來,一定在online。我們只不過由用菲林相機拍攝,轉變成拍攝數碼相片。」

所有創作也要成本
跟Netflix不是競爭對手,跟YouTube算不算?我拍了條片,放上自己的戶口可以了,為甚麼要交給另一個平台?身為監製的伍奇偉很老實:「成本!」
「香港人覺得好多工作不用付費,請個婚禮攝影師,也拍拍膊頭。其實,所有創作也需要成本。我們的運作模式很簡單:你傳來一個WhatsApp message,有人物概念,故事大綱吸引,合理,不會像拍一齣《阿凡達》高成本,我們批錢開拍。」
有人為因素,換句話說,一定有偏頗。至少,一齣讚揚警察的藍絲作品,恐怕不會受到青睞吧?也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剝削。「我們只注重故事好看不好看,有沒有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建制可能有好人,警察都可能有人有惻隱心,如果拍得好,不可能因為大家好憎警察,便阻止作品面世。就是希望平台的內容夠豐富,百花齊放。」
除了錢,目標顧客原來也很重要。「以我接觸過的年輕創作者,好多時拍完畢業作品,情願收在褲袋,也不肯公諸於世。他們希望找到一個比較得體的發放平台,大概知道會接觸到哪一類型的觀眾,附近不會是一條教你如何將魚蛋彈上天空的無聊短片。老套點說一句:我們是嘗試聚合一班志同道合的創作者和觀眾一齊開派對。」
這也大概是歐文傑被選中的一大原因:「我包容性夠大,你看看我們的短片,沒有一種所謂的歐文傑style。很多年輕人比我厲害更多,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自由的空間一個平台去實踐去發表。香港需要他們的作品,我也希望成為他們的觀眾。」

在年輕人中見到希望
整個計劃,在去年年底開始籌備,那時,社會還風平浪靜。一場反送中抗爭襲來,是帶來助力還是更大的阻撓?「跟我們搞網絡的,說過一句:『政府一句封網,你們就玩完!』以為不可能發生的,原來已近在眼前。不是單單因為這場運動,這幾年香港的變化,我相信令到不少香港人對發聲空間有更大的需要,看着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不斷被收窄,越來越多人想保留和珍惜蘋果這個平台。這個催化作用好犀利。」
於是,本來視壹傳媒為洪水猛獸的,也願意主動接觸,甚至合作。「之前,一直有人問我:『還返不返大陸?』今日,我可以反問:『還敢返大陸?』行出街,隨時『被返大陸』,很多人對社會的看法跟以前大有分別。」
伍嘉良忍不住笑一笑:「這幾個月,拍紀錄片的傾向明顯多了。拍劇情片,不可能夠現實荒誕。」最難適應,或者在工作模式的改變。拍一齣《樹大招風》,拍足幾年,鑽研一句對白,用一個月。網上平台要維持出片量,不可能再現拍電影的奢侈。「這一年,不停構思,不停有不同計劃,跟拍電影比較,是另一種得着。」
「對,我們是沒有時間沒有資源搞鐵甲奇俠副盔甲。我們也不追求。故事最重要,人物最重要,《樹大招風》好看,因為葉繼歡好看。馬田史高西斯在《愛爾蘭人》的製作特輯說過:『新片沒甚麼特別,只有人物性格。』好像很廢話,但你想一想整場反送中風波,你會記得的人物,全部性格突出。拍到出來,已經可以好好看,跟錢和時間的關係不大。」
「錢、人、資源,統統可以克服;只有自由,被奪走的話,不能解決,只能適應。給我選擇,有資源,還是有自由?我當然選擇免於恐懼的自由!曾經有過大成本合拍片找我做導演,說可以解決上內地的問題。結果,我還是推了。搵食有好多種方法,電影是一種表達真實感受的工具,如果拿來賺錢,代表要將自由自行奉上,是一種違背。哪倒不如用其他方法為生?更容易更快捷。」
一丁目的辦公室內,除了比較有社會經驗的這三位,還有不少年輕員工。「運動之前,帶住一班後生仔工作,就似一般人對後生仔的觀感,他們的確有好多問題。透過運動,我對他們的認識深入了,開始知道他們的想法,明白他們為甚麼,願意犧牲。我見到希望。最後,無論是贏還是輸,我也見到好多希望。」要贏呀,不可以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