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訪談】
馬世民(Simon Murray)是個陽光的人,不管在幽深暗冷的倫敦。香港回歸22年,英國人的首都,成了多少香港人的重心?11月尾,又凍,又下雨,又經常沒太陽。無意中,半個下午的事情,成功邀請馬世民見面,到訪他倫敦的家。他曾經最觸動記者的說話是,如果他和KS(李嘉誠)一起在倫敦,有時,基辛格(Kissinger)會來跟他們見面。
撰文:冼麗婷

「原本很多人不支持示威,但現在都變得同情示威者」
11月29日,清晨7時像黑夜,8時簾外陽光普照,嚇你一跳。從肯辛頓南地鐵車站乘的士到達,迎着溫暖的陽光,不到十米,呯一聲關了大門,一個穿深色便服的男人,在如射燈的陽光下迎面走向記者。充滿力量如鐵人一樣的小個子,像是一道前行的黑影,盯着記者。神秘冬日,五秒之間,好想問:「Mr.Murray? 」可是,他已首先開腔:「Are you Jophy?」然後互相大笑擁抱。「是你早了15分鐘,我要去郵局,你先等一下。」跟他一起去郵局?腦袋轉了一下,回頭望,約60年前到阿爾及利亞打仗的法國外籍兵,已在遠遠街角。五分鐘,他回來,在iPhone鏡頭前,快80歲的商人、和黃前大班(董事總經理)馬世民,又動作多多鬼馬起來。
香港亂局,記者在倫敦拜會幾位參與過香港前途問題、居英權及相關工作的人,無一不憂心香港。馬世民在倫敦、巴黎、南法、泰國等地都有屋,四海為家的英國人,曾經為香港爭取居英權,至今依然每90天就要離開英國一趟的英裔香港居民,視香港為家53年了,這六個月,他在哪裏?「我大部份時間都在香港啊,我沒有坐這裏(倫敦)。」他坐在米黃花卉圖案的布藝梳化上,背後白色木框玻璃窗門外的花園裏,有個尖頂的涼亭,園藝由太太打理。說視香港為家,港人抗爭半年,馬世民是誰?他跟記者說,約一個月前,他在銅鑼灣逆流走向以十萬計的示威者,按他描述,和平示威者向他迎面走來,一整條路,厚厚的人群和示威標語紙牌,佔據整條馬路。他走在中間,如穿過一塊偌大的罌粟花田,示威者沒有躁動。他在中環看了一小時欖球賽後,一直找不到的士回銅鑼灣酒店,終於有一輛停下來,司機以危險為理由,五四口議價,先收他400大元,才肯送他。到達之時,銅鑼灣平靜得鬼影都冇。
「下車時,你笑了嗎?」
「你問我能怎樣幫忙?我想,我最少幫助了的士司機,他在我身上賺錢。」他是個時刻可以說笑的人。馬世民因為眼睛有毛病,不停流淚水,所以不能到英國鄉郊小屋狩獵了。曾幾何時,記者致電他老友、上海灘已故創辦人鄧永鏘,對方身在英倫,劈頭說:「我在打獵。」馬世民身邊、口中的老朋友,都有世界精采故事。來香港之初,他先在怡和洋行工作,後來派往史丹福大學商學院進修,認識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路透社較早前關於李嘉誠的一篇特別報道,分析香港首富對中國早有戒心,早於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時,李嘉誠已經考慮把資產轉移到外地,並叫其時得力助手馬世民「走遍英國,去找一間好公司,讓他們把錢投資進去」。文章其中重點,是和黃發言人以中國古人智慧的回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馬世民欣賞基辛格,也一直學習跟中國相處的智慧。首富分散投資會得罪中國,他是知道的。一向關心做生意的英國人,香港過去六個月,卻讓他的戰爭經歷與感受,回到現實。他這樣比喻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始源:「如橡樹的從小橡子長成,也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很不受歡迎的大公爵被刺殺後,令1,700萬人戰爭中死去。」他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推出的《逃犯條例》修訂,無事生端,「是她推出,不是中國。」引起巨大不滿風波,又不作回應。「原本很多人都不支持(示威),街道受阻,大小事情都不能做,但現在,都變得同情示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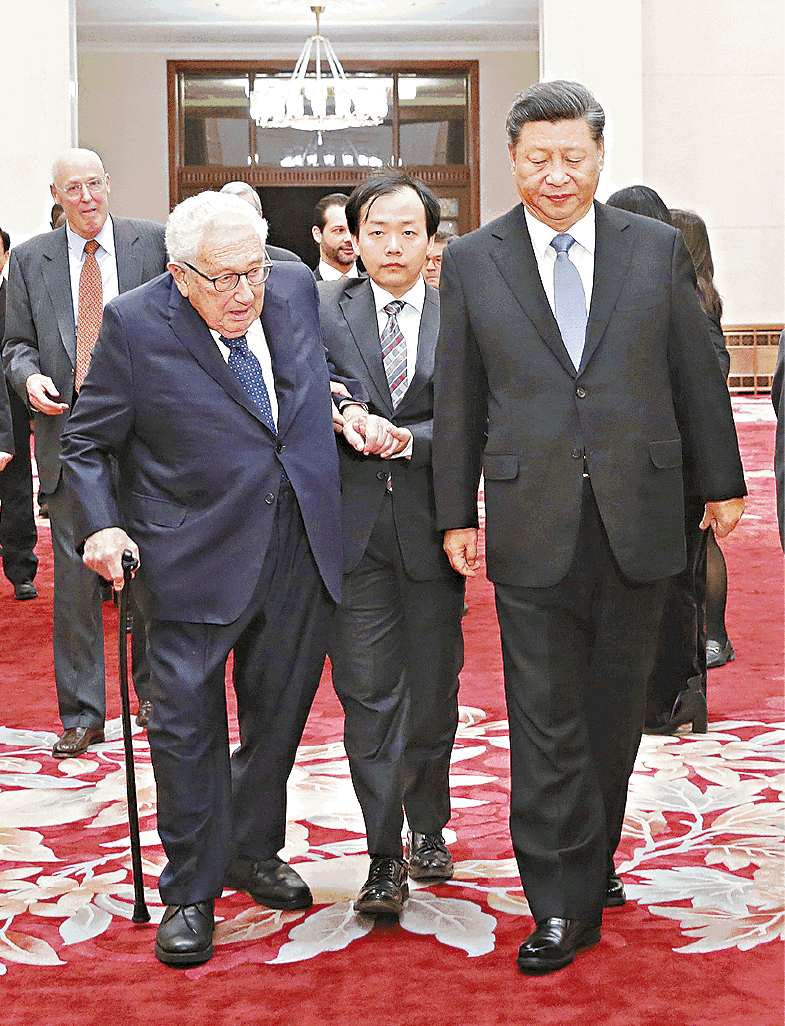
「應坐下來商討,但政府從沒提出這樣的協助」
前軍人看亂局,視點是不一樣的。「你有100萬人在街上,有人被殺,這是正常,是會發生的。當我們有100萬人在街上,越來越憤怒,雙方情緒都上升,這就是問題,這是應該坐下來商討的原因。但我們(政府)從來沒有提出這樣的協助。」他期望學生選出領袖組成委員會,跟政府代表坐下對話。「如果你明天能有這樣的委員會,政府會坐下來跟你傾。」他也知道,找年輕抗爭者及學生選出領袖的困難,「學生不想有領袖,因為,領袖明天可能就要被監禁。」在他的思維裏,網上號召學生出來的威力,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我們不想抗爭者包括學生被收監,或是發生甚麼。我們希望他能走出這窘局。你們想要甚麼?大規模的公共房屋供應,所有需要的。我們不可以再如此生活,不是可以這樣的,我們可以有對話,我們往前走,可能可以走回原本的情況。我明白,我也對此同情。」
「你知道警方放了幾枚催淚彈,是一萬枚。」
「學生及示威者也投擲了汽油彈,在人身上點火,這些又如何?我看到一個男人被潑滿電油,然後點火,這是好玩嗎?」雙方暴力都不能容忍之時,對話是一個現實方法。「你要說,誰先點火?要另一邊自動停止,必須有商討,這是解決問題的首要事情。」
「兩邊給予特赦,可行嗎?」記者問。「當然,我正為此聯繫商討。我們可以找方法,但你必須冷靜下來,投汽油彈,打砸商店,打爛商品,是過份了,就是說因為警暴也不應該。他們不會為此調查的,誰開始暴力?」現實或許殘酷,如果這是場「戰爭」,這位前軍人看的結局,只有和平,「非關於誰是誰非,是關於誰能留下來的結局。」
「作為前軍人,按你的經驗及哲學,有何建議?」
「Yes, it ends in peace,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o war to get the peace。 (是,戰爭的結局是和平,有時,你要從戰爭取得和平。)」這是他說明白學生的深義所在,但他的經歷,卻也是現實的。他參與阿爾及利亞戰爭,他知道誰發動戰爭,但發動戰爭的人,會說是其他人開戰在先。「1957年有示威,示威,就如香港的示威,失控,法國人的反應過了頭,有人被殺,最後完結,簽訂和約之時,你不會說誰人開始,『他們反抗,是警察介入』,誰做這,誰做那,不會是這樣的,(到那時),和平才重要。」
「怎樣可以平息下來?」
「為雙方開一個委員會,通常如此。越南戰爭,法國及美國都坐下來商討,就完了,德國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在法國議和,也是以商討作結。」
「你認為政府有開展對話的能力與意志嗎?」
「在我的意見,我只是說他們應如此做,但直至現在,我沒有聽過政府有如此說,零。從政府那邊,我甚麼有意義的都聽不到。」
「那你對『戰爭』得到和平是悲觀還是樂觀?」
「這種事情都是如此完結,我們不會這樣繼續20年,但它正在繼續,而且比我們想像中長。」

「林鄭辭職就能幫上忙,現在就補選,把她取代」
以往馬世民說過不認識林鄭月娥,不評論她,這一趟,他矛頭一直指向她:「她說她不能辭職,因為中國不讓她辭職,她其實明天早上就可以辭職。」
「所有人都認為她是傀儡,有主子在背後,其實,誰管我們的明天?」記者問。「我不知道誰在她背後,正如有人說學生的背後是CIA,是台灣人。她根本是主事人,卻說自己不能辭職,如果她想辭職,她是可以的,而且是邁向正確方向一大步。是她造成亂局,是她令我們所有人都憤怒,如果她明天病了,她能不辭職?如果她明天跌跛了腿,她可以辭職,不能說你不被批准辭職,這講法全是垃圾。是她引致所有現況,不是中國。」
「誰人可以幫上忙?」
「林鄭辭職就能幫上忙,現在就補選,把她取代。不要告訴我沒有人知道誰能接替她,如果她肯走,誰可當下任特首?這是很荒謬。當700萬香港人是甚麼,總有人能勝任。」
馬世民也曾跟商界圈子談過化解問題方法,他們都跟他想法一樣,化解問題之前,要先停止暴力現狀。他跟香港的感情,當然跟人有關。商人富豪是他朋友,曾經被判入獄的前特首,也一直是他提在口邊的老朋友。很早以前,前特首曾蔭權在赤柱監獄服刑之時,馬世民就去探過他。「我問起逃犯條例,以為是中國要引入來,他說不,是林鄭自己開展的。」曾蔭權出獄後外遊,雙方曾在英國見面,談起港事,後來在香港,也見了兩次面。「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當英國要把香港移交中國,我們設法為香港人找英國護照。我們最終可以找到五萬個家庭受惠,曾蔭權當時非常非常努力。他不應該入獄,這是令人憤怒的。」他出獄後,對甚麼地方發生甚麼事,都很熟悉。
「你們兩人對香港的亂局怎樣看?」記者問。
「我不能代他回答。」
「那你跟KS(李嘉誠)談過了?」
「我當然見過他,但我沒有跟KS談這局勢。」
「為甚麼?」
「因為我不想他扯進去,我認為他不應介入,但他是介入了。」李嘉誠曾以一個香港巿民身份,在報紙上登廣告,「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以愛之義,止息怒憤」,也叫年輕人「不要讓今天的激情成為明天的遺憾。」
「他同情抗爭年輕人。」記者說。「是,但他做錯了,這很容易做錯,他說,你是明天的主人,或者甚麼,中國不會喜歡,是不是說過這類說話?」
「為甚麼我們要說中國喜歡的?」
「我不是說應該,我只是說,你會迷失了?」
「你認為KS迷失了?」
「我不談KS,ok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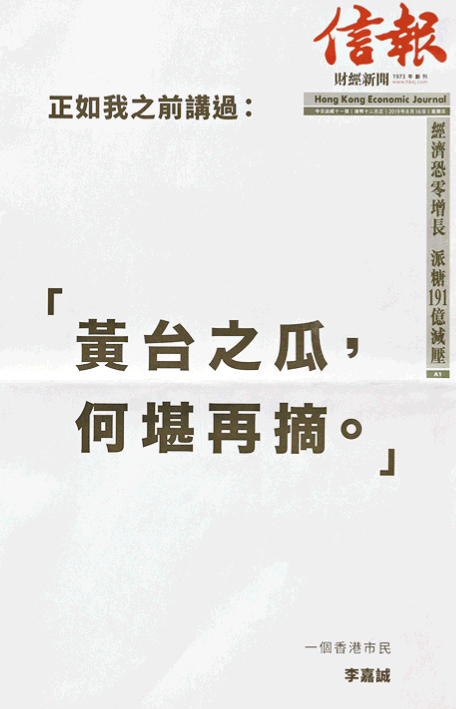
「香港曾是個平靜的地方,這次是災難」
李嘉誠曾叫政府對年輕人網開一面,好些香港人,變得從未如此喜愛李嘉誠。而馬世民與李嘉誠的關係,是可以有話直說的那種。他說四個月前在李嘉誠辦公室見過他,那時候情勢完全很不同,大家只談過整體上的社會問題。「我在香港53年,我是深愛香港的人,香港是我家,我同情抗爭者,但我不認為他們需要做這樣的事情」。六個月看着香港的亂局,馬世民坦言傷心,「看着自己的故鄉走向四分五裂的方向,誰會不傷心?以往,我在香港的時候,都是很放鬆及感覺安全的,就是午夜你走在街上,都感覺安全。香港曾經是個平靜的地方,這次是災難。」
香港,給過不少人一生的傳奇。作為一個快80歲的人,在香港過了大半生,相識天下,現在香港人支持抗爭者,並努力爭取國際關注及協助,馬世民可會找基辛格聽一下意見?「他是一個老朋友,但我不相信他會來。不會。」
「為甚麼?」
「他太老了。」
「93歲還能走動啊。」
「他住在離北京兩小時車程的郊區,他不會想來香港,他有其他事情要做。」
「他可以表達支持。」
「我們可以自己支持香港,這是應該由香港人自己解決的。它不需要仲裁人,一切應該由香港自己處理,否則永遠不能解決。」
跑過242公里撒哈拉沙漠馬拉松,也曾經步行至南極的探險者,馬世民獨有的宏大視野,不一定貼近香港年輕人的心,他知道。年輕人沒有大台的概念,他也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意見只能代表自己的想法,但他還是想給學生說話:「學生們,你聽過我的意見了,但我希望你們雙方坐下來商討。」他認為學生可以組成委員會去見特首,如果政府不商討,學生可以繼續抗爭,但應該盡量按法律上街示威。「不要擲汽油彈,因為這樣會走入戰爭狀態,毀壞店舖,也不要做。」他明白有時和平示威不一定達到訴求,但總有別的方法。「所有戰爭都以和談結束,如果你回望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1,700百萬人,需要嗎?第二次世界大戰,6,200萬人死去,需要嗎?以和平作終結,商討吧。」
香港傳奇,英國人開始,香港人,一定有能力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