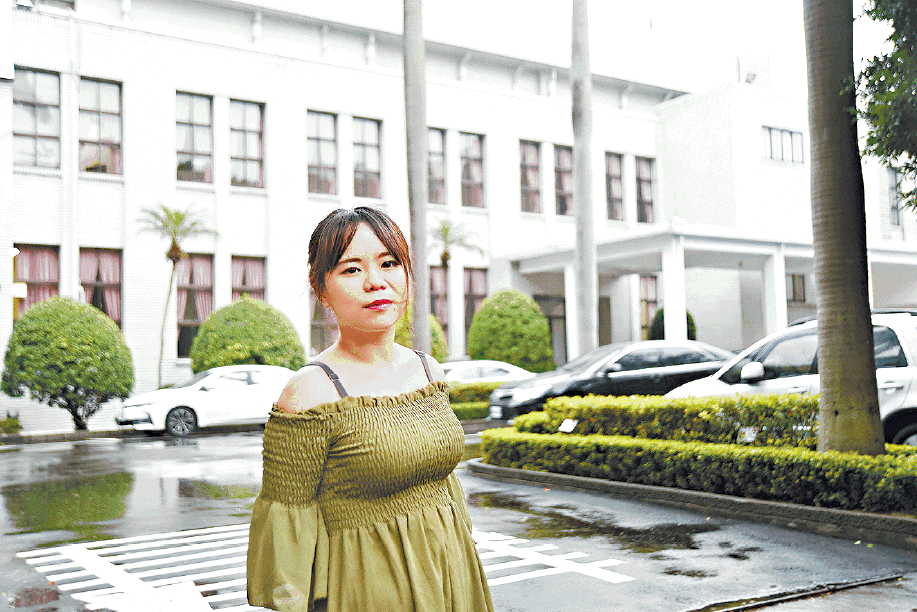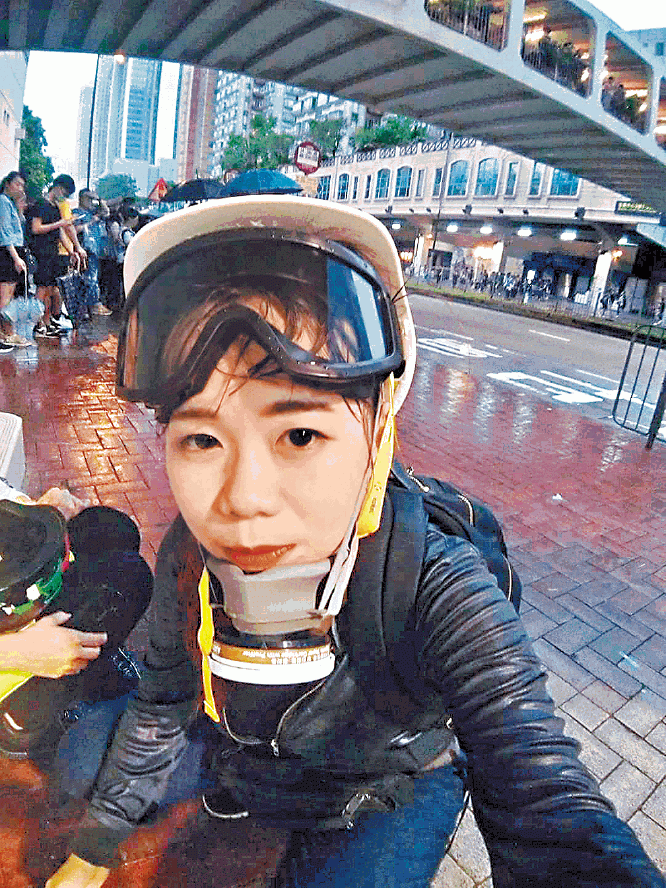
香港跟台灣兩兄弟,鏡中有我,我中有你。雙生兒活在中共「Big Brother」的後面,兩地社會運動一直互相關愛,互相模仿。1989年,台灣擔心香港1997年回歸後變成北京的「天安門」;2014年,香港的自由花含苞待放,佔領區的黃傘子一下子消失,夏慤道、彌敦道、軒尼詩道如常車來車往,政府的政治清算隨之而來,香港民主之聲沉寂五年。
2019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五大原則,探索一國兩制下台灣方案。「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再是口號,確切說明了港台在中共政權下是命運共同體。2019年,台灣人不再隔岸觀戰,太陽花運動「衝組」成員黃燕茹兩度來港,跟香港人一起「衝」,一起迎接無大台的抗爭年代。
撰文:王紀堯
全球見證香港逆權之夏,跟中國共產黨對着幹,中港意識形態如着一條隔鴻河。「你是甚麼人?」的身份認同上除了民族和種族以外,還有一層——「自由/民主」。
「命運共同體來自我們對中共政權感到不信任」,曾經是台灣太陽花學運「衝組」成員的台灣女生黃燕茹帶着這個想法,6月底以及8月底兩次來港,以邊紀錄邊抗爭的方式參與反送中運動。
「這一切,台灣許多人都看在眼裏,今夜台灣同樣憤怒。」黃燕茹走過荃葵青大遊行的前線,事後在紀錄文章中寫下這一句。她感受過示威者包圍警總的氣勢,又嚐過催淚霧中逃避防暴警的追捕。不一樣的身份,一樣的憤怒,在這個異鄉人眼中,香港一場逆權之夏有港警紅了眼的暴戾,也有人性光輝的一面。
2014年黃燕茹曾到旺角佔領區觀察,見證港台抗爭大不同,一旦燃起人民抗爭的心,不愁沒有力量,「台灣的社運就是擔心被遺忘沒有焦點、沒有話題、沒有輿論性。在香港,讓事情一直燒下去是警察的暴力。」
不論是6.12發射的催淚彈與子彈、7.21白衣人在元朗站無差別襲擊市民,8.31太子站警員進入港鐵站打人,警方在整場運動中所使用的武力,在台灣人眼中,是自身島嶼上不可能發生的事情。7.21白衣人發狂入車站、車廂狂打人,全球譁然,黃燕茹說:「我不感到意外。」
早在五年前,她已經來港參與雨傘運動,身為台灣社運中堅成員的黃燕茹選擇離開金鐘,轉戰旺角佔領區。「因為太陽花我一直在前線,所以我會找前線需要幫忙的地方。我去過金鐘,發現是一個樣辦,是我不需要錦上添花的地方,旺角卻是一個雪中送炭的地方。」她沒有準備住宿的旅費,就在旺角街頭睡了一星期,經歷「旺角黑夜」。
她憶述佔旺一晚發生的衝突,一名警員被相機的閃光燈閃到憤怒,於是衝出來打佔領區的示威者,當時她未反應過來,但黃燕茹感到示威區仍然是「Lady First」。 黃說,當時「哨兵」會在旺角港鐵站出口上放着長鐵梯,讓她和其他女示威者爬上去,之後迅速收起長梯,讓女示威者躲開揮動警棍、身形魁梧的警員步步進擊。黃燕茹記得一名女孩子走避不及,就在她眼前被警員打至骨折,另一面就有一個男生在她面前被打爆後腦,瞬間人倒地噴血。「因為閃光燈閃到警察就要去打人,這件事在台灣是不可思議的,但在香港竟然發生了」。
那場抗爭後,黃燕茹對香港「改觀」,深深明白城市亮麗的背後,早已存在很多台灣人無法想像的問題,「那時候『光復旺角』的情況一直很危急,和現在反送中運動有點像,例如黑社會問題、港警打人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
事隔五年,黃燕茹6月底首次參與反送中運動,一抵港即前往包圍警總的現場。她指,香港稱「示威者」與台灣的「抗爭者」有所分別,她看見「示威者」用鐵枝敲打物件發出聲響,也有不斷的謾罵聲,充份感受到憤怒的情緒在空氣中蔓延。「這個在台灣算是激進,台灣現場是各式各樣平靜的畫面,在香港是聲勢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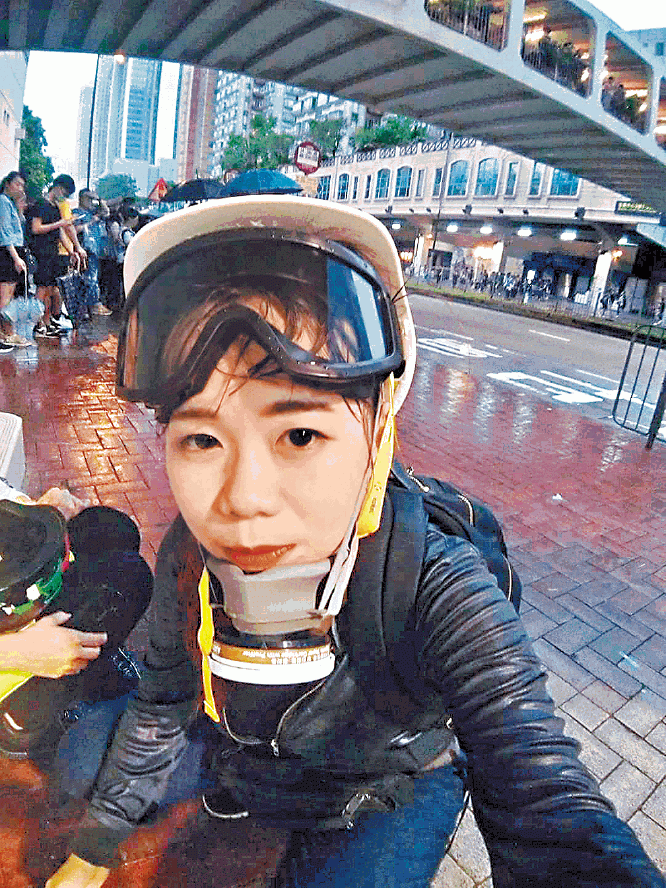
「當時圍着警察,隨即舉黑旗,被罵就放催淚彈,是玻璃心嗎?對於不舒服和恐懼的耐受度可以拉很長,港人的耐力真的驚人。」
8月炎夏,她再次請假來港,走到抗爭前線。在荃灣楊屋道帶上頭盔、眼罩與「豬嘴」,黃燕茹第一次嚐到催淚彈的滋味。「當時大家圍着警察,然後隨即就舉黑旗,被罵就要放催淚彈,是玻璃心嗎?」警方施放催淚彈,眾人蹲下,但皮膚隨即感到十分刺痛,但一眾示威者繼續滅彈、堅持留守,她感嘆:「對於不舒服和恐懼的耐受度可以拉很長,港人的耐力真的驚人」。催淚彈後還有橡膠子彈、布袋彈等接踵而來,「我想了一下要前面還是後面走,因為前面是眼睛,後面是腦蓋,旁邊是太陽穴,哪裏中彈都有機會,就想說用爬的好,不會那麼容易中彈」。
她認為香港警察在煙霧中發射子彈是「隱藏彈道」,「那不叫驅離民眾,那叫謀殺」。荃灣一役,警察首次採用包抄方式逮捕示威者,黃燕茹與其他示威者一起逃命,眼看就要衝上來,她拼命逃跑,爬過了高牆,腿撞上了牆壁,留下一片瘀青。
整個參與過程,是退是進,沒有指令,現場討論得出結果後即時執行。黃燕茹在台灣社運界一向擔任組織者,也就是俗稱「大台」的角色。她說,台灣大台風氣很明顯,行動中總有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人物站在「戰鬥車」上發號司令,「所以對我來說現場沒有舞台、沒有人發號司令,就是沒有大台」。
她認為「無大台」的社會運動模式是國際趨勢,早在太陽花運動時已經隱約有群眾有不願意「被組織」的狀況。直至2015年,台灣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民眾不滿決定過於草率,認為時任總統馬英九政府未經公開決策、以矮化主權方式遞交加入意向書給亞投行。
她代表的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與其他組織開會商討行動,帶隊突襲總統府,但現場群眾拒絕跟隨計劃行動。十多個領軍團體在大台上走下來個群眾談,從而得出共識。這次「現場去談、去投票」的模式已經是黃燕茹心中台灣版的「無大台」社會運動。
但她也承認台灣的社會運動是組織主導,雖然沒有大台,有份策劃的組織還是有迹可尋,與香港反送中的社運模式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別。她分析,一個曾經有領導的大型運動沒有成果後,讓群眾越拒絕所謂「領導者」,間接導致「無大台」的出現。
她又指出,香港的「無大台」需要依賴互相信任及抗爭者的默契,在運動組織的角度來看是「有點危險」,但「香港已經到誰冒出頭誰就會拘捕」的狀況。大家到無路可退之下,「無論你有不滿對方,也只好牽起大家的手」。
追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因一宗港人在台殺人案而起。台灣陸委會多次拒絕在逃犯條例修訂的框架下移交逃犯,惟港府在陸委會表態與百萬人遊行後繼續將議案直上立法會大會。不少台灣人早在6月前開始留意事態發展。
台灣24小時新聞緊貼報道,把香港的消息帶到各年齡層的台灣人,讓不少人感到十分驚訝「天啊,怎麼會這樣!」這樣連環播放有關整個運動情況的報道,黃燕茹形容是非常「特別」。她指,這畫面讓反送中運動對於台灣不是「其他地方的單一事件」,而是一個持續四個月之久的社會運動,也讓台灣人覺得「讓給中國管治看來真的不太好」。
「現在香港要捍衞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對於台灣來說可能是一個未來」。台灣會否終有一天步香港的後塵?黃燕茹指,其實自從銅鑼灣書店事件後,台灣一直害怕被吞併,害怕一國兩制,這次反送中運動再次將這種恐懼推到另一個境界。
面對內地提供經濟援助的拉攏,和守護台灣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考量,香港的反送中行動,為台灣人提供了一個參考例子。港台命運共同體不再流於空話,面對中共政權,黃燕茹深知道如果兩地都需要面對「一個有一定法治水平、穩定生活水平的地方突然間要下降」的心理準備。
初春之時,香港人還是懵懵懂懂,對於社會制度與不公漠不關心,修訂《逃犯條例》成了港人的政治啟蒙,警暴激起群眾誓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黃燕茹知道,在台港「共同體」氛圍下,仍然有不少台灣民眾認為「反送中」離自己很遠,台灣人要跟着香港喊「光復」之路,還需要時間。接下來,明年大選結果,將反映台灣人的選擇,決定明日的台灣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島嶼。就如黃燕茹所說:「台灣會不會變壞,要看2020的台灣大選」。
在抗紅的年代,香港人、台灣人光復本土,港台「煲底」相見之日何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