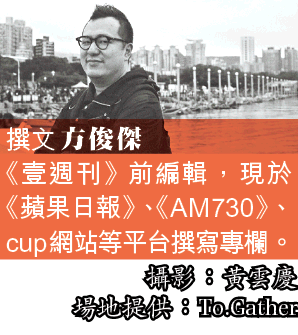
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巴打絲打聚焦在隨時被緊急取消的區議會選舉的這邊廂,那邊廂則有人選擇角逐藝發局委員。
在藝發局,廿七個委員,三個是政府代表,十四個是政府委任,由選民投票出來的十個,又是少數。電影導演陳詠燊、舞台劇監製張珮華、戲劇教師胡俊謙、鋼琴演奏家閻韻組成參選連線「Arts 4 More」。做區議會議員,至少,受薪;做藝發局委員,無償。在不少香港人眼中,無償付出,是不可能的。「是一個人生選擇。來到這個階段,你想做人安安定定,還是真真正正作出一些貢獻幫到別人?你的快樂,究竟來自哪裏?」訪問過程中,最感性的張珮華,如此解說。
競選是為了糾正制度
「近半年,尤其近三個月,我監製的兩齣舞台劇,正在公演做宣傳,買了不少巴士的車身廣告。換了在以前,在馬路撞見,想立即影張相,追都未必追得及。今次,我見過同時同地有三架印上舞台劇廣告的巴士停低。那一格畫面,對我的衝擊好大,好像連皮膚底層也被觸動了。然後,不禁問自己一句:『作為一個成年人,應該選擇繼繼着眼於物質上的爭取,還是有其他工作更加緊要?』」在張珮華眼中,所謂的life style,從此不再局限於吃喝玩樂。是覺醒。
本身做過藝發局的戲劇藝術顧問,跟同樣有公職在身的另外三人,於工作上各自認識,交情或淺或深。參選就參選,為甚麼要煞有介事組織連線?又不是民建聯。「現實層面上,藝發局的選舉方法相當特別:設有十個範疇,每個範疇的選民可以在所有範疇投票。換句話說,從事舞蹈工作的,可以投票給電影範疇的候選人。既然明知很多選民對其他範疇的候選人毫不認識,倒不如聯合不同範疇但志同道合的朋友,提出共同政綱。希望支持胡俊謙的選民,相信胡俊謙的,可以同時投票給我們另外三個。到時,入局後,胡俊謙提出的政策,至少有四票支持票,事半功倍。餘此類推。」陳詠燊接力解釋。
去年才憑《逆流大叔》完成導演處女作,入圍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算一舉成名,陳詠燊沒有急急腳找老闆投資開合拍片,反而留在香港加油,也真夠蠢。「近幾年,整個香港不同界別也發生過一些事,一直想幫社會做多點事。根本應該是每個人的責任。有些工作,在我們的崗位,未必幫到手;我們卻可以在另外的層次做到某些事。各司其職吧,每個人想想自己在能力範圍內,最適合帶來甚麼。」
除了拍電影,陳詠燊也有在演藝學院任教,每一年望着學生畢業,總有份無奈。「很想協助他們發展,但我不可能長遠地扶着他們行走。唯一可以做的,是糾正個制度。我在電影行業的時間夠長,知道個行業絕對有權變得比現時好得多。」說覺醒,陳詠燊說自己一早覺醒。「不過,很坦白,在五年前,以我當時在電影圈的成績,沒可能說服到他人。我算影圈的中生代,環顧四周,前輩們不是升到更高的層次,就是已經退下來,也真要靠我們落手落腳去撐住個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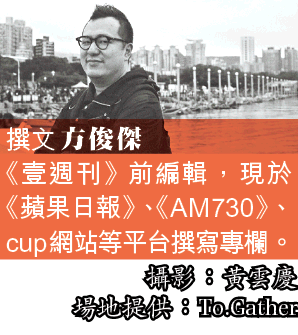
真正的是游說工作
想糾正壞了的制度,藝發局做到幾多?或者,應該問:過去做少了幾多?「又不是對藝發局不滿,只是,感受到可以做得更加好,做得更加多。」如果你上藝發局的官方網頁,看他們的簡介,大概可以理解藝發局的主要工作是分配資源和推廣香港藝術。一牽涉資源,即是錢,要改變原有制度,多數會遇到強大阻力。你看看自己間公司自己個部門,也清楚。「藝發局的工作不只將政府的資源分配好,變成不同資助計劃。我們不是只求爭取到更多錢,便算數。」胡俊謙說。
在旁的閻韻補充:「審批資助,有行內人士負責;演出時,也有專業藝評員評核。」即是對委員們不會有甚麼直接好處。「所謂的既得利益者,即是受資助團體吧。總有爭議,例如資助金額幾多,例如總有人覺得其他人要落車。藝術畢竟主觀,如何釐定?所以要設定一個申訴機制,負責監管、賞罰。不過,相對上,另一方面的糾正更加逼切。」張珮華關注的,是合約精神。
說出來也未必有人相信,偏偏又好像很合理。藝發局並無要求資助團體遵守甚麼契約。「編劇可以無跟藝術團體簽下任何合約,對知識版權完全沒有保障;演員也可以在綵排時沒有簽合約,演出前受傷的話,連保險也不受理,沒有演出便沒有收入。還想把藝發局資助的團體發展成國際化?如果想長遠發展,至少要提升到業界的專業水平吧。」
說推廣香港藝術,當然做得更不明顯。Arts 4 More想成立人才資料庫、想成立原創劇本資料庫、想替學校跟駐校藝術家配對。他們想做很多。就算當選,也只有三年任期。
張珮華又說了另外一個故事:「六年前,黃秋生是其中一位藝發局委員,他倡議過增設第11個界別:舞台及製作藝術,讓燈光師、音響設計師等工種名正言順。中間換屆,改革又停頓了。」Well,你不會還覺得意外吧。胡俊謙依然樂觀:「我父母管教很嚴格,我本質上是個循規蹈矩而紀律性很高的人,但我又偏偏天生反叛,兩種性格,充滿衝突。這讓我學懂如何在規則之下革新改變。舊路不一定最好,規則也可以更改的。」明知聽教聽話委任委員有17個,佔大多數,他們即使全勝,也只得四人,寡不敵眾,早早有心理準備真正工作不是戲劇性的傾力反抗。「我們入去做游說,了解一下他們不肯求變的原因在哪裏,有甚麼顧慮。有些衝突,可能永遠也解不開;如果,有些結,拆得到,讓大家舒服少少,讓列車向前郁動到少少;三年後,無論由自己繼續好,還是放手交給下一個也好,已經功德無量。」
以生命影響生命
將視點再抽遠少少,藝術創作,真需要倚賴政府資助?閻韻所屬的音樂範疇受惠最深:「大約二十年前,開始實施一生一體藝。今日,香港的小孩個個手持幾件樂器,培養出好多人才。問題變成如何幫助這班音樂人才?外國的樂團,很多也不需倚賴政府資助,錢來自財團。香港也有職業樂團,藝發局的撥款主要協助中小樂團,希望扶助它們成長,有朝一日也變成職業大團。蛋糕只有一件,切來切去也是一樣大小。要一個藝術工作者牽頭,弄出一件更加大的蛋糕,未必有人認同;有一個藝發局民選委員的身份,用藝發局的名義,跟商界加強聯繫,效果會截然不同。」
要商界合作,最緊要有市場。原來,不用擔心,在學校任教藝術的胡俊謙計出一條數學:「在我讀書的年代,戲劇社跟足球隊一樣,導師由常規老師兼任,教歷史科的無厘頭要教踢波、美術老師要指導戲劇學會。現時多了學校把戲劇獨立成科,多請了專業人士例如演藝學院畢業生去任教,學生的藝術水平一直提升。多了藝術教育,小朋友由小到大接觸,觀眾層自然變大。香港七百幾萬人,三百幾萬就業人口,平均收入接近1.8萬,一齣劇,一個月上五、六場,一場400座位,一定有足夠觀眾人數。」
數是這樣計,如果,香港人在將來還有心情欣賞藝術的話。「一個城市,體育跟藝術,其實不只娛樂。藝術可以帶動旅遊業,令城市更加多活力,影響超越藝術水平的衡量,商業價值本來很高。藝發局要做好的工作,只是在發展初期推一推動,之後便可以讓市場主導,自給自足。像日本政府當日發展職業足球聯賽。」
陳詠燊舉了杜琪峯作為例子:「杜琪峯導演搞《鮮浪潮》計劃,栽培出好多香港的新導演。用同一個方向去思考,很多看似細微的事情,只要對得準問題核心,就會帶來很實在的改變。不要看輕制度上的小改變,後來的人條路,隨時易行好多。」
藝術重視啟發,怕只怕政情重視洗腦,藝術教育有朝一日跟通識科一樣,未至於壽終正寢,也面目全非。「以今日的政治氣候,我們一定越來越需要藝術。」
「說藝術跟政治分開,是廢話,藝術跟政治從來分不開。藝術是甚麼?藝術是透過另一種形式去表達。不論立場,藝術也是好好的途徑去展現自己的想法,凡追求藝術的人,也是追求真善美,已經超越政治。有四種職業,可以以生命影響生命:律師、教師、傳媒和藝術家。追求公義的話,我們身在藝術家的範疇,我們有天職去完成(投身藝發局)這回事,捍衞創作自由。」胡俊謙最後補充。前面有座高山,不易攀越,但,可以甘心就此跪下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