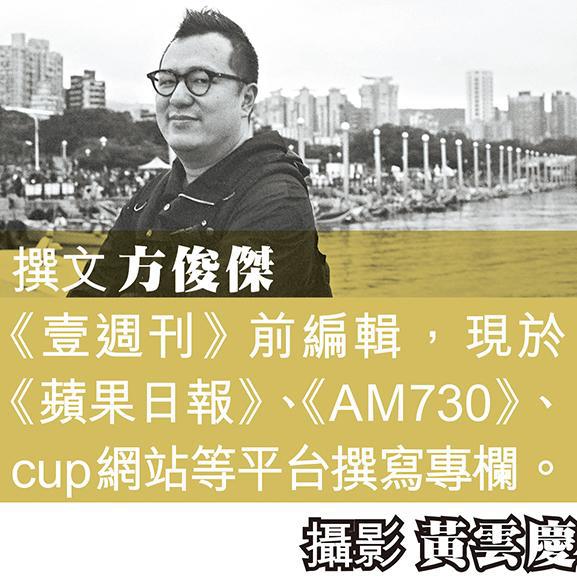
姊姊周樂娉比妹妹周樂婷早出生三分鐘。同為鋼琴演奏家,尤其專長二重奏,齊上齊落,即使外觀上的衣着打扮已經明顯營造出點點差異,要分清姊妹二人,還是存在很高難度。
因為,兩個人的人生軌迹,接近一模一樣。在同為鋼琴教師的父母安排,或薰陶下,兩歲起,已經開始永無寧日的訓練,繼而進入演藝學院,繼而過德國小鎮進修,繼而回港正式出道,除了鋼琴兩個字,好像甚麼也沒有。兩座品質被調控到接近一致的鋼琴放在外行人的眼前,很難分辨出當中究竟有甚麼不同。
鋼琴是死物,大概不會介意並非獨一無二。人類呢?我肯定不能。她們乖乖女到或者可以。「如果你說我們是溫室長大沒經過風浪的小花,我們絕對同意。最好,以後也不用經歷任何風浪。」在溫室以外的世界飽受風風雨雨的你們,會羨慕嗎?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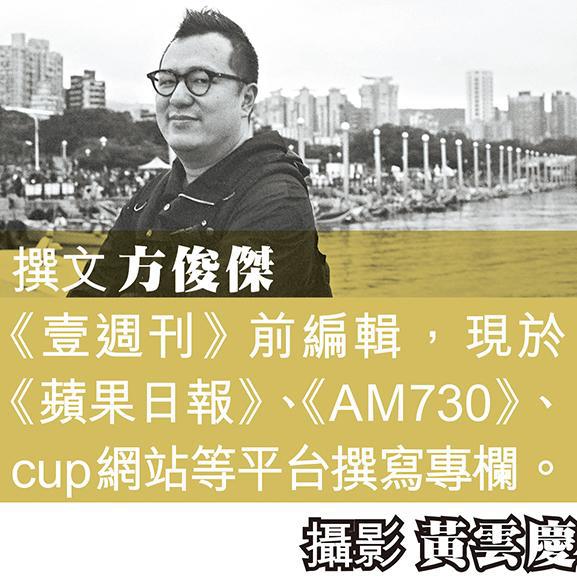
影子與影子的關係
父母是鋼琴教師,每日,學生都登門學藝。小孩愛模仿,懵懵懂懂的周樂娉和周樂婷最愛擺出彈琴手勢,在父母眼中,是興趣,更是天份。「他們立即替我們物色老師。因為,在他們眼中,做父母的,永遠教不好自己的親生子女。」本來,二人只不過似一般孖生姊妹,會被安排穿上一模一樣的服飾,以為是得意的一種。自此,連作息也一致。「跟同一個老師學琴,小學又被分配在同一班,我們親密到似對方的影子。我做甚麼,她會跟隨;她做甚麼,我又照做。」
姊姊較早熟,早學半年,一開始的時候,參加比賽,排名往往比妹妹較高。踏入中學階段,遇上樽頸,停滯不前,又剛好給妹妹追上。「有時,妹妹甚至比我更加細膩,因為她為人更加有耐性。」姊姊像有心維護,總之要說到不分高低,沒比較,沒競爭。
也不是完全沒有抗拒過。「很小很小的時候,孖公仔一樣,也介意其他人古古怪怪的笑意和目光,會刻意地分開少少,盡量不走在一起。」人大了,又發現好處遠多於壞處,至少,對自己沒信心時,下不到決定時,想放棄時,有一個接近心靈相通的人在身邊鼓勵,總好過孤軍作戰。「功利一些去看,兩姊妹齊齊參加同一項比賽,就似買了保險,一個輸了,還有另一個補上。」
現實是根本再沒有空間讓姊妹以外的閒人進入小圈子。其他同學,即使同樣學琴,不過當作嗜好一項,還有空閒看看電視劇,聽聽流行曲。對於周氏姊妹來說,童年時代的電視劇,只聽過一齣《真情》。應該因為播放年期歷時夠長。「每一日放學後,先練琴兩至三小時,才去做功課。父母將習琴放在第一位,我們自然有壓力,慢慢變成習慣,便再沒有其他娛樂。其他同學的興趣跟我們有太大分別,很難溝通得到。」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經歷相似的姊妹,根本連一個談天訴苦的對象也沒有。
相濡以沫,想感情不好也不能。

習慣服從便不辛苦
父母明顯希望女兒傳承下去,女兒要直到考入演藝學院才夠膽視鋼琴演奏作為職業看待。「在學習階段,經常懷疑自己能力。很多人建議不如早點出國找大師學藝,就說我們保守吧,還未成熟,便貿貿然出國?未免自視太高。我們情願先留在香港練好技術,為自己增值。」這種不願冒險的個性,自小已根深柢固。
究竟是出於熱愛,所以選擇?還是別無他法,惟有堅持?「由小到大,投放了這麼多,沒理由去到那個階段才放棄。其他項目,根本未接觸過,我們只有對音樂最熟悉,選擇從來不多。」因為熟悉,所以喜歡,不是沒想過在其他範疇冒險,是無法實行。組成二重奏也一樣。「孖生姊妹二重奏絕對是一項噱頭。二重奏講求心靈上互相信任,有哪一對拍檔似我們熟悉對方?有人建議過我們分開發展,可能覺得我們太過相似,再沒有新鮮感。他們只是不明白孖生姊妹在生活上如何互相倚賴。他們得一個人,獨行獨斷,當然覺得跟任何人說分開也可以隨意分開。」其實,也是不敢離開安全區。
在香港,已完成碩士課程,再沒有途徑專門地進修二重奏。是有點半帶逼不得已地前往歐洲,搬到德國漢諾威升學,兩姊妹初次遠離家園,學習自立。「人生終於第一次自己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好自由。」一直以來,父母老師說琴應該怎樣彈,她們便怎樣彈,縱使有時希望試試自把自為,最終也只會接受了事。「一反對,就會被視作反叛。習慣了服從,便不會覺得辛苦。」在德國,跟隨不同名師,何謂對何謂錯,完全倚靠個人判斷,是一大考驗。例如,要選擇留低,還是回流。
「在德國三年,靠獎學金支持學費及生活費。留低,兩個人,生活負擔就很大。去歐洲留學的,個個都想留低,生活平靜得多,不似香港壓迫。可惜,機會太少。香港有很多小朋友學音樂,個個星期都有不同表演機會。在漢諾威之類歐洲小鎮,聽音樂的人口老化。想跳去大城市嗎?要不斷參加比賽,要多人認識,至少要浸七至八年,亞洲人如果想得到歐洲人賞識,更困難。」結果,她們留低了半年,贏過一些二重奏獎項後,離開。雙手,始終只需放在鋼琴上,不用兼職應付生計。「慶幸。」

任何人也沒有虛榮便最好
周樂娉與周樂婷說,香港的古典樂市場,算大。挾鋼琴大賽得獎者的名義,最近,她們有機會跟垂誼樂社合作,跟大提琴名家李垂誼及小提琴名家姜東錫同台。特別在分開演出。回港已四年,心態出現少少改變也很正常。「會開始希望讓更多人明白古典音樂不是如想像的難以接觸。」她們很明白,大多數香港聽眾喜歡簡單,最好似流行曲,有歌詞去表達情緒;似古典樂,談結構談層次,是太深奧。試過在中環花旗銀行廣場表演,最多容納到30人,台下行人來來去去,專心的沒幾多個;也試過在文化中心,過千人入場。一直客客氣氣溫文到有點納悶的兩姊妹,竟然異口同聲:「有得選擇,一直選擇大台。」
兩個人,同樣帶點害羞帶點離地,很難想像居然自認虛榮。「虛榮?如果任何人也沒有虛榮,好得多。虛榮遮蓋了很多真實,讓聽眾只留心宣傳手法,忽略了真正的藝術。」回到文章的題目,不能從俗地用上孖生姊妹作為賣點,大概正是她們口中的宣傳手法。「如果聽眾入場是為了一睹所謂的美女,我根本不願意為他們表演。」妹妹周樂婷說。
自言較為成熟的姊姊周樂娉,果然比較包容。「很少優質觀眾,或者大量普通觀眾,給我選擇,我揀大量普通觀眾。因為,我相信當中總有人會受我影響,不會永遠停留在同一個層次。」聽眾,對藝術家來說,究竟是甚麼?看兩姊妹含蓄文靜,一生都似孝順父母聽教聽話逆來順受的品學兼優好學生,彈琴,似為滿足他人期望,多於滿足個人需要。「拍齣劇集,也希望有觀眾。如果,彈琴要彈給自己聽,幾可憐。」
「坐在鋼琴前的自己,跟鋼琴外的自己,是兩個人。彈琴時,全情投入,心無旁騖,可以表達出自己的另一面。聽眾比較似我們的分享對象。在音樂層面,還有很多可以吸收,還可以期待下次的大型演出,還可以期望跟其他的音樂家合作,怎會生厭?如果可以彈到老為止,我們會覺得好榮幸。」
一生一世,只能集中火力在同一件事上面,對於我這類既花心又缺乏耐性的非藝術家來說,想想也心寒。成長階段,當其他同學在享受青春之際,她們連外出過夜也被壓抑,連感情也要放棄,不是太大犧牲嗎?「或者,在以前,看多點漫畫,看多點卡通,玩多一點,性格會變得比現在開朗得多。不錯,整個童年的玩樂時光,是完全犧牲了。換來一些獎項,換來一些掌聲,也是值得高興的。」來到今日的年紀和成績了,還有需要為滿足父母期待而過活嗎?「成年人永遠對細路仔有要求;爸爸媽媽永遠當子女是細路仔。」說時,表情沒有變化,仍舊流露出一副賢良淑德的淑女氣質。「我想,我們今生也不會離開音樂的了。」她們不是港鐵紅磡站,人生軌迹,不需要出現太多意外。
鳴謝:垂誼樂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