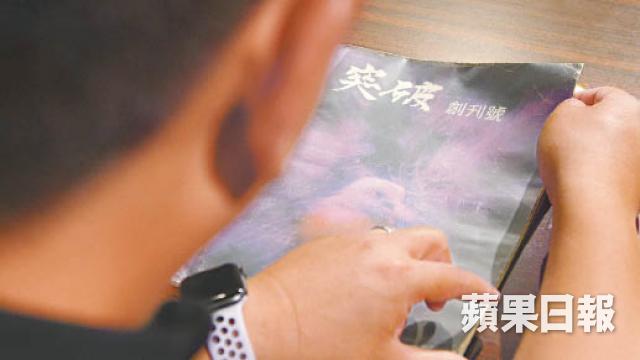
反修例風波引發的年輕人抗爭運動,至今超過三個月,五大訴求政府只回應了一個。令人髮指的濫捕、迫害,昭然若揭,香港年輕人追求的公義、法治與自由,逐漸消失。
歷史總是不斷重複。45年前,殖民地年代中的年輕人同樣處於迷失絕望之中,社會充滿各種問題,當時以服務年輕人為使命的突破機構出現,開辦月刊,陪伴年輕人成長!
突破創辦人蔡元雲醫生已經交棒給新一代,今天突破文化及創意事工總監蔡廉明(Andrew),是他的大兒子,也是本土電影《十年》的監製。
他本來像普通打工仔一樣,畢業後一心想找份穩定的工作,建立家庭,但人生的體會、爸爸的身教,最終引領他踏上和爸爸相同的路上:「今天處境比當年更唔容易,好多年輕人睇唔到有希望,但我哋仍然都要去做,呢個係一個使命!」
撰文:黎明輝
攝影:梁正平 陸智豪
《突破》──劃時代的刊物
沿着沙田醫院旁邊的山路蜿蜒直上,不久就會見到位於亞公角山的突破青年村,綠樹繁蔭,蔡廉明帶記者去到在地下的圖書室,翻開第一期的《突破》,1974年1月15日創刊,賣兩蚊,封面是破殼而出的雞仔,很有象徵性,再細閱目錄上一個一個的標題,大家都感到很震驚!──「香港青年的橫切面」、「蛻變中的香港青年」、「我們的明天」,全部都是現在年輕人最切身的話題!
「嘩,這些內容你會覺得放在今天都好有關,最好笑是有篇係講李小龍成為香港青少年偶像,我哋今日講嘅Be Water,正正出自李小龍。」這本45年前創辦的雜誌,竟然一點也不過時,簡直劃時代,「其實歷史會不斷重複,好多當時嘅問題,好多嘅處境,其實冇解決。《突破》最初係回應香港文化,帶種先知性嘅聲音,所以係劃時代,可以向唔同年代嘅年輕人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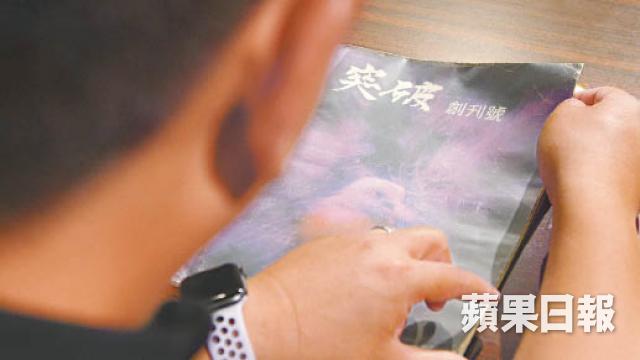
雜誌起義 抗衝社會問題
48歲的蔡廉明,在《突破》創刊時只有3歲,但他自細已從爸爸蔡元雲醫生身上,聽到好多有關《突破》發展的故事。
「香港當時經濟起飛,但都有好多社會問題,黃賭毒係比較明顯嘅問題,亦有好多迷失嘅年輕人,當時突破就用抗衡文化為主題,透過雜誌打一場街戰,希望喺香港立足一本有意義嘅雜誌。」只是,這場街戰仍未完結,而突破關心的,依然是年輕人的處境,是一種同行的態度。
「唔同年代有唔同處境,做青年工作同處境好有關係,80年代,中國要收回香港,好多人移民,當時就想起,突破作為年輕人機構,年輕人走唔到,要留低,所以就以尋根植根扎根為主題,探討作為一個中國人,根在哪裏?當時在佐敦成立的突破中心亦慢慢有書廊、出版社,又成立影音中心,當年第一套影音製作就係叫做根,我哋叫多元影像,其實是幻燈片,好多張幻燈片投影成為會流動嘅影像。」
「去到90年代,當時好想有個俾年輕人嘅地方,訓練21世紀嘅領袖,於是向政府申請地方,建立咗突破青年村,1996開始事工,最初有幾個館,資訊館、文化園、創造坊、更新園,用唔同角度回應年輕人嘅需要,都係同處境有關,覺得21世紀是屬於年輕人。」由始至終,突破的關注點,都是年輕人的生命成長。
信任──視年輕人是未來
「好多年前有個領袖訓練計劃,有句口號,there is a leader in you,我哋相信每一個年輕人,無論成績好唔好,咩背景,我哋都覺得佢可以成為領袖,需要更多嘅鼓勵和信任。現在政府所講嘅與年輕人同行,可能只係從就業、房屋出發,看似實際,但同年輕人距離好遠,今日嘅年輕人,你問佢想唔想買層樓,佢未必想,有時你要明白佢哋嘅需要係一個點樣嘅處境。」
今次反修例抗爭運動,政府完全漠視年輕人的訴求和處境,蔡廉明感到很悲哀。
「現今年輕人要求公義,覺得社會無公義唔得,要為自己未來,為香港未來,去爭取過去香港所擁有嘅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公義,但政府都唔去聽,所有訴求唔回應,只係不斷譴責指摘佢哋,唔係設身喺佢哋角度去諗,作為年輕人當然會好憤怒。」

寫遺書控訴 比傘運更悲
「這種憤怒我覺得比起幾年前雨傘運動嘅無力感更大,有幾個年輕人自殺,以表達一種絕望,好多抗爭者嘅背包寫定遺書,佢哋將條命都拎出嚟,我覺得作為青年工作者,見到咁樣係好可悲,佢哋唔應該得到咁樣嘅對待,政府唔應該漠視呢班年輕人,完全唔理佢哋,喂,大佬,一國兩制應承我哋50年不變,而過去10年我哋就睇住呢個承諾一步步被破壞。」
「以往我哋係唔需要恐懼,今日嘅年輕人就活係恐懼、活係白色恐怖嘅處境,我覺得好悲哀。」
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在美國讀電影的蔡廉明,畢業回港後一直也在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價值,當時碰着互聯網熱潮,於是他便投入IT市場,想法和普通打工仔一樣,希望工作穩定,建立家庭,也沒想過跟爸爸一樣做年輕人工作,「我爸爸成日都講,做青年工作要有個使命,佢都有問我有冇,但坦白講我當時都唔知自己使命係咩,佢冇push我,畀好多空間,叫我自己諗啦。」
重病──認清人生方向
直至一場重病,蔡廉明才認清自己的目標。「十幾年前,我有個病,個腦有個大腫瘤,我一直好健康,有事之後,我父母和太太好擔心,我記得我去做手術做咗九個鐘,爸爸緊張到衝入手術室。
腦瘤割除,頭腦也清醒過來,「回想起來,自己讀電影出身,其實都好想透過媒體,做青年工作,唔係爸爸叫我要點做,而係佢一直鼓勵我搵自己條路,無論我做咩都好,佢點都會支持我。」
「佢係出面講好多嘢,但屋企唔係講好多,但我見到佢言行一致,我係好欣賞尊重佢。」結果,十年前蔡廉明加入突破,希望藉媒體網絡推動年輕人文化及創意空間,工作的地方除了在突破青年村,也包括位於佐敦吳松街的突破中心大本營,「佐敦我哋有個創意共享空間,搵對創意文化、文創產業有興趣嘅年輕人,開唔同嘅工作坊,亦會透過網上媒體接觸年輕人。」
身為蔡家後人,他笑說不是承繼爸爸事業,只是大家一齊做,「我細佬都喺突破唔同崗位工作,一家人喺度做,唔係咩家族生意,但大家都係愛香港嘅年輕人,好想見到佢哋成長。」

《十年》──由絕望到美麗
年輕人的想法,往往打破框框,四年前,蔡廉明監製本土電影《十年》,找了五個香港年輕導演,要求好簡單,放手讓他們想像十年後的香港,然後他們各自拍了短篇影片,成為《十年》,上映後引起廣泛討論,更奪得第35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戲裏很多情節,都已經陸續在香港應驗,回想起來,他說很多是意料之外,但最感動他的,卻是父親對電影觀感的改變。
「我好記得,當年拍完《十年》,有個rough cut(粗剪),我叫爸爸嚟我屋企睇,佢睇完有幾分鐘完全冇出聲,我諗死啦,咩反應呢,佢話拍得好沉重,覺得社會唔係咁灰嘅,個刻我有少少覺得佢唔明白我哋嘅想法,之後佢都係覺得唔需要拍到咁沉重,但當套片上啦,佢再去睇,我覺得佢明多咗年輕人嘅處境,其實真係去到好絕望,佢話電影就好似聖經入面一首哀歌,我覺得有佢嘅肯定,好開心。」
訪問當日,《十年》「自焚者」導演周冠威出席突破中心一個工作坊,與在場的中學生分享電影創作,他說:「自焚者係好絕望,但係都有盼望,兩者好弔詭地同時間在片中出現,問題係,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幾多?二百萬人走咗出來,用佢哋嘅智慧同政府周旋,力量好大,唔理,要出來就出來,做啱嘅事。」
蔡廉明說:「雖然現在社會情況不斷惡化,但你見到香港人好多美麗嘅圖畫,對美對善嘅堅持,對公義嘅堅持,你仍然見到,呢個係好重要,你問我,五年之後都係會差落去,差成點唔知道,但有啲嘢依然值得我哋去堅持。」
此際耳邊響起80年代陳百強的名曲《突破》:「求突破,衝障礙,時代會因你多變改。」年輕人,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