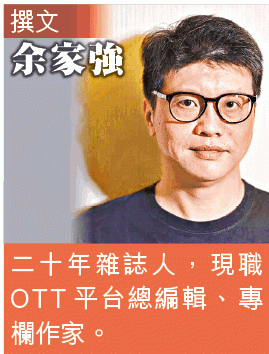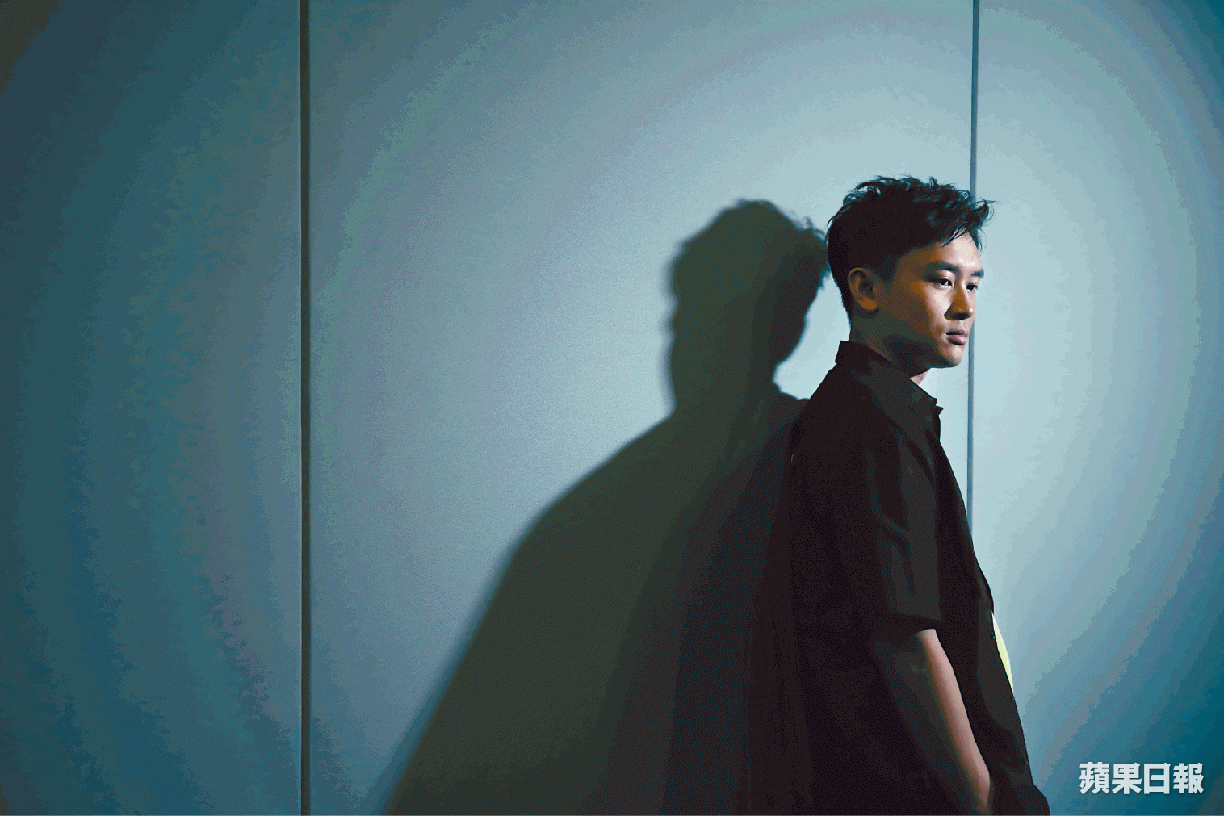
你記得他是藥油廣告的新一代福仔,你記得他是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反而無乜人記得他演了十幾年舞台劇。「聽到『新人』兩個字,好老尷。」講「老尷」而非「尷尬」,其實頗麻甩。「我卅幾歲,又不是第一日做戲。」凌文龍苦笑。
《最後作孽》中的魔童、《都是龍袍惹的禍》中的少年皇帝同治、獲獎電影《黃金花》中的自閉兒,以至即將公演《情敵勸退師》中的世界仔樂少,包辦各類小子角色,永遠被暱稱「小龍」。
像柯南──筆者一提,凌文龍即時共鳴說:「成熟的靈魂困在細路的身軀。」
成熟是,他知道世界從來艱難,沒因為近日名成利就鬆毛鬆翼。屢獲殊榮的校友,因演藝學院之名,被稱為演藝人、學院派,但求學中的師弟師妹,場地太矜貴,四年課程竟甚少有緣踏足校園歌劇院台板(主要租用給商業團體)。今次《情敵勸退師》為戲劇學院發展基金籌款,大膽起用未畢業學員,雖只跑跑龍套,率先薪火相傳意義重大。凌文龍回歸排練,興奮得像當年考入。做人,毋忘初心的好。
何必怕長不大?
撰文:余家強
攝影:羅錦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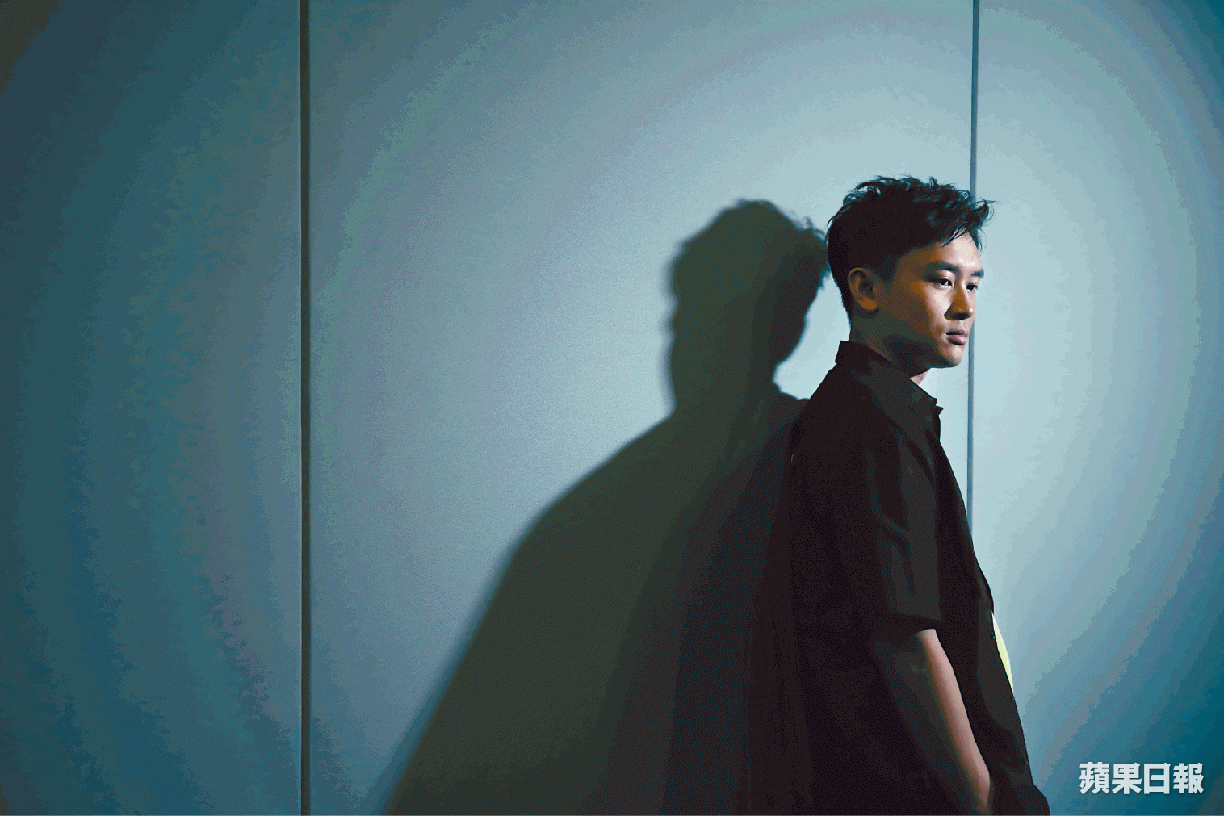
有待改善
電影圈青黃不接,歐鎧淳出鏡一分鐘都入圍最佳新人,凌文龍以十年香港話劇團全職演員的資歷去角逐,超晒班了。去年提名期間,筆者見過他,他說有得參與已經開心。如今回顧,他依然說僥倖。
以為凌文龍是個謙虛得近乎造作的偽人。
「重看《黃金花》,個心唔舒服,有些地方點解會咁做?我甚至少少竧𣉢。創造角色,行為動作上攞到節奏,但內心世界未夠豐富,情感未夠清晰。
「卻要接受,是在那階段所能做到最好的了,人生經歷過後睇番,當然可更深入,所以我說僥倖。」
原來他不斷求進步。
「今次舞台劇導演陳淑儀(男),也是我老師,他會用不同方式和練習刺激演員想法。例如他要求:『小龍再嬲啲。』我就握緊拳頭,眉再皺實啲,未夠?講嘢大聲啲,成身震晒,最後變得好似搞緊笑。老師啟發我知道,表情、動作有盡頭,有一種憤怒叫深沉,人反而會定咗,講嘢好慢,令到觀眾驚。」
流水作業的影視未必探索得咁深,難怪凌文龍偏愛舞台劇。
拍廣告(白花油)更加不用方法演技。「演員最好睇是靈魂,所以做自己就得。」無論如何,酬金比演劇賺得容易許多?「這個當然。」他笑了。
成名真偉大。
凌文龍說:「成名令我生活上經濟改善,梗係好啦。但我不覺得自己成了名,行出街,認出我的人依然不多。擴大觀眾群,從不是我目標,我只求有份參與講故事、研究戲劇。另方面,演員會否因為成名而自我膨脹呢?若果會,我的演員生命便玩完。」
怎可能?越壓得住場的才越是大明星,怎會怕出名?
「我不這樣看。大明星之所以自信,正因為慶幸自己還有進步空間。」
太和的後裔
成名的代價,包括被起底。網友發現,凌文龍參加過網上組織「太和的後裔」(指大埔太和邨)。很少有藝人如此貼地,而且是公共屋邨。網民以為凌文龍活躍於地區運動,甚至,會不會去衝呢?
實情,凌文龍自幼居住太和邨,幾年前全家認購那公屋單位,轉頭大廈翻新工程開出天價維修費,要業主夾錢,霎時群情洶湧,凌文龍立即加入監察。
倒反映凌文龍果然來自草根,是他也是你和我的獅子山下故事。
「我一路大埔大,屋企無乜錢,直頭窮啦。爸爸做司機,媽媽家庭主婦,兼職賣吓煎釀三寶。我讀沐恩中學,距離太和邨算遠,所以lunch time趕唔切返屋食,否則可慳一筆。我就每天攞媽媽廿蚊,在學校小食部吃個五蚊福字麵,儲起十五蚊,日積月累,終於……買到咁大個仔第一部PS1。」
真反高潮,以為甚麼省吃儉用的勵志故事(例如儲錢買書鑽研戲劇之類)。
卻諗深一層,快樂就是硬道理。凌文龍說,人生志願唯望將來工作唔使悶。怎叫悶呢?例如寫字樓paperwork。怎叫不悶呢?諗過做巴士司機,所以遊戲鍾意玩《電車Go》。
怕悶,也可以構成發奮原動力。
某天放學見到同學在練舞,覺得好型,原來在為drama club排歌舞劇,便去casting,入選玩埋一份,在校際比賽中獲獎,回校又重演多次。
「我讀書成績普通,難得有一樣嘢找到存在感,而且成班人仆心仆命為一件事,每個部門不容分割。咁好玩去邊度搵?」
中四暑假入讀演藝學院summer course,才知道香港有專門教人演戲的地方,最重要係應該包保唔會悶。課程完結,凌文龍升中五第一件事卻是推辭學校drama club一切活動,專心應付會考,否則根本無望。要得到,先要割捨,很禪。
在香港走藝術的路,總是如此迂迴。

「老師說,預咗將來一定辛苦,唔好諗發達。」凌文龍說:「演藝成立至今三十幾年,每屆畢業幾十個,市場已經飽和。」
那麼,樂趣究竟在哪裏?
「舞台,會勾住人的。常常說,舞台比起影視有即時交流,怎交流呢?我們並非棟篤笑並非演唱會,不能直接對話,甚至不能偷望,但可以感受到。感受到台下籠罩睡意,便加快節奏,有默契的拍檔自然會配合,所以每晚演出都稍稍不同。那種交流好正,像在講鬼古,感受到觀眾俯身向前,氣氛漸漸收緊,然後由我一下子引爆。觀眾被勾住,我也會被勾住了。」
十年舞台不及一個金像獎多人認識,但與大家所想不同,踏足電影圈,才是凌文龍冒險的開始。
首先,凌文龍以優異成績畢業,考入香港話劇團當全職演員,十年來出月薪,收入比很多同學穩定。「但正如我的初心係怕悶,建立了既定模式和安全感,來來去去同一群,突然好想試吓和外邊合作,例如我老師陳淑儀,不離開不可能合作到。」《黃金花》未上畫,他已經辭職,時間點很重要,並非貪圖富貴而走,恰恰相反。「外邊市道不太好,無咁易搵得番話劇團的人工。明白的朋友自然明白,我沒再特別解釋了。」
「上天待我很好,我本來為求冒險,但離職時總有點planning,得獎後,計劃又打亂了,原來人真不能樣樣計較planning,順着天意便好。」即使現在,接片約畢竟不及全職月薪長做長有。「休息多咗,有時放個幾月假期,個心囉囉攣、唔踏實,摸着石頭過河。」
可堪告慰的是,由PS1到PS4,今次他一早一炮過買下遊戲機,不用逐蚊逐蚊儲了,雖然並非買樓一炮過(未置業),同樣滿足。

後記
凌文龍不算矮,但配合baby face,真可以扮初中生。他笑言,這也算一種優勢,尤其當初入行,香港話劇團戲接戲,總需要孩子角色,現實裏很難有專業舞台小演員,所以他吃香。
凌文龍說:「肥仔也吃香。」筆者醒起,他師兄白只(憑電影《踏血尋梅》獲金像獎最佳新人及男配角)曾經告訴我,每屆演藝都有肥仔,而肥仔通常容易搵到工,包括白只本人。不關甚麼,就係關肥事。
凌文龍那一屆的肥仔,叫何遠東,果然也在電視彈出。
凌文龍說:「因為很難得有肥仔識做戲,又包保帶點喜劇感。有個同學瘦咗,就無工開喇,老師叫佢唔好減肥。」
正如他自己,外形上的少許不標準,反變捷徑,幾黑色幽默。「So far沒老師叫我高咗無工開。肥瘦可以變,我無得再高啦。」凌文龍還懂自嘲,戲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