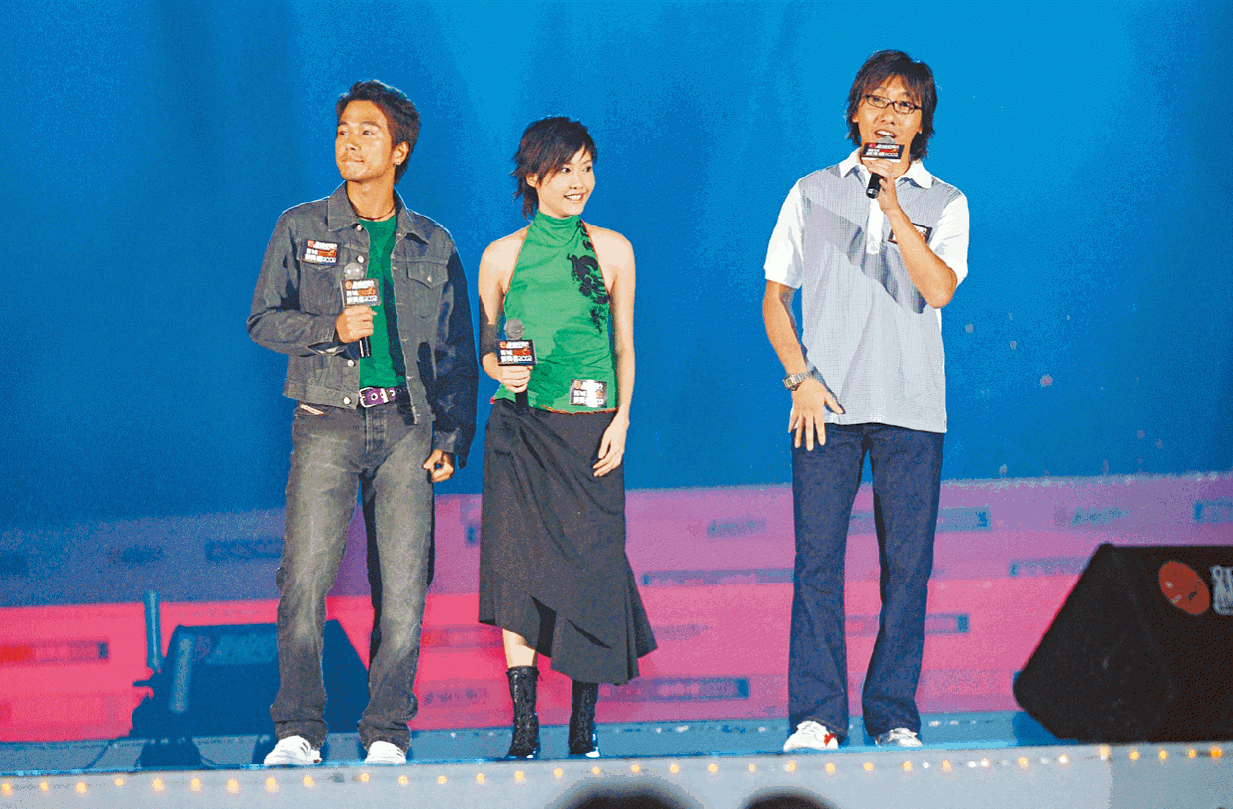
【蘋人誌】
徐繼宗是位作曲人,寫過容祖兒《心淡》、薛凱琪《男孩像你》等大熱作品的旋律。不過,還是會被娛樂版記者誤以為姓余。有甚麼出奇?「廣東歌,大家都是看詞多於看曲。」功勞落在黃偉文身上,因為大家最記得又最喜歡的,從來是一句「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好歹也曾經組過樂隊,在台灣出過唱片,徐繼宗卻非常明白自己的地位。「就算以前當主音,焦點也放在身旁的靚仔隊員。」隱身幕後十多二十年,突然自資推出新歌。不服氣?選擇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的徐繼宗,只不過盡力在香港留個位置。像投資。「我是香港樂壇的一隻曱甴。」曱甴,正名蟑螂,雜食性動物,存活能力驚人。因為,擅於演變。
吸引人的是靚仔
徐繼宗跟我就讀同一間屋邨男校。不是專出明星的傳統名校,是專出書蟲的一類。音樂堂,老師連牧童笛也懶得教,有本事叫學生帶李克勤或楊采妮的CD播播便算。「我自小喜歡音樂。不過,讀完中學,甚麼樂器也不懂,甚麼樂理也未學過,只知跟着電視劇主題曲唱歌。」
升讀大學,正路地選擇了理工英文系。香港教育從來是創意墳墓。「在大學,入學會,日日走堂彈結他,無師自通,開始試試寫歌。有位唱片公司的前輩,聽過,介紹我們去台灣滾石。」樂隊名字叫星盒子,也真有種台灣文青味。「正值台灣唱片業還在輝煌期,周華健大紅,隨便一個奀星在台灣出碟也賣過十萬張,聽到我流晒口水。想也不想,立即答應。」
對前途無限憧憬,偏偏出師未捷,樂隊的靈魂人物竟然先行離開。「他想做音樂,覺得樂隊越來越似賣偶像,重點變了,不願意繼續下去。」很有種青年藝術家的傲骨。「他本來寫最多歌,又最了解台灣文化。失去他,樂隊像斷了雙腳。」徐繼宗想過放棄,想想,又不甘心。「那時,我負責唱,負責彈,負責寫,不過,我很明白,商業上,吸引人的,是靚仔的一個。」靚仔的,是現時在電視台當主持的歐永權。換句話說,只要歐永權一日留低,樂隊便有成功可能性。「走了一個人,也有好處,逼到我肩負重任,要寫很多歌。」
唱片銷量最終三萬多,不過不失。以為陸續有來。做好第二張唱片,台灣滾石改組,推出無期。「幸好香港滾石願意出手救濟。一班香港人,做一張國語唱片,在台灣沒有做過任何宣傳,反而在香港派台,真夠古怪。也無可奈何,只好出了再算,好過倒落海。」成績當然不可能理想。為期兩年有多的台灣之旅,失敗收場。
那時的香港,陳奕迅最紅,容祖兒剛出道。不失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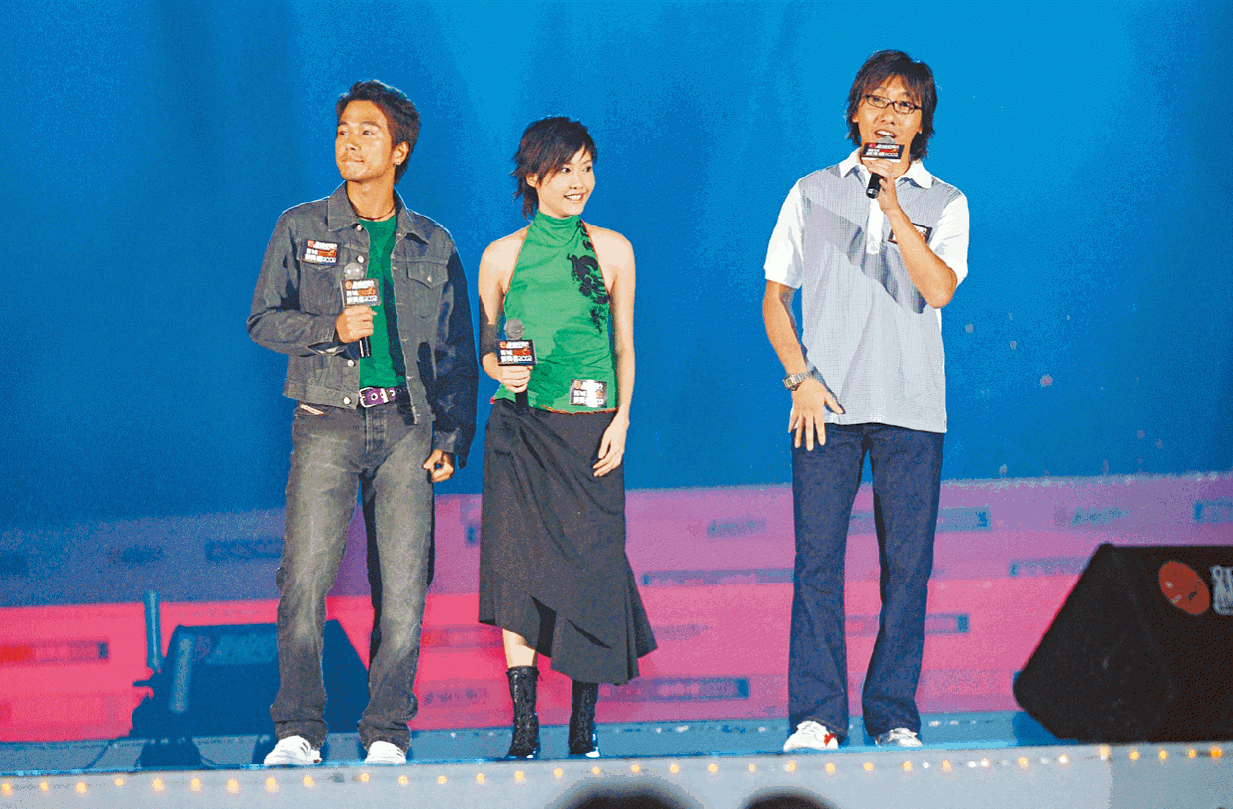
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一返港,阿媽便叫我打份正正常常的工。又不是沒有學歷,要賺幾萬元一個月,不是太困難。我給自己半年時間,日日留在家寫歌,如果半年後依然沒事發生,轉行教書,教英文。」
「好在夠窮。因為窮,跌入人生困局,小宇宙才會被激發。壓力最能夠將一個人推到另外的層次。一開始的時候,交歌給唱片公司,全部無人問津,說我的旋律太小品,太台灣,叫我聽聽陳奕迅的歌,容祖兒的歌。再寫不出,我會仆街。生活壓迫總讓人發生到一些事。」
結果,徐繼宗寫了《心淡》,寫了劉德華的《十七歲》。「未算搵到食,總算餓不死,叫做跟家人有個交代。」本來是站在台上的,唱歌的,接受掌聲的,不知不覺,變成最少品題的一個。「年少氣盛時,是會忿忿不平。為何一首歌的好壞好像完全取決於歌詞?是因為人人懂解讀文字,很少人懂得分析旋律?慢慢,開始接受娛樂圈的現實:這一行從來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遊戲,名或利永遠不會跟才華與能力成正比。一首歌,能夠發表,能夠出街,已經值得開心,不要計較製成品究竟似不似自己的想像,不要計較歌手究竟唱得好不好。有時,我以為自己寫了一首必定大爆的旋律,結果石沉大海;有時,我以為不外如是的,又會給歌手唱到火熱。每首歌也有自己的命。」
即使內心一直希望繼續當歌手,勇氣已經不再。「開始考慮成本效益。給我一小時,匿埋在一間房,我可以寫出兩首歌。別說做歌手,就是做監製,花費的心機和時間也比寫歌多太多。既然做個作曲人的成本效應最高,我處於最安全的位置,為何要刻意求變?」
沒有移民加拿大的決定的話,徐繼宗大概會繼續安於留在安全區。像你,像我。
沒有移民一回事
徐繼宗於台灣奮鬥的時候,認識了任職電台節目主持的現任太太。兩年前,擁有加拿大國籍的太太決定帶小朋友離開香港,丈夫進退維谷。「走,無嘢撈。近幾年,接了很多演唱會的和音工作,可能連續幾星期在大陸走埠,錢是賺到。開始時,想得很理想,有騷做便飛回來,現實當然不可能百分百接得下。有得有失吧,少了落地的工作,但人在加拿大,集中得多,歌又寫多了,整體計算,工作不減反增。」
「現在才發現,原來,生活得健康,很重要。在香港,早睡的話,會有種罪疚感,覺得浪費時間。在加拿大,10時上床,7時睡醒,還有時間自己煮早餐。」在香港,為了停車場的租金而肉赤,為了錄音室不斷加租而憤怒;在加拿大,生活成本低得多。「我想像不到還有甚麼不好。」
連個性也大幅度改變。「同一種生活模式,維持了好多年,好悶,一直也想變一變。留在香港的話,不會主動出擊。因為,機會夠多,反而令人消極,佛系。有危機感,才會讓你有動力想想有甚麼可以做。」埋藏了十幾年的心願,隨移民決定重見天日。「我喜歡唱歌,不難聽,覺得用自己的聲音去演繹自己的作品,才表達出真正的意思。交了給其他歌手的,不在自己控制範圍,我完全接受到;不過,總有事情想一切也是自己一手操控。」
難得來到大叔之齡,還有改變人生的打算。明知今日唱歌無錢可賺,也重新背上歌手身份。「目標是希望有人知道我是唱歌的。我走之了後,還有個位有張凳仔給我踎下。」
「移民,也想把根的一部份留低。」
坐移民監的幾年,徐繼宗需要有一半時間留在加拿大。他的飛行密度,讓他開始擔心能否達標。「現在的世代,好像已經沒有移民一回事。機票平,通訊系統方便,飛來飛去,好簡單。好多人也害怕選擇。其實,沒甚麼好害怕,將條生命線延長來看,無論作出甚麼選擇,總會是一件好事。」徐繼宗記得初入行時,捱窮捱苦,曾經很羨慕聽聽話話的同學,做海關賣保險,收入穩定。「今次回港,也有跟舊同學重聚,做海關的,已經做得相當高職級,個個也月入十多萬等閒事。他們反而羨慕我,一直以來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已經是很大鼓勵
換了我是徐繼宗的同學,也羨慕。不羨慕他住在四千多呎的大宅,也羨慕他能夠從容離開。工作性質畢竟跨地域,最近,替麥浚龍替謝安琪創作的歌曲,就在住所內錄音室完成,一封電郵後,薪金便袋袋平安。其他朝九晚五的舊同學,由香港過加拿大,等於放下一切從頭來過,根本走不動。「如果我像他們,我也不走。叫家人走,自己留低。想想,也悲哀。全世界有哪一個地方的人,要主動跟家人離鄉別井?菲律賓?印尼?」說悲哀,身為一個香港人,也真的很大機會比家中女傭更悲哀。
關於徐繼宗,還有一段回憶。
之前說過那位音樂科老師,因為懶,經常把音樂堂變成粵語流行曲欣賞大會。學生聽得高高興興,她總是一臉不屑。徐繼宗說自己在中學階段從未接受過正統訓練,我很明白。因為,根本沒有人重視過。
大約十多年前,母校校慶,邀請舊生回校參加表演晚會。神秘嘉賓是當時已創作出K歌王《心淡》的星盒子成員徐繼宗,在台上自彈自唱,校長、主任、音樂科老師,與有榮焉。學校出到一位作曲家,好像是他們的功勞。徐繼宗應該忘記了,在台下的我,歷歷在目。
「以前,會覺得編曲人把我的旋律編到一塌糊塗,明明首歌好好聽,歌手又唱得難聽,白白糟蹋了我的傑作。其實,有甚麼所謂呢?只要有人覺得在背後寫歌的人寫得還不錯,對我來說,已經是一份很大的鼓勵。」
徐繼宗可能是位藝術家。是一位香港的藝術家。即是,縱有藝術家脾氣,也要好好收藏,能屈能伸。
否則,應該早早消失。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化妝:Tinnie L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