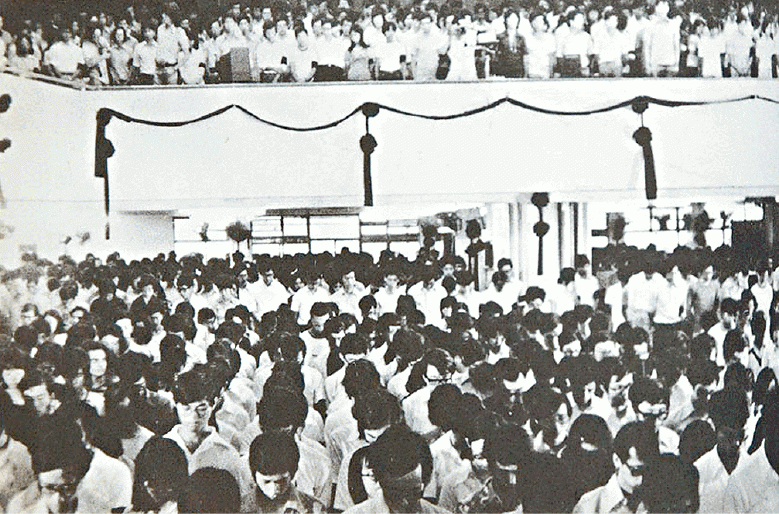
由反送中觸發的逆權運動,兩個月間席捲全港,都說屬於新世代2.0,但抗爭現場,卻不難看到耆英的身影,夾在防暴警和示威者中間;還有銀髮族大遊行,由耆英「圍阿sir」溫柔勸導要錫住年輕示威者,到輪椅陣與藥油飄香,那樣的溫馨,在劍拔弩張的今天,特別珍貴。「老人家同年輕人,一樣可以connect到」。
67歲的楊寶熙,是上世紀70年代中大學生會首名女會長,也是耆英大遊行的發起人之一,由昔日國粹派學運先鋒,到但覺「今是而昨非」的銀髮先鋒,40年過去,歲月無聲,一度遠離政治的她,選擇再次走在前頭:「已經係全民運動,行出嚟唔單止為支持年輕人,仲係為我自己爭取。」說話時總是面帶笑容的寶熙,輕輕的說。
記者:呂麗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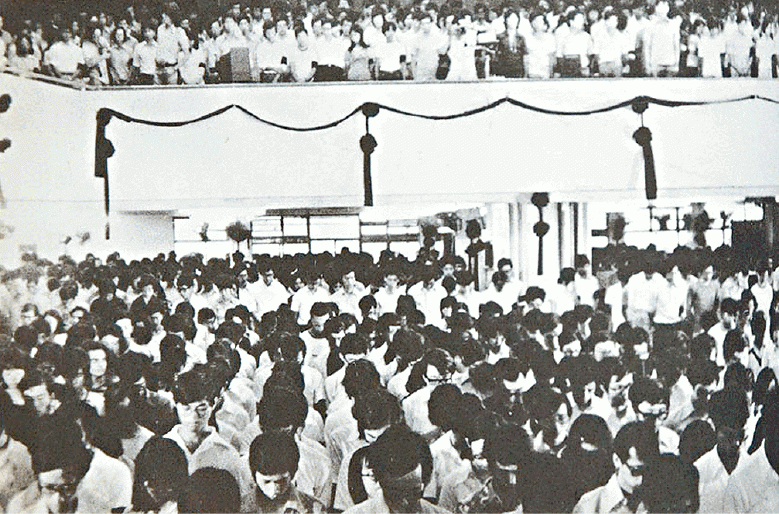



相約寶熙到她位於粉嶺丹竹坑的農地訪談,甫坐下,總腳踏行山鞋的她即拿出自家茶壺倒出熱茶,一派悠然自得。「都好幾個星期冇嚟嘞……」望着雜草叢生的田地,她嘆了口氣。這也難怪,過去兩個月,又有幾多香港人可以日入而息如常生活?就如訪問前一晚,元朗站白衣人衝入港鐵車廂無差別圍毆市民,甫坐上小巴,寶熙已急不及待瞇着眼在滑手機:「林鄭一陣開記者會喎……」邊說,雙眼沒肯離開手機屏幕。除了每星期一次的大小遊行,這大抵便是今日香港人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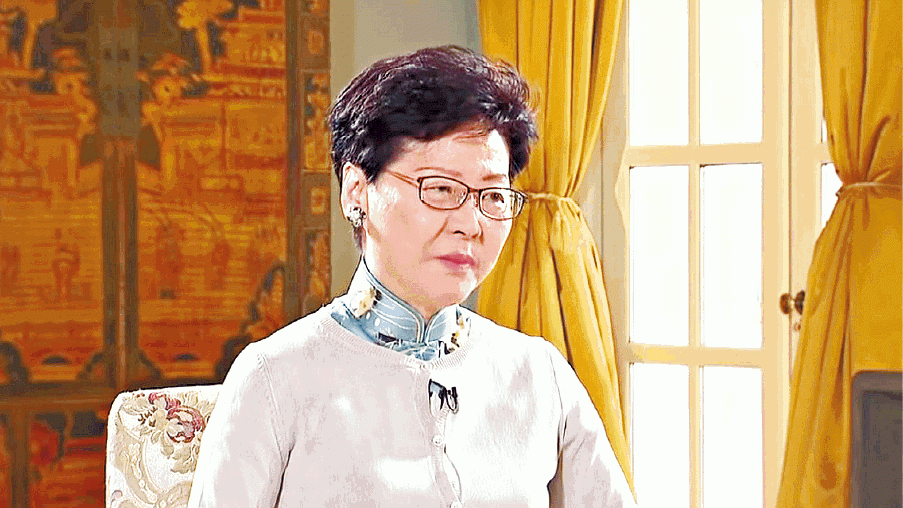
「林鄭話要認識年輕人,佢收埋自己喺禮賓府又點認識?你見到佢之前接受TVB專訪,喺個大宅一身長衫,唔好忘記,嗰時出面其實已經打到七彩。」
「搞完個遊行,好多網友add我,都未得閒處理,個facebook𠵱家有千幾個朋友,不過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係十隻手指數晒,大部份都係年輕人」。這還未計她是連登和IG用戶,以及那個有份打理的「銀髮族老而不廢」面書專頁。「你話要了解年輕人,就要試吓進入佢哋嘅世界,𠵱家嘅年輕人係好有創意好靈活,好識得利用網絡,話就話搞呢次遊行係支持年輕人,但其實係佢哋令我大開眼界」。沒大台、動員能力高,物資分配有序……在親建制的陣營中,最尋常的說法是:外國勢力干預,寶熙笑着搖頭,笑指超越想像,只怪說的人太離地。
「最初我都唔識,但只要你真正接觸佢哋,就會知喺網絡世界,咩都有可能」。對着不熟悉的新秩序,這個新老就是好奇又謙卑:「最驚奇係決定搞遊行,出咗個新聞稿,最初只有中文,有記者問有冇英文版?時間好急,有個後生就提議,話不如開個google document一齊譯,我以前有用過,但冇諗過咁用,開住已即時見到篇中文稿後面,不斷有英文彈出嚟,同一時間,一段段,好似變魔術,冇半個鐘已搞掂」。譯的人她都不認識,笑說最後悔是無拍片開心分享。
「林鄭話要認識年輕人,佢收埋自己喺禮賓府又點認識?你見到佢之前接受TVB專訪,喺個大宅一身長衫,唔好忘記,嗰時出面其實已經打到七彩」。放下身段,才可看到別人,作為兩子之母、就連小兒子也已男人三十的寶熙,是這樣想。就如發起銀髮族靜默遊行,她說也曾經歷由不理解到理解的過程。「好似7.1衝入立法會,起初我同好多人一樣,都有問號,你知我哋呢啲老人家,好怕好暴力,及至披露越來越多入面嘅嘢,你先知佢哋咁做係有針對性,唔係外國燒車胎,好似打爛投票掣、損毀立法會主席啲相,甚至係燒《基本法》,都係有象徵意義」。那脫下口罩的宣言,讓她明白闖入立法會的意義,有更多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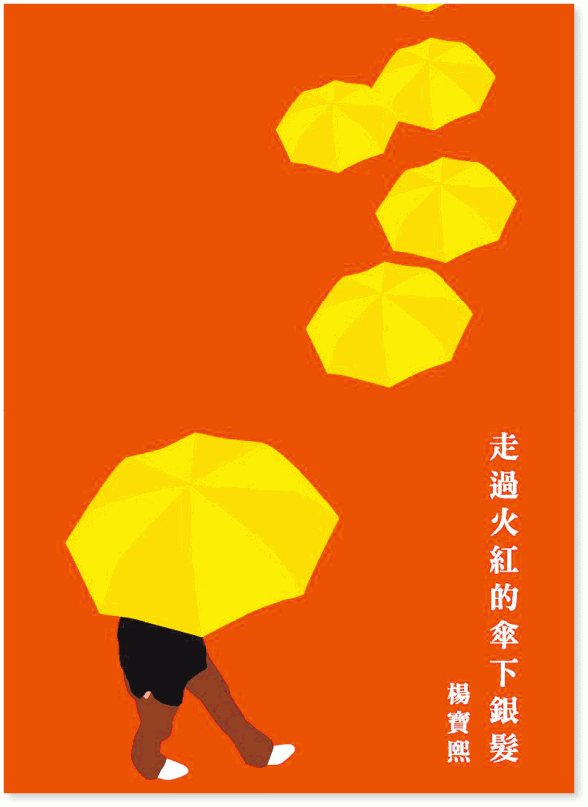
「用智慧和靈活性繼續抗爭,爭取民主自由。」
「傘運嗰陣聽好多講座,好多理論,有時都會懷疑,係咪只係理論,我哋以前讀書都冇咁多呢啲嘢,到衝入立法會,我先知年輕一代原來係有讀書,仲讀通咗」。自問已是與年輕人有connect的前進老人,受到眼前玻璃爆烈的刺激,尚且曾抱懷疑,更遑論其他與她年紀相若的公公婆婆,所以很希望「做啲嘢」,向「見到暴力會好驚的長者」解釋。「我哋係好老餅,只諗到搞遊行,仲真係諗過要登報通知人嚟,只因為時間太急,又要籌錢先搞唔成」。她自嘲大笑。
連寶熙在內四個退休人士,就連如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一頭霧水,「以為要團體先可以申請,原來個人都得,又要估計人數同定遊行路線,識得有年輕人有搞遊行經驗,就約咗出嚟傾偈」。耆英發起,年輕人加入,發展成為「有老有嫩」的團隊,前後不過一星期,寶熙說真正體現新一代「落水就郁」的幹勁。最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由最初預計只1,500人,到後來近萬人參與,誰說老人家就是愛蛇齋餅糭小便宜,不懂為自己爭取?「嗰日我行最前,邀請咗牧師同藝人打頭陣,好多嘢都係事後先知,好似有個阿婆叫警察唔好打咁大力……仲有年輕人幫遊行嘅老人家搧涼……」
單坐輪椅的都有10部,而最令寶熙感動的,是一個單腳伯伯默默擠在遊行行列中的一幕。這股溫柔的催淚彈,在木棍鐵通血淚交織的7月,自有一股以柔制剛的力量。「用智慧和靈活性繼續抗爭,爭取民主自由」。這是她重回母校中大,這是她在連儂牆,也是她期望。70年代先後出任中大學生會和學聯會長,由深紅到淺黃,這個那些年的國粹派,不諱言時代不同,但有些感覺卻很熟悉。「明明係好攰,都一定要做嘅衝勁」。寶熙謂政治從來複雜,但她慶幸,走過火紅年代,以為雁過無痕,但一些美好的價值,原來早植根心中。
「嗰時仲有盲人工潮,睇到好多唔公平唔公義,好想改變。」
「我鍾意耕田,係因為好想知道一粒米係點樣出現,就如文革嗰陣要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到現在我都認為係啱嘅,只有咁樣,你先唔會離地」。出身小康,五兄弟姐妹之中她排行第四,做會計文員的爸爸,是30年代的華仁番書仔,但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他,充滿民族感情,家中少談政治,但一份《大公報》卻不可或缺。事實上,與當年很多懷抱理想的文藝青年一樣,愛看《70年代》雙周刊的她,在火紅年代,積極關心社會,參與中文運動,又為保衞釣魚台上街,「嗰時仲有盲人工潮,睇到好多唔公平唔公義,好想改變」。
也許就如國學大師牟宗三曾所說: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大師之言,某程度應驗在楊寶熙身上。71年考進中大,主修經濟副修地理,認識社會、關心祖國,理所當然。畢業那年,她就在國粹派老鬼鼓勵下組成內閣,成為中大學生會首個女會長。「嗰時嘅大專界,基本上係一片紅」。她是親中的國粹派,與當年社會派時有衝突,但作為「被揀選的人」,就是明知只是棋子,為達致認定的崇高理想,也是義無反顧。卸任後她又當上學聯會長,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月18日學聯舉行追悼會,寶熙當年就以會長身份致悼辭。
只是,狂熱的信仰,隨着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倒台而徹底崩潰,偉大政治領袖背後的腐敗,被越揭越臭,是成王敗寇下的必然結果?還是本來已百病叢生,只因被狂熱蒙閉了雙眼?寶熙說不知道,但現實是倏忽失去精神支柱,有人傷心自殘、有人憤怒割席,而她,就選擇逃離。「有一段好長嘅時間,我係去政治化,唔想再談政治」。退任學聯會長後,她當老師、做主婦,在社會服務中心兼職,去嘉道理農場推廣有機耕作,建立「共同購買點」支持社區農業,成立社企「自在生活」,仍然是先鋒,卻已是農業先鋒,由紅變綠,就是要遠離政治。

「地產商點解要囤地?以為搞環保可以不談政治,但原來背後仍係有好多政治。」
「89六四之後嘅一個月,係我個細仔出世」。臨盆、坐月,百萬香港人黑衣上街,她沒參與;就算是曾經引頸以待的97主權移交,她也再沒感覺。「可能我太完美主義,政治都在講妥協」。只是,少年時代植根對美好價值的追求,到底還是無變。大學畢業後,她教過五間中學,最長一間也不過五年,最經典莫如在五育中學任教時,因校方無理禁唱抗戰歌曲自我審查,而與多名老師集體辭職抗議。當年的「逆權老師」沒人敢請,她就跑去教私校。縱然政治立場不同,過去高舉的價值,她依然相信:站在雞蛋的一方,訪貧問苦,與受苦難的人同行。
只是對政治,她還是敬而遠之,直至後來加入嘉道理農場,協助推動有機耕種,她才發現,政治是無處不在。「地產商點解要囤地?以為搞環保可以不談政治,但原來背後仍係有好多政治」。08年,港府企硬清拆菜園村興建高鐵車廠,她開始感到痛,以普通參與者身份擠在年輕抗爭者之中,不禁反思:「一直以來嘅訓練係好策略性,啱未必會出聲、有效果先會出聲,今日睇番,我反而覺得係我嘅缺點」。看到認為對就奮不顧身的年輕人,她特別感動。那是政治、也是理想。
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群70年代的社運老兵出來絕食,聲援學生抗爭,那條九人的絕食名單當中,就有楊寶熙,一條繫在頭頂的紅布,恍如隔世。及至雨傘運動,埋藏多年的感覺又再湧上心頭。「由1975年做學生會,到傘運之後,剛好40年,搵朋友傾,梳理咁多年嘅諗法……」直視自己的過去,由逃避到覺醒,是為《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的緣起。「今日的我係打倒昨日的我,係唔好受,但我希望林鄭都可以拎出勇氣,唔好再逃避」。千帆過盡,寶熙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