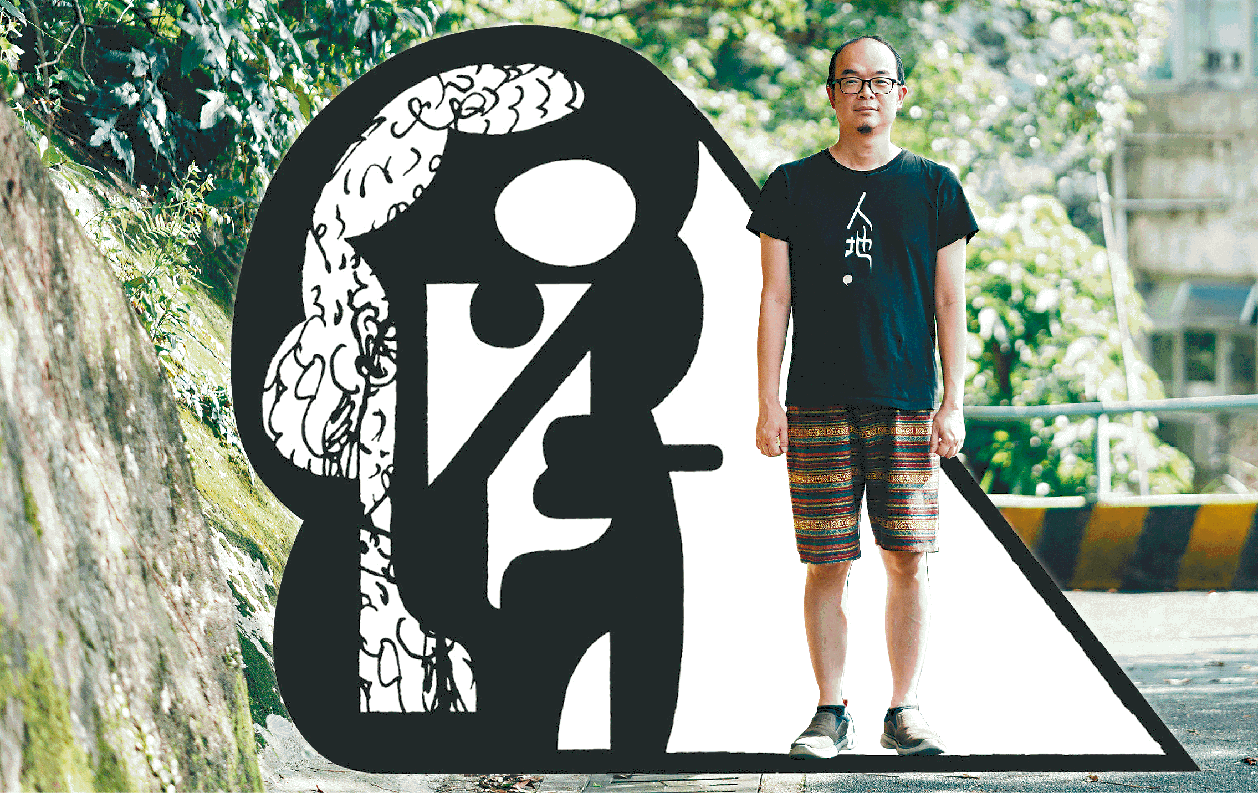
藝術家住所果然暗藏寶物,如叮噹百寶袋:中五上課時在櫃桶底偷畫的漫畫、尊子真迹……還有袋玻璃碎,來自7.1衝擊後的立法會大樓。
從露台遠眺,還依稀見到壁屋監獄。「陳健民、黃之鋒都住過喺嗰度。」藝術家白雙全指向遠方。
他說,最近容易流淚。
各區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訪問前一天他剛參加完沙田遊行。遊行、回家、在梳化看直播、看到睡着——是白雙全這陣子的日常。有時在直播看到有人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眼淚便不自覺流下。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喊同depressed冇關係,depressed 嗰陣係喊唔出。」眼神篤定。
沒有眼淚的日子,是在雨傘運動後。當時的白雙全像掉進黑洞,找不到情緒出口。
五年後,反送中,他的世界不一樣了。
撰文:鄭晴韻
攝影:陳傑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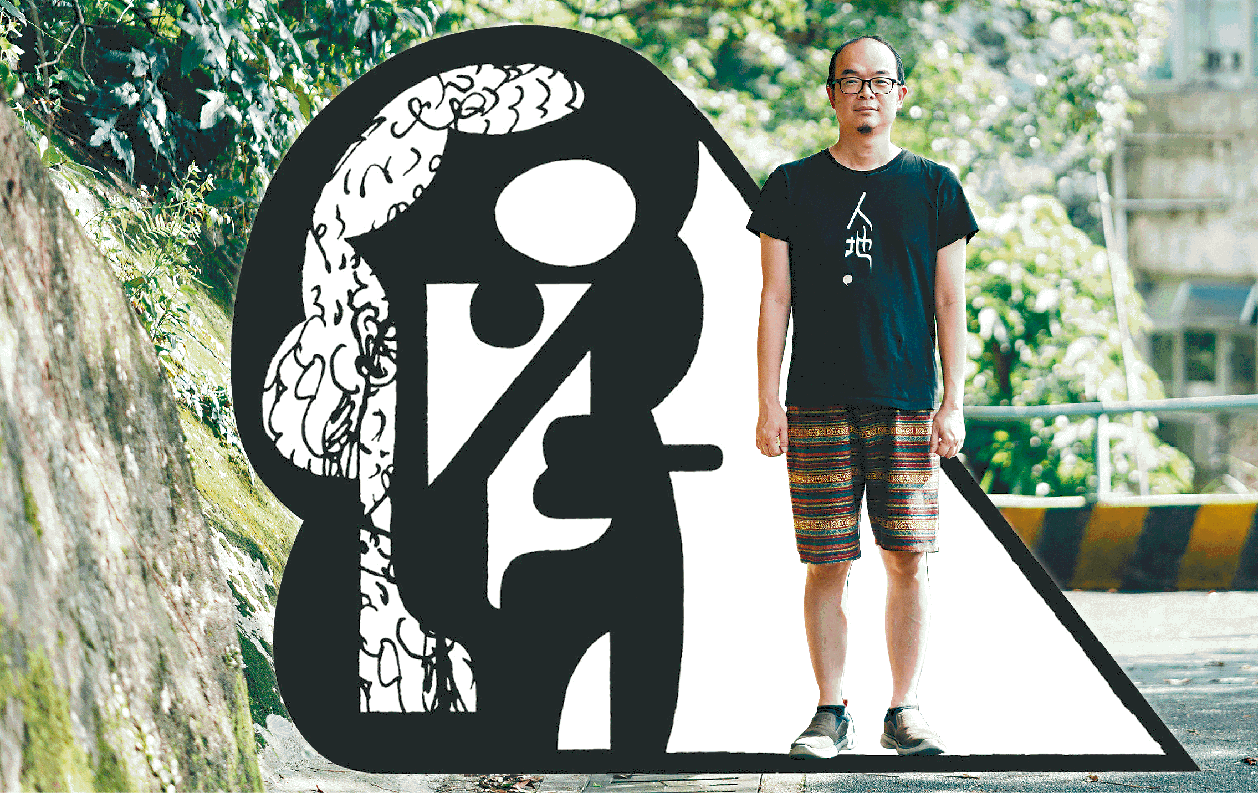
幻滅
「好記得細個幼稚園老師當住全部同學面前舉起我幅畫,話我好有天份,因為所有人畫嘅火車都係向前行,我嘅就識轉彎,有perspective仲識轉彎!」小小白雙全應該沒想到幾十年後自己會成為全職藝術家,在《明報》專欄發表作品、到世界各地辦展覽、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白雙全1977年生於福建,七歲移民香港,200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他習慣身邊常備筆記本,憑直覺記下生活中的靈光一閃,例如一灘水與一張用來吸水的Tempo紙巾。「嗰個moment畀我睇到一個sculpture嘅轉化:由水變做圓形、然後方形;由不規則的水,變成固定形狀。」
從一灘水到巴士站牌的數字、硬幣、收據,都可以成為作品。密密麻麻的筆記本,跟他看見的世界一樣,豐富多元,充滿提示。
但這持續了十幾年的創作狀態,雨傘運動期間完全停擺。
「我發覺坐喺旺角佔領區,我冇辦法再攞起支筆……真係無mood寫,唔想再做。」白雙全邊說邊舉起筆記本。取而代之,進駐他心情的是抗爭。他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坐在旺角佔領區,跟着群眾行動,叫口號,「好亢奮」。
過山車抵達最高點,無預警急墜。那一下離心力,最可怕。
佔領區清場後,那藝術家獨有的敏感,使白雙全的身體和情緒馬上反應,「對日常生活冇咩興趣,最鍾意就係瞓覺,匿喺張床。」還有聽謾罵不斷、吵鬧的網台節目,尋找可以維持亢奮的刺激。這種狀態大概維持了大半年。
「再咁落去真係唔掂,好難受。」
他說,那段日子,像一個美好世界的幻滅,然後飄浮半空。「好想有個platform畀你可以企得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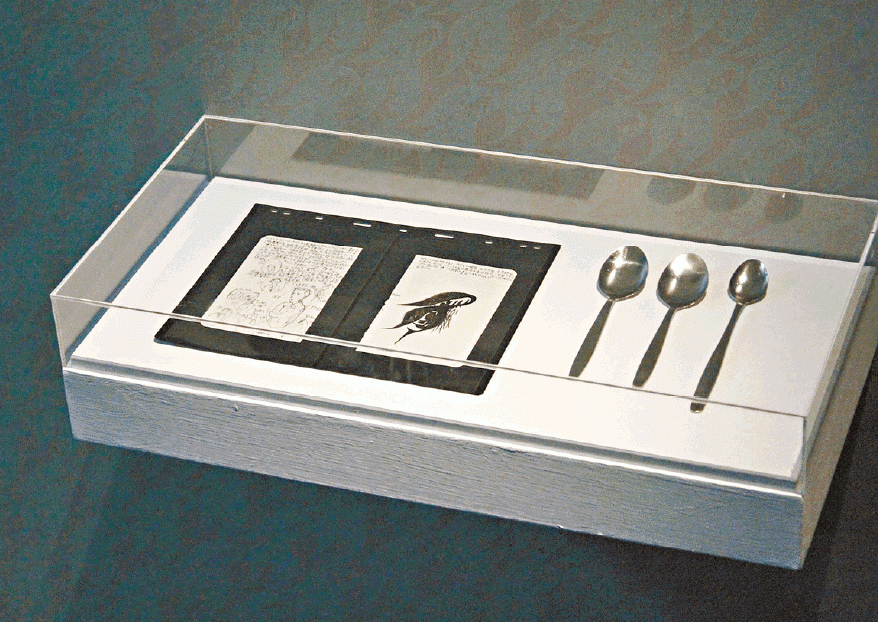
療癒
白雙全開始找療癒方法,慢慢重新建構對世界的想像。
療癒方式既有以excel表格規律地記錄及整理每日雜亂無章的生活,「用觀者嘅角度睇番自己」,亦有到法院聽審。
2017年某日下午,白雙全獨自在街上蹓躂,漫無目的,藉由走路「釋放焦慮」。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身處觀塘法院公眾席。純屬偶然。
「入到去我發現,我想要嘅嘢好似係晒度。」冰冷、肅靜、莊嚴的空間,在場人士的嚴肅,讓白雙全自然而然進入一個專注、緩慢的狀態,「嗰種焦慮好似凝固咗咁。」
接着,他開始旁聽一系列佔中案件:重奪公民廣場案、蠔涌爆炸品案、旺角暴動案……藉由抽絲剝繭的審訊,他重新組織並梳理整場運動的記憶與看法,再用自己的角度去接收。
心靈受傷的藝術家,坐在公眾席,任由手裏的筆在筆記本上游動,記錄腦中浮現的圖像,扶乩般地自動書寫;壓抑的情緒得以釋放,變成符號,產生出一種新的創作語言。解讀符號時,白雙全會用掃描器把圖案放到極大,觀察情緒在每條線上的微小波動和變化,慢慢調整混亂的內心,與外界建立聯繫。
在法院創作的同時,白雙全能夠近距離接觸佔中案的被告,聽見他們的聲音,共處同一空間。「呢種physical接觸,係我認識世界嘅關鍵。講得哲學啲,就係對抗虛無世界時,佢畀到我一個最底層嘅實在。我嘅創作只係滿足緊呢種基本需要。」
「所以我會收集『華仔』嘅羹。」
華仔是旺角暴動案九名被告之一,常被庭上控方證人警員強調「身材比常人矮小」,散庭後總是獨自離開。有一次散庭,白雙全主動約華仔食飯,自此兩人偶爾當飯友。每次飯後白雙全都會收集華仔用過的湯匙,洗淨,做記號,放入家中的餐具盤。家人至今都無法辨識出華仔的餐具,只有白雙全自己知道。家中用來發蛋的唯一一雙黑色筷子,也是華仔用過的。
「呢啲嘢好似好無聊,好變態,但我話畀你聽,真係好有用,好直接connect到,而且係真實嘅。」每次食蛋,都想起華仔,很親切。

連結
久而久之,白雙全與華仔成為真正的朋友,甚至在困難時會想起對方。有次華仔在街上被打傷入院,他沒有找家人,卻致電白雙全,要他幫忙帶換洗衣物到醫院。「佢有需要嘅時候,真係會諗起我。」那真實經驗及關係對白雙全而言,很重要,是他世界構成的一部份。
後來,白雙全將旁聽旺角暴動案時畫下的符號,製作成「噩夢牆紙(No.DCCC901-16#15):蛇吞熊圖」——一條蛇把熊吞下,後來變成一隻單眼怪獸,三個殉道者則站在白熊體內。暴動罪成的華仔,也許就是殉道者之一。
每幅抽象圖像,都隱含着白雙全的生命經驗,如何一步步重建世界。
「《噩夢牆紙》就係咁㗎咋,我係度講緊我點樣建構我嘅世界出嚟。」他相信作品本身「有種神秘的healing力量」。
從2015年開始聽審,一直至今年4月29日的陳同佳案,他去過法院140次以上,繪畫加文字紀錄超過360頁。不再聽審,不是因為疏懶,純粹因為痊癒。
然後緊接着就發生的,就是反送中。
人生有太多巧合的白雙全笑道:「時間真係夾得啱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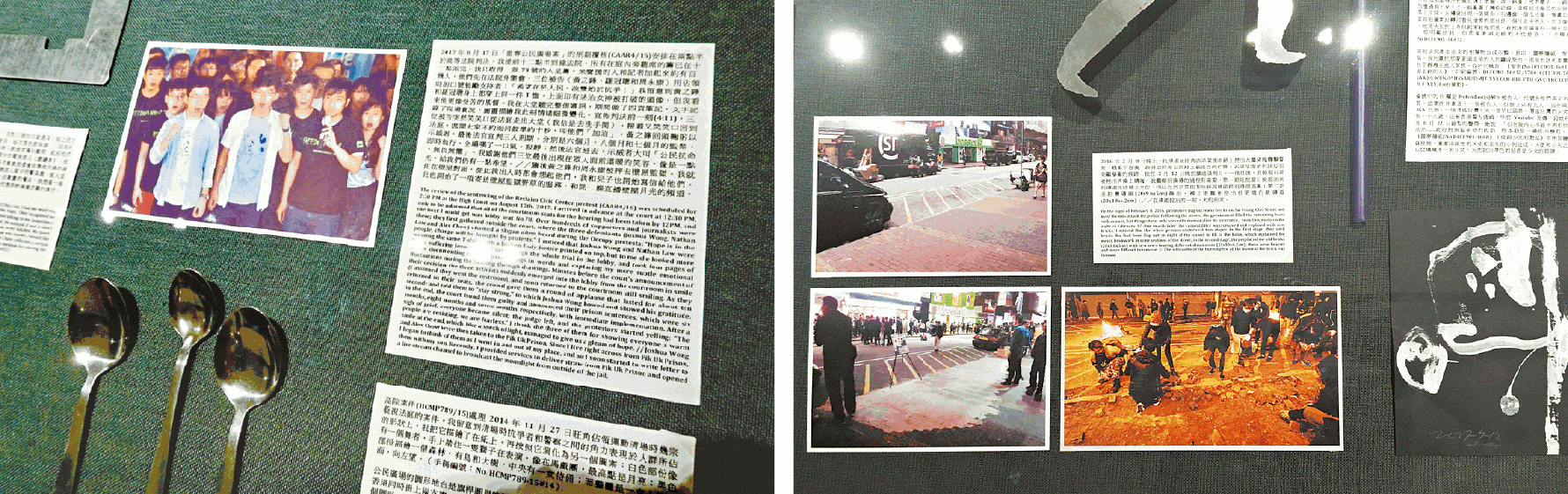
從絕望痛苦層次 融入創作
6月以來,幾乎每次反送中遊行白雙全都有參加。就連7.1立法會衝擊,他也在示威區留至超過晚上10點。
6月16日,在200萬+1人遊行那天,白雙全看着佔滿夏慤道的人群,感覺像回到雨傘運動。We'll be back。他來回穿梭夏𡰪道兩端,看到路面的白色大箭嘴,就坐下來看前方人群,然後在箭嘴前端寫下心中浮現的字眼:民主、自由、法治、公義、互助……共寫了20個箭嘴。當中「民主」和「自由」各寫兩次。6月21日再次佔領夏𡰪道,他把「民主」改成「普選」,一個具體訴求。
一周後,這些箭嘴的照片出現在《明報》專欄,又一份報紙作品:「在夏慤道上開啟的20個箭嘴。」
再次經歷一場大型社會運動,他發現:「我係去到一個狀況,自己都幾詫異,就係過程中我識得拿揑自己情緒:放、收;幾時要闊啲睇,幾時要畀佢(情緒)包多啲。」連亢奮,也收放自如,不像五年前「高呼咗七十幾日」,「意志操作多於理智操作。」
他認為這些轉變是因為雨傘運動後的創作重建了自己的內在世界,讓自己再次面對類似的社會處境時,「已經唔係以前個狀態。」過去他將藝術家的身份完全放下,只想當運動中的一員,「一齊嗌、一齊行」。經過這幾年的沉澱,他意識到自己其實很怕被群眾淹沒,「好想可以single out。」

感應
「Single out」,不是要當大台或領袖,只想在群眾裏感受到的自己,強烈一點。既是群眾,也是藝術家,甚至治療師。
白雙全很清楚自己這次分工,「既要在群眾裏面,同時需要抽離。」在群眾無法處理情緒時,能夠去安撫他們,幫他們將情緒釋放。「我過去幾年嘅創作可以話係build up緊呢啲嘢。」
話說一半,白雙全忽然掏出一袋玻璃碎。「嗰次立法會畀人撞爆玻璃,清場時我執咗好多」。在藝術家住所看到立法會玻璃碎,好神奇。他計劃用它們做一個療傷課程,名為「玻璃心素描班」。他會把玻璃碎會放進黑色袋,讓參與者伸手進去,在看不見玻璃碎的情況下畫出來。
「我想佢哋用心感應佢,畫完後我哋就share,一齊將某啲情緒攞出嚟。」
他還有一個平時常背的藍色尼龍袋,下方有一行褪色的字:「一個湖,是一片很大的浮雲。」袋上,兩條皺紋膠紙貼成一個十字架。這個十字架原來貼在立法會示威區某根柱子。7月3日清場時,唯獨那十字架,沒有示威者帶走。白雙全想都沒想就將它撕下,貼在袋上,救回家。
白雙全說,十字架很簡單,所以力量更大。
「真迹先有力量,呢個係我信念。」就像當年走進法院,遇見那些曾經參與運動的人。
雨傘運動至今,白雙全深感在社會運動中,藝術無用。但在運動與運動之間,「藝術就好似一條死唔斷氣嘅線」,連住那些重要經驗、感受以及思考。
「我覺得自己又回到最初那開放、充滿可能性的創作世界,但呢個世界已經多咗層layer,有苦澀、痛苦,亦知道世界有絕望嘅部份。」
而他能做的,就是將絕望中呈現的想像融入創作。
此刻藝術家的筆記本,寫滿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