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權運動爆發一個多月,如果有勤工獎應頒予譚文豪,44歲的他一直與示威者同行,想必冷落嬌妻,他說:「如果她接受不到便不會嫁給我吧!」綽號bite豪,分享夫妻之道時chok bite:「總之她說甚麼都是對的,即使她說地球是四方形你都要同意,不過有點兒像籃球,那就夠了,你不要和她爭辯,某程度這令人生更容易過。」
一次死佬又上街,譚大嫂下最後通牒:「你下次出去講一聲好啊,否則我當你包二奶!」譚文豪透露其實妻子很信任他:「我老婆非常放心,因為沒甚麼比從政安全,有何行差踏錯,哪用我管你,大把記者幫我監視你,《文匯》、《大公》還不立即做你?」
訪問就由信任談起,今次運動示威者與議員互信,7.14譚文豪為了令群眾相信沙田站還有列車載客,更揚言跳下路軌,他沒有不軌,只有跳軌。
撰文:陳勝藍
攝影:王子俊

新城市當晚廣場如戰場,7月14幾乎西曆變農曆(鬼節),其後示威者在沙田站上車準備離去,卻有傳那是最後一班車,兄弟爬山齊上齊落紛紛擋門,氣氛有如屍殺列車。譚文豪跟港鐵交涉後行車回復正常,但職員費盡唇舌也不能取信於群眾,譚解釋:「不要忘記港鐵七成多股份是香港政府持有。當時我跑到車尾,看見的確有另一列車等候駛進月台,車站經理也親口向我承諾有車,我才逐個車門解釋,勸人放手讓車門關上,否則後面列車不能駛入,接載不到其他人。」
其間有人問他如何確保下一班車必定停站載客,他斬釘截鐵地道:「下一班車如不停站,我會跳下路軌令列車停下,後面的人一定可以離開,信我!」之後果然有車,他在訪問中說:「我知道下一班車會來,但我仍走到車頭,如果離遠看見下一班車不打算停下,我真的會跳下去,車站經理在我身邊,這情況下他一定會叫停列車。雖然你會說我知道他會叫停,即是我沒有必死的決心,但我不是要必死,我是想盡任何辦法一定要截停下一班車,讓人們上車。」
承諾不能背棄,信任不能出賣,「這是我與示威者——我不認識他們——的信任,他們信得過譚文豪這個人,既然應承了就要想盡任何方法,即使跳軌都要截停列車,他們信得過我會做,而我的確有這個準備。」今個夏天香港人的互信程度達到新高,政府誠信則跌至新低,他說:「我信得過學生不是要搞事,學生信得過議員會出來保護他們;我們也信得過捐出去不同的資源正正經經應用則用,幫助被捕人士;我們信得過義務律師,當有事WhatsApp他們,打給他們會即時出現;我們信得過每一次都有一群社工出來從中協助。」
大家甚至將血汗錢交給誰人牽頭也不知道的連登在外國報紙刊出廣告,包括本文主角,「不是小數目,不是一萬幾千、十萬八萬,是六百幾萬,信得過(負責人)不會把持不定挾帶私逃,很困難也很厲害,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幾多地方做得到。」今次運動譚文豪像大家一樣出錢出力,大事不用說,即使6月9號晚警方在灣仔圍捕示威者,只有他一個議員在場;7.7在旺角與警察理論;7.10油塘連儂牆爭執他又去調停,「總之6月9號至今可以參與便盡量參與,你不知道幾時需要到你,但你一定要有個心態,真的需要到你的話盡快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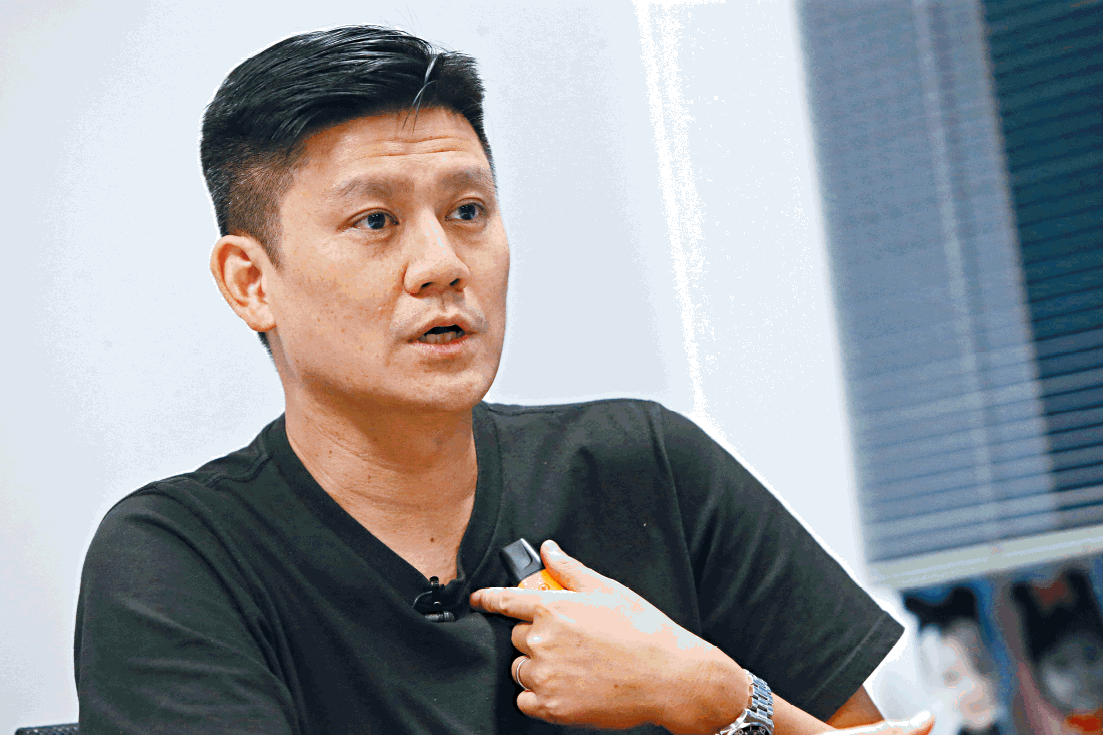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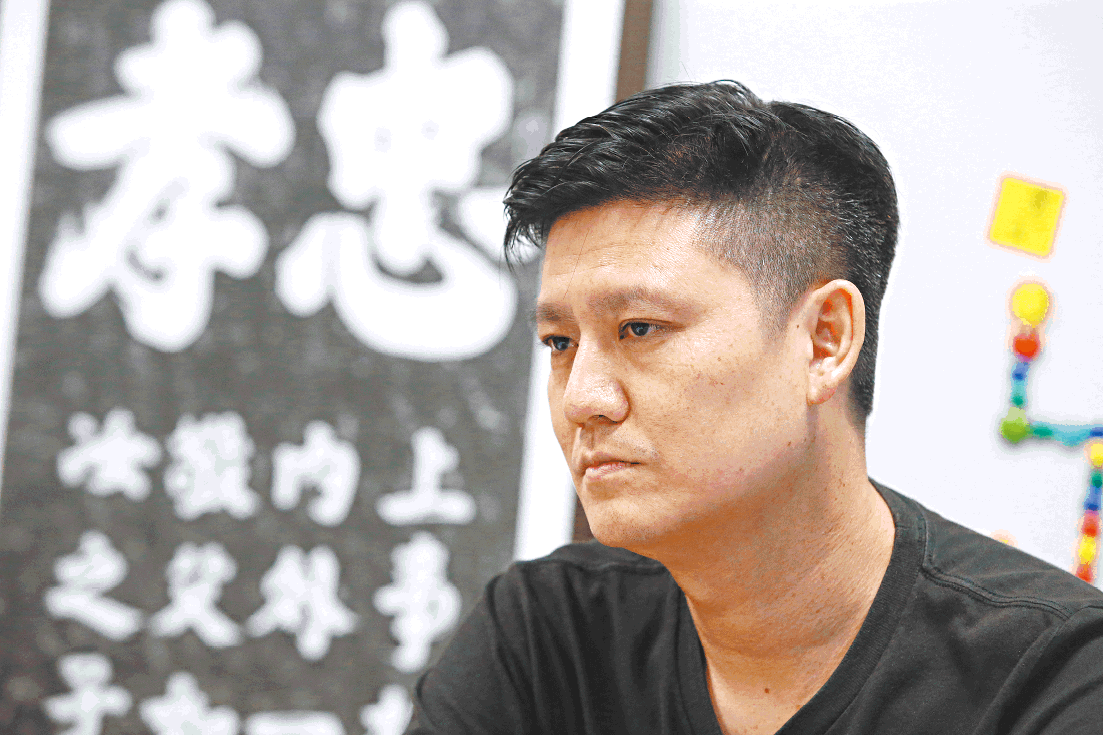
陪伴 也是同行方式
一直與示威者同行,他解釋群眾人多不怕差人,退場時人丁單薄才兇險,傳媒又走了,警察為所欲為。例如6.26包圍警總,好些人堅持留守,譚文豪只好誓死相隨到天明,「很多示威者未必想聽你意見,只想你在場陪着他。你可分享自己想法,但你不能強迫人參與不參與,這份尊重很重要,我必須承認民主派今次學會了,2014年絕對不是這樣。」
6.26當晚圍捕歷時兩、三小時,他在場確保警察沒使用過份武力,「你可能會問我為何不擔心警察打我,其實他不打我,我沒有受到比較嚴重的暴力對待,不是因為譚文豪,也不單單因為我和他講道理,他不能駁斥我,更重要是我有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而這個身份不是我的,這身份是市民的,既然市民授權我得到這個身份,我就要將這個身份發揮到淋漓盡致,協助整個運動,協助香港。警察不是怕譚文豪,他們有所避忌的是一個立法會議員,如果今天我沒有這個身份,轉頭已被人挾去後巷打。」
從政 為想服務市民
多年前他已希望為香港做很多事,「我怎樣做到?譚文豪去做是做不到的,要靠一個議員去做,所以我便利用這個身份,行使我的權,令香港得到改變。我這個信念幾強烈,希望有一天我不再從政或者百年歸老,我仍然夠膽講這句說話:我譚文豪不是為了議席所以服務市民,我是因為想服務市民所以我要得到議席。」市民大抵看得見,6.12晚上他與楊岳橋走在金鐘,沿途群眾鼓掌,「我可以告訴大家,那一刻我的心很不舒服,因為我認為當時的掌聲沒有一下我deserve,一下都沒有!」
手段與目標要分清楚,當年加入公民黨不是目標,「我不管這是一個組織一個黨也好,一個議席一個議會也好,這不是你的目標,你的目標其實是背後你想做甚麼,而你想做甚麼的時候你需要不同工具,你便選擇一些你覺得合適的工具。」同一道理民主也是手段,希望通過民主締造公義公平社會,道理沒錯,可是譚文豪的正職是飛機師,凡事考慮所有可能性,選擇最好的一個作目標,這在立場先決的香港選舉注定吃虧,故此之前多次參選區議會落敗,他透露如果2016年立法會也敗陣便不再選。
「(考慮可能性再作決定)這是正常三角形的思維模式,但在選舉論壇要倒轉來,你要先講立場,甚麼是對,甚麼不對,有時間才慢慢論述為何有這結果,這跟我做了40多年人的思維頗不同。」終於2016年勝出,立即更改航空公司工作,保留機師牌照但不用飛行,留港做議員。譚文豪不想記者着墨太多他為議政犧牲財政,畢竟立法會薪酬也不少,但的確不及正職減薪那部份,而且機師生涯不如律師靈活,「律師可以開律師樓,飛機師不能開航空公司嘛!」
飛機師的爸爸是的士司機,譚文豪生於草根,長於葵涌木屋區,後因火災遷往安置區,廚房門外搭,廁所公家用,如此十年才搬到沙田博康邨。兒時頑皮已極,將粉筆磨成粉末放在吊扇扇葉上,一開動有如今天催淚煙;街上拾起溪錢放進同學書包、抽屜。小學四年級被老師木乃伊式封嘴,膠紙繞到後腦再周而復始打圈;小五全校早會,場中間放着乒乓球桌,他在上面罰站。
頑皮每每為了抵抗不公義,一次老師笑他髮型像飯碗,他回敬對方髮型似蕉皮,可以想像他的下場很慘,他發聲:「為何你可以笑我飯碗頭,我不能笑你香蕉頭,為何不對等?後來我為甚麼從政?不合理嘛,跟現在年輕人一樣,我完全明白他們做甚麼,現在你(政權)挑戰我的常識、常理。」這時執起螢光筆,說:「這是甚麼?螢光筆吧,你別說毛筆,現在你逼我承認這不是螢光筆,是毛筆,要我附和你,還要寫篇文章說這支毛筆真好用,今天社會就是這樣。」

傘後 愧疚化作力量
當年留學澳洲才修心養性,入讀昆士蘭大學。譚文豪沒有當上大文豪,1998年回港建造船用引擎,起薪10,800元,當時房子還不太貴;20年後房價翻了幾番,大學畢業生卻一樣掙萬多塊錢,政府則越來越富有,他批評:「你沒有藉口,倚天劍、屠龍刀都給了你,你跟我說劈蔗都無力?香港人不應該如此不開心,生活如此差,自然覺得是制度、架構的問題。還可以是甚麼問題,誰人的錯?流年不利嗎,作個法會否好一點?」
從木屋飛到天上,香港給了他很多,為公義為回饋都要幫年輕人。2014年7月雙生子女呱呱落地,妻子早更照顧,他當夜更,兩個月後傘運爆發,幾乎每晚1時他餵過子女吃奶便搭的士去金鐘參與,4時許回家,「對我來說是很大心結,以香港來說一場偌大的運動,對民主有追求的一個人來說總想付出多一點,投入多一點,但當時投入不到。」同時黑社會入侵旺角運動,一晚爆發衝突他也在場,妻子就只有這麼一次下金牌召了他回家。譚文豪形容當下心情有如逃兵,慚愧、內疚、痛苦,故此今次比誰都出力,「我沒甚麼做多了,我只是做回自己,這件事2014年我本來就要做,只是當年沒有議員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