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想看動畫:一家大細可以選擇迪士尼的《反斗奇兵4》(Toy Story 4),名聲較弱的,也有《Pet Pet當家2》(The Secret Life of Pets 2),或者《樣衰衰奇兵》(Ugly Dolls);文青必推介日本新海誠的《天氣之子》;追開有感情,還有《蠟筆小新》、《多啦A夢》、《名偵探柯南》。圍攻之下,不知道有幾多人留意《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大追捕》,香港出品。
隨口問一句導演袁建滔及鄒榮肇,曾經被哪些香港動畫影響過,全神貫注想了好幾分鐘,才勉強吐得出一句《小倩》。1997年,大導演徐克還會忽然興起,抽空炮製一下動畫。20年來,香港動畫長片,大概只剩下袁建滔執導過的麥兜系列。像流落荒島。「是很沮喪。」拍廣告短片起家的鄒榮肇,對執導長片還有點興致;距離《麥兜故事》,接近20年,袁建滔是氣餒得仿似一隻被綁死的蟹。
攝影:黃雲慶

沒有底蘊沒有生意
袁建滔在大學主修電影,想當作家,對做導演的興趣反而不大。「拍電影,每一次拍攝,有好多部攝錄機,好多支燈,一大班工作人員浪費大量時間搞一件如此事幹,行為幾無聊。說故事,是不是一定要透過拍電影?我從來不會堅持。」自然不是堅持非動畫不拍。無奈,小說寫不好,袁建滔入過電視台當編劇,又想過當漫畫家。那是《少年Jump》最鼎盛的年代,日漫如《IQ博士》、《龍珠》、《北斗之拳》影響萬千少年,港漫代表也有馬榮成有黃玉郎,前途無限。
「然後,我發覺,畫好分鏡,我便沒有動力上色。做動畫好像更適合我,開了個頭,餘下工作交給其他專業人士接手。」碰巧麥兜的作者謝立文找人執導《麥兜故事》,跟袁建滔一拍即合。「我只不過當打工。」
這種打工心態及生態,估不到直到今日,還在。袁建滔試過跟本地漫畫家楊學德合作,希望開拍一齣充滿港式風味的愛情動畫電影,完全找不到投資商肯放膽一試。「拍動畫,短則12個月,長則18個月,甚至兩年。真人電影,拍十日八日還可能搞得掂,拍兄弟膊頭也可以。總不可能拍人膊頭兩年。製作成本,最低,要600萬至800萬港紙左右,即使得到政府資助,也要找到幾百萬的投資額。對於投資者來說,根本看不到收回成本的可能性。」
「我不怪他們,因為,我很明白。」想製作屬於自己的創作?異常困難,困難到拿着計劃書周圍拍門,推銷十次也不會成功一次。結果,袁建滔之後執導的《長江七號愛地球》,是周星馳主導;今次的《大偵探福爾摩斯》,也建基於暢銷的兒童小說。的確是打工,和麥兜時代沒有分別。
沒有出路嗎?「很多人見我拍過麥兜,叫我諗個公仔出來,以為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他們不明白,底蘊這回事,不是話有就有。麥兜在動畫化之前,累積了十年功夫,有深厚底蘊。幾年前,試圖發展《老夫子》,名字夠響了吧,甚至《龍虎門》,最後也無法成事。去到計數階段,是否一盤生意先?身邊有很多畫漫畫的朋友,努力開發,但要行到這一步,太困難。見過很多財大氣粗的老闆,真肯投資拍齣動畫出來,但沒有底蘊,一下即過,無用,根本不成一盤生意。」
即是需要放長線釣大魚?「紙本時代已過。以前,麥兜賣聖誕卡賣生日卡,利潤足夠開齣電影。一去不返了。我們最推崇日本,日本的故事,會由輕小說開始,發展成漫畫,再發展成動畫,一步一步來,讓角色價值可以增長可以成熟。由最廉價的方法做起,大家開始有信心,才越做越貴,投資的風險自然會降低。香港從來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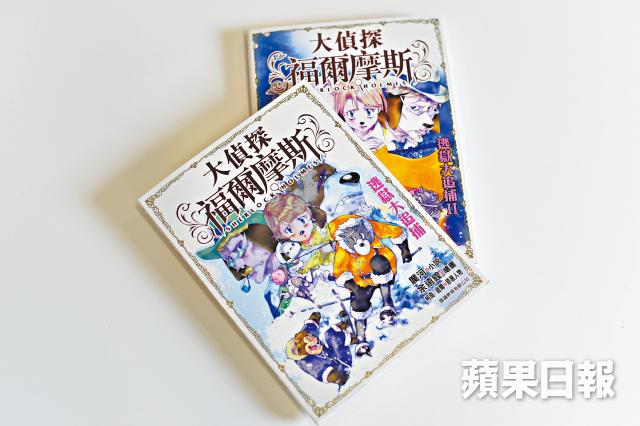
香港人還有優勢
情況險峻,何況,香港現今內外受敵。做開廣告短片的鄒榮肇,面對香港人才流失的斷層情況,特別痛心。「香港從來沒有動畫工業,就算跟南韓相比,我們現今的技術也落後很多年。十年前,南韓政府大力推動動畫行業,作出很大程度的補貼,成功爭取很多生意,人才因此可以累積經驗,一路發展下去。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場嘛,政府的電影投資基金,對動畫的幫助更加少。」
「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很難找到投資者。你看大陸,製作成本畢竟比香港低,每年有一齣收到四、五億票房的《熊出沒》,足夠累積一班人才,讓他們在技術上比我們有優勢。」給小朋友看的動畫《熊出沒》,講述森林有兩隻熊,對付破壞天然環境的伐木工人。很簡單,勝在小童人口夠大。「今年,國內還有齣以成人觀眾為主要目標的動畫《白蛇:緣起》,也收了四億幾。實驗成功之前,好幾齣同類作品的票房其實很一般。」人家有金錢有時間可以冒險,我們沒有。「馬榮成也一路想拍《風雲》動畫,給成人看,對技術性的需求好強,製作費太高,始終未能成事。」
根本是自討苦吃。鄒榮肇說,製作劇情長片的滿足感,遠超製作廣告短片。實際一點的理由,是動畫市場龐大。「沒有小朋友不喜歡看動畫。換轉語言,好容易可以賣去全世界不同市場。」
全球票房最高的動畫《魔雪奇緣》(Frozen),收入超過12億美元,但製作成本同樣高達1.5億。「香港當然做不出這種程度。」放眼中國大陸、東南亞,應該還有生存空間吧。「我們的資源不夠,起步遲。我們的優勢只是香港人的思想比較闊,比較開放。」像《大偵探福爾摩斯》,不用跟柯南道爾購買改編版權,本地作家將原著小說變異成兒童版,鄒榮肇說,十個小學生應該有八個接觸過,如果一眾小書迷肯購票入場觀看動畫版,拉埋父母,不愁生意。
如果。想取悅小朋友已經不容易。袁建滔有兩個小朋友,每日上YouTube找片自修,英語能力超強。「比起我們一代,今日班小朋友的成長期被壓縮得很短,精靈得多。看得外國短片多,有比較,質素相差得遠的,根本不願一看。」要取悅家長,更難。「我也不想帶小朋友入場,小朋友看得開心,家長想死。一齣電影,八成是生意,餘下兩成,總希望放到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大偵探福爾摩斯》,以19世紀工業革命作背景,時代轉變,很多行業消失中,放在當下,成人原來一樣有共鳴。這些信息,我便不會期望小朋友看得明白。」也不知是自嘲,還是哀鳴。

從來不接地氣
兩位導演認為香港人的優勢是眼界比較闊。可以是優勢,也可以是更大的局限。畢竟,大陸擁有最大的市場,而大陸觀眾的口味又比較獨特。想兼顧全世界?倒不如扭曲一切集中火力討好同胞來得實際。香港人又未必做得出。「我也有想過,故事設定在英國發生,但如果想遷就國內觀眾,是否要把招牌的英文字改為中文字?」想想,福爾摩斯是國際知名品牌,總無可能違背事實。「我從來不接地氣。甚麼叫接地氣?接地氣就是寫一些只有當地人才聽得明的笑話,我不會寫得好過當地人。所以,我永遠做環球性的創作,務求人人也看得明白。」袁建滔說。
說到底,有沒有後悔投身一項在香港從未被為意的行業?「動畫在香港曾經有過希望,連無綫也覺得是一盤生意,投資製作電視節目《成語動畫廊》。」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事。「到大約97年,無綫還有動畫部,我參觀過,已經接近可有可無,只做加工片。到現在,當然被淘汰了。我打的第一份工,在無綫做編劇,那時,人人說電視台是夕陽行業,今日,無綫還未死。做漫畫,也有人說漫畫是夕陽行業。當然可以選擇冒升中的行業,例如做遊戲?總要看看自己有沒有能力,又適合不適合。」比較悲觀的袁建滔,是氣餒,還是有點不服氣。「站在作者立場,我只不過有自己的故事好想說出來。我沒有辦法將故事化成生意。」
鄒榮肇形容自己樂觀得多。他不是不知道香港甚少大型動畫計劃,新晉從業員只能不斷製作成本有限的短片,經驗無法累積,技術無法提升。仍然有夢。「如果要拍一齣《阿凡達》(Avatar),要用好多錢好多錢才拍到。做動畫不同,原則上,畫得出就拍得到,創作空間大得多。」他在等候香港誕生一個新海誠。
然後,想起,香港不是沒有出色動畫,最近已有好幾段,不說網民自發製作被譽為世界級足夠反攻日本的好幾條,也有為茶餐廳上市造勢的重金製作。或者,香港,缺乏的,不是人才,只是發表空間。都2019了,還在食老夫子老本?也真有點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