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98!5,999!6,000!
2017年2月24日黃昏,墨西哥聖布拉斯,蔡牧起、薛綺蓮夫婦搭乘小船沿着河道找鳥,一隻北方林鴟停在枯枝頂端,同行隊友爆出歡呼,卻不是因為那隻鳥,而是因為這是蔡牧起探索生涯鳥種(life bird),達到6,000的關鍵時刻!蔡牧起這對夫婦,肩並肩遊歷世界各地觀鳥,為台灣觀鳥紀錄保持人,持續34年的觀鳥行動,兩口子似乎仍意猶未盡,「我們還有4,000種沒看過呢!」
撰文:蘇惠昭
攝影:張先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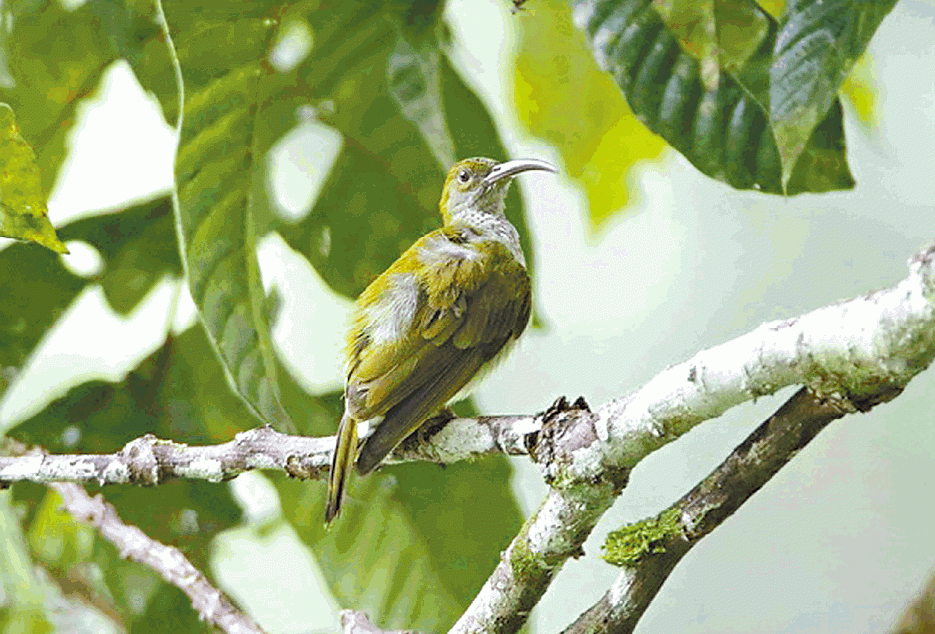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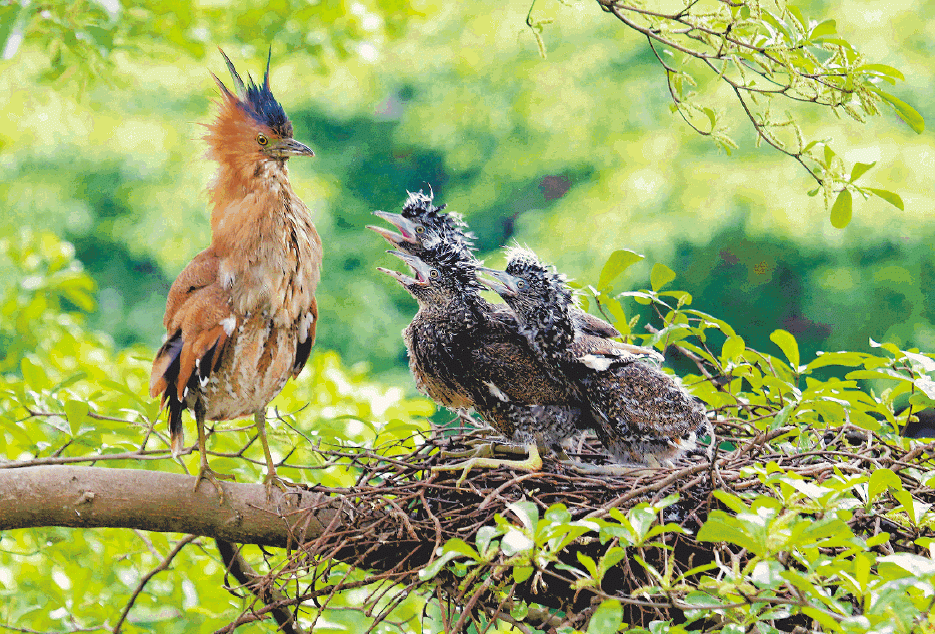
締造六千傳奇 「觀鳥讓我很快樂」
6,000,是蔡牧起夫婦設定的觀鳥目標,「以前體力好時,看到亂草堆,她還在猶豫,我已經鑽進去了,所以記錄的鳥種比她多」講起衝得比老婆快這件事,蔡牧起心情大好。
五個月後,在婆羅洲,薛綺蓮以一隻婆羅洲的捕蛛鳥,登上6,000天梯,這是他們一起看鳥的第32年,人生彷彿攀到頂𥧌,足迹踏遍過半個地球、一年製作出一本、堆叠起來有如小山的觀鳥紀錄簿、以及191篇部落格文章。之後呢?在埔里的家中,擔任「蔡鳥家族」發言人的蔡牧起盤點現在的生活:每星期有一天回到梅峰農場、一天到台中科博館當志工、也會主動帶領埔里籃城社區的媽媽觀鳥,教導她們如何用植物及水,營造吸引鳥隻飛來的環境,「觀鳥讓我這麼享受,這麼快樂,為甚麼不讓更多人知道,大家一起來?」
薛綺蓮則是每天從家裏出發,把鳥況頗佳的鄰居慈濟基金會作出發點,徒步約一公里,記錄聽見或看到的鳥,並上傳到eBird Taiwan,就算不在埔里也一樣,人在哪裏,就記錄哪裏的雀鳥,至今400多天不曾間斷。eBird是全世界最大的觀鳥紀錄資料庫及共享平台,四年前出現了繁體版本eBird Taiwan,讓蔡牧起夫婦積極做記錄,目前上傳數目,是世界排名第24、25名。
蔡牧起解釋,這就是結合眾人力量幫忙累積,貢獻一份生態資料的公民科學家,單單看一天兩天的紀錄沒有意義,但長期累積下來便是大數據,可以看出趨勢與變化,譬如麻雀數量有沒有下降,或者黑冠麻鷺是否多到把蚯蚓吃盡?
「等下我帶你們去慈濟看黑冠麻鷺育雛。」薛綺蓮打開手機讓我們看她當天早上所走的路線,260公尺就記錄了11筆資料。


耗盡人工退休金「興趣是沒道理的」
為甚麼看鳥?為何這樣瘋狂,必須給自己設定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
「興趣是沒有道理的。」蔡牧起的答案就這麼簡單。
蔡牧起回想起40歲那年,薛綺蓮當時小他一歲,台灣觀鳥風氣剛萌芽,連一本鳥類圖鑑也沒有,夫妻倆靠着望遠鏡和《日本鳥類圖鑑》學習辨認看到的鳥,辨識越多,越是魂牽夢繫,最廣為人知的一段故事是,當時兒子九歲,女兒十歲,每周六中午,還沒到放學時間,爸媽就把車開到學校門口等他們,接到小孩後直奔觀鳥點,晚上的旅館房間,就是小孩做功課的地方。
觀鳥人是一群神經不正常的人,蔡牧起記得有一次在大雪山,於廁所小便的男生從窗戶看到藍腹鷴,接下來,女生也衝進男廁,一行人就在尿兜前駐足欣賞得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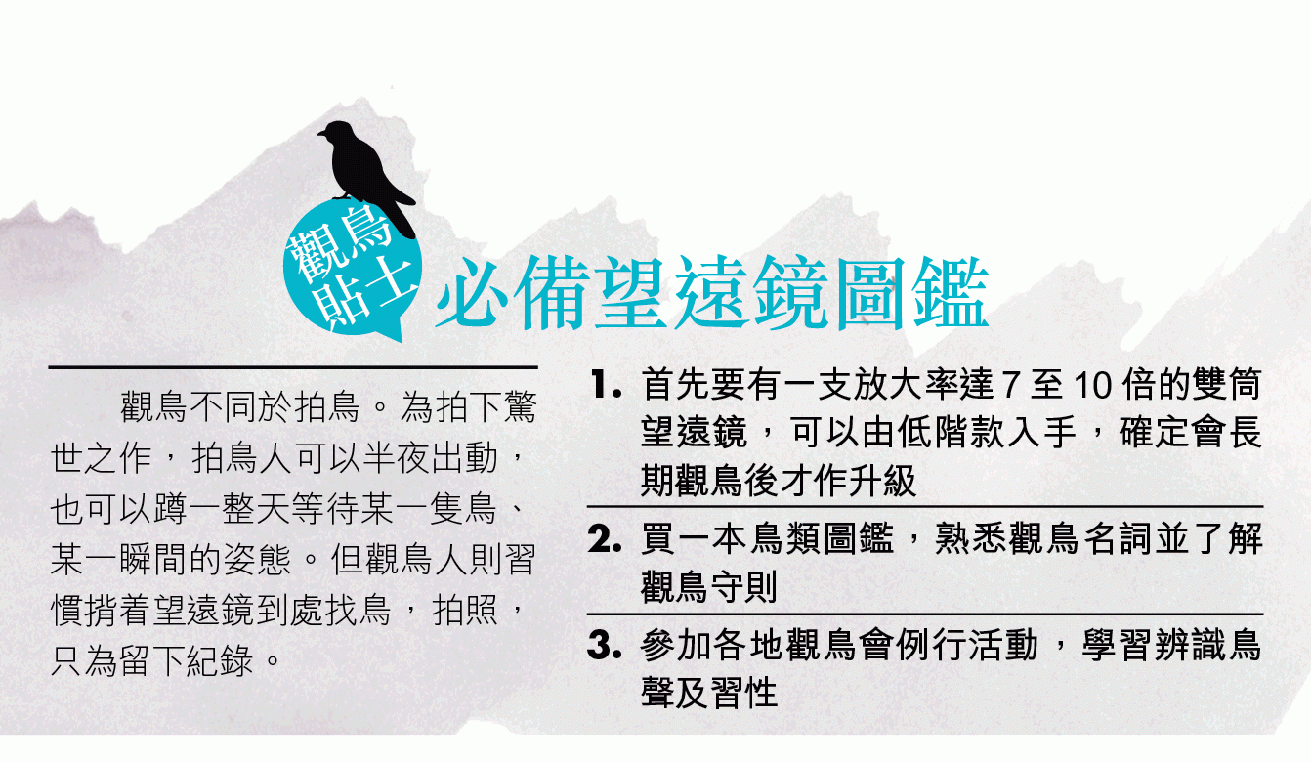
瘧疾蚊赧當紀念品
第一次的中國大陸觀鳥是到西雙版納,當地地陪正對着一群台灣來的觀鳥人講中國國歌的故事,一肚子學問如瀑布傾瀉,忽然不遠處一棵松樹傳來鳥鳴,他們像聽到某種暗號,咻一下飛奔過去,留下地陪呆立當場,渾然不知發生何事。
從菲律賓巴拉望帶回來的紀念品,則是瘧疾,而新幾內亞是蔡牧起夫婦認為最艱難的觀鳥之地,「有些地方簡直還在石器時代」,雨鞋一穿就是十多天,爛泥與蚊蟲永遠同在,洗澡必須到河裏,「但是怎麼辦?有些鳥就是那裏才有。」
有些鳥,譬如西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威氏極樂鳥(又名天堂鳥),就是蔡牧起生平所見「最最讓人驚艷、讚嘆、奇特的種類,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依蔡牧起的界定,偶爾去觀鳥、一有空就去觀鳥,還未算真正的觀鳥人,真正的觀鳥人不會只迷戀美麗的鳥,他們會用檢索表記錄所看過的鳥,他們有一張全球鳥類地圖,而且有計劃的一隻隻去追逐、填補。至於看到目標鳥的狂喜,蔡牧起如此形容:「那一刻,一切都消失了,人世間只有這隻鳥,再沒有煩憂雜事困擾你,禪定狀態感受到的狂喜也或許就是這樣吧 !」
為體驗這種會上癮的幸福,蔡牧起夫婦花光了薪水和退休金。
觀鳥34年仍未畢業 「還有4,000種沒看過」
然後,蔡牧起自以為出師了,直到學者劉小如號召他、丁宗蘇、方偉宏、林文宏和顏重威等台灣五大鳥人撰寫《台灣鳥類誌》,他才驚覺「我好像甚麼都不懂」。整整六年,蔡牧起寫了近20萬字,經常為兩句話翻查3小時資料,眼力嚴重退化,「但寫完後看鳥的視野又不一樣了,跳了一階」。
台灣實乃觀鳥天堂。根據中華野鳥學會2018年底報告,台灣特有種鳥類已增至29種,記錄663種鳥類,包括明星鳥如黑面琵鷺、八色鶇、帝雉、藍腹鷴,觀鳥本錢雄厚,但為何一直無法吸引更多外國人來觀鳥觀光,「因為保育人士和拍鳥人極端對立」蔡牧起直指核心。
極端的保育人士無法容忍「不自然」的放鳥音、餵鳥,為拍攝美麗畫面而造景,但蔡牧起認為除非干擾育雛、不尊重自然,否則這些對整體生態影響不大,而到過海外觀鳥的人都知道,鳥導若不適時的放鳥音或錄下鳥音再回播,觀鳥人可能空手而返。「真正導致族群數量下降的元凶,是毫無節制的開發,以及消失的棲地」蔡牧起說。
生涯鳥種6,000至今,蔡牧起、薛綺蓮是「台灣觀鳥紀錄保持人」,台灣663種鳥類,薛綺蓮跑得勤力,看過536種,蔡牧起是524種,同樣驚人,之後兩人又去了一趟稱為「畢業旅行」的南極,然而金盆洗手談何容易,他們一再破戒,去了廣西弄崗、又去了緬甸和柬埔寨,持續34年的觀鳥行動,形成頑固的、根深柢固的慣性,「那是我們的大半輩子,我們的人生故事」,有天兩人在家打電腦,整理資料,忽聞台灣藍鵲叫聲,這在中部並不常見,於是話都不必說就一起衝出去。
「所以鳥還是要繼續看下去囉?」我問。
「嗯──當然要。」蔡牧起大笑「地球上1.1萬多種鳥,我們還有4,000種沒看過呢!」
「更老的時候,我們就坐着輪椅去看。」又補上一句。
薛綺蓮也笑了,揹起望遠鏡說:「走,我們該去看黑冠麻鷺育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