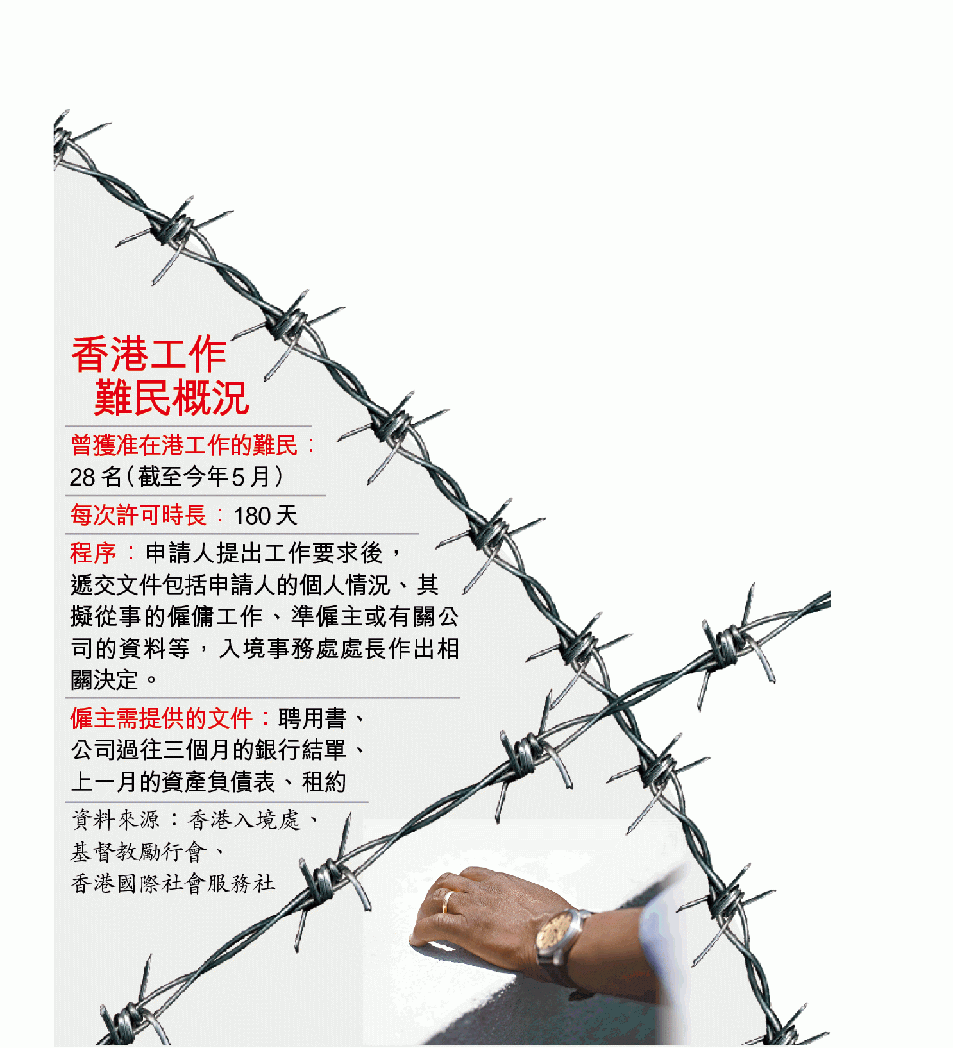在港政治難民少見,能工作的更絕無僅有。想想中國維權律師,就能理解Martin(化名)這位非洲小國布隆迪人權律師的遭遇。他是60萬名流亡海外的布隆迪人之一,來港僅五天已獲聯合國難民公署批出難民身份,也是首名於2013年獲臨時准許工作的難民。
在港難民絕大部份無工作權。根據入境處資料,2009至今年3月完成審核的兩萬餘宗聲請中,僅有160名獲批難民身份,截至5月曾獲批准工作的僅28名。2001年,由曼德拉代表聯合國,調解布隆迪衝突的和平談判中,Martin是人權顧問。
2004年,接到來自當局線人的死亡預告,他急得於兩小時內出逃,被迫遺下懷孕八月的妻子,來到香港。由於難民被禁止工作,包括義工,他的生命荒廢了足足九年,一度抑鬱。如今,在基督教勵行會工作,他說:「幸運,因我仍活着,不幸,因為我來了香港,如果我有選擇,我會去別處。」
記者:鄭祉愉 攝影:江智騫
2004年6月26日炎熱的下午,於布隆迪首都基特加,Martin正在律師樓處理公務。忽然,手提電話鈴聲響起,政府內工作的朋友捎來警告:「你只有兩小時離開,我們剛剛開了一次會,要處理你。」兩日前,才有另一位抗貪污的人權律師被擄走,翌日早上屍身被棄置在家門外,遭秘密處決。
只有兩小時,Martin匆匆整理好文件,通知教會的朋友便急急安排離開,只來得及致電懷孕八個月的妻子。三個孩子還小,夫妻隔着話筒道別,妻子有心理準備,仍因別離之苦,幾乎泣不成聲。
行行重行行。Martin身上僅僅帶着一部電話,一點現金,便趕至機場上機,朋友替他安排了最快出發的班機,為他選了香港——安全而不用簽證的目的地。他對香港一無所知,但鄰近國家均局勢動盪,「冇得揀」。來港不到五天,聯合國難民公署已審批出他的難民身份。下一步是等待第三方國家收容,他滿以為不遠,沒想到,足足等了15年。
對抗極權遭滅聲
布隆迪的國史由種族仇恨鑄就,殖民時代由少數圖西族(Tutsi)統治大多數胡圖族(Hutu),數十年間,頻頻發生種族屠殺。因1993年胡圖族總統上台又被刺殺,引爆長達12年的內戰,令足足30萬人死亡。隨1996年圖西族前總統Pierre Buyoya重新上台,只要任何人質疑政府施政,撰寫文章,向傳媒發聲,只有一個下場:某一天忽然被消失,從此杳無音訊。
今年約50歲的Martin屬圖西族,以往開私人律師行,任職檢控方律師。2001年聯合國調解布隆迪衝突的和平談判中,由曼德拉任調停人,Martin擔任人權顧問。
眼見政府公然違反人權,一個個異議者被滅聲,Martin終於忍受不了這種「有目的的謀殺」,偕同約八名專業人士組成著名人權組織Ligue Iteka。除了揭發政府高級官員貪腐、洗黑錢的金流外,還不斷拯救被政府秘密羈留的人士,嘗試撐出一片自由的天空。
每月,Martin都接到兩至三個高級官員求助。「唯一救出一個人的方法,就是向國際社會發聲。」迫於輿論壓力被釋放的受害者中,僅有一部份見外部傷痕,政府又另覓方法滅口。曾經有個案,被囚四個月獲釋後,忽然暴斃而亡,發現他曾被迫接受藥物注射。Martin幾乎每一天都接到恐嚇短訊或電話,威脅他停止人權工作,否則會「處理他」。

為人權甘願犧牲隨着
隨着Martin離開,他的家人七年前也逃了,Ligue Iteka其他成員也逃到歐洲。唯一留下來的戰友兼人權律師Ernest Manirumva,致力揭發政府官員貪污。2009年,Ernest從辦公室被擄走,帶回家慘遭殺害,當局聲稱為入室搶劫,卻無貴重財物被盜,僅有重要反貪腐文件消失。Martin甚至不忍述說他的死狀。
事態逐步惡化,2015年布隆迪政變,2016年起必須以實名註冊SIM卡,民眾一切溝通途徑被監聽,不斷有反對分子被消失……2017年Ligue Iteka被下令禁止運作。「如果我不走,那就是我的下場。」
對Martin而言,政治難民意味着「為他人付出自己,就算身陷麻煩之中」,「有許多人持同樣意見,懷着同樣的感受和靈魂,但因身處的位置,或者要保護利害,他們不想,也無法發聲」。
值得嗎?問句未完,Martin已說:「我們不能把每個人交到獨裁者手中,永遠要有人發聲,人們或會恐懼,但人們總會說『夠了』。」Martin舉例,沒有突尼西亞的小販自焚,就沒有席捲整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許多人要犧牲,只是剛好到我。」哪怕要放棄一切。他仍有幫助布隆迪境外的受害者家屬組織:「我好想回家,但如果現時政府仍在,沒可能。」

曾住天台屋頹活
在港難民不能出境,不能念大學,不能工作。曾與曼德拉一起討論國家大事的Martin像擱淺的鯨魚,無數次拒絕出席受邀的國際會議。隨體制轉變,他先後依賴聯合國難民公署,以及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救濟度日,住在天台屋,生活日夜顛倒,睡了又吃,吃了又睡,他曾羞於承認難民身份:「一個成功人士,又是律師,但突然成為了乞丐,只因為你想生存,甚麼都得求人。」
2009年Martin獲贊助,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念法律文憑,每次考試都要為難民身份解釋一番;2013年勝訴後,好不容易獲批工作,想兌換糧票開立銀行戶口,銀行職員卻懷疑他是小偷,又致電入境處。無法出境,闊別家人15年,兒子甚至跟他說:「爸爸,我們不想做難民。」今年家人來訪香港,他才首次見到最小的女兒——此前,他是存在電話中的父親。
難民工作權案件最終告上終審法院,最終敗訴,但律師帝理邁致電說「有個好消息」。尋求庇護者整體輸了工作權,但難民可獲臨時批准工作,他成了第一人。
基督教勵行會轄下的難民服務中心在2004年成立,Martin以個案身份來過無數次。2013年9月23日早上9點,Martin第一次以員工身份上班,像「尊嚴的開端」。Martin本來有三個工作機會,最終因渴望回饋社群,選了這裏。九年後,他終能交稅回報社會,並租房,擁有私人空間。

受助者變施予者
有了收入,Martin最後一次前往以往領取津貼的國際社會服務社,職員恭喜他,他終能說:「不用,謝謝,你給另一個需要的人。」有常常提到「假難民」的建制派區議員與Martin碰面,並了解其遭遇後,對他說「我哋唔係講你」。曾經的受助者成為施予者,施比受更為有福。Martin負責福利工作,統籌義工為尋求庇護者煮免費三餐,以及分發救濟品。6月是世界難民月,全球難民人數突破7,000萬人,他曾後悔來香港,卻別無選擇,只希望更多香港人了解難民處境。
今年,有香港人成為政治難民。作為過來人,Martin指成為難民是別無選擇,「如果你被監禁,被折磨而死,別人又會怎說?如果發生在你的孩子或親戚身上,你會說逃跑是做得好。」他寄語黃台仰二人:「你是難民,生活還得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