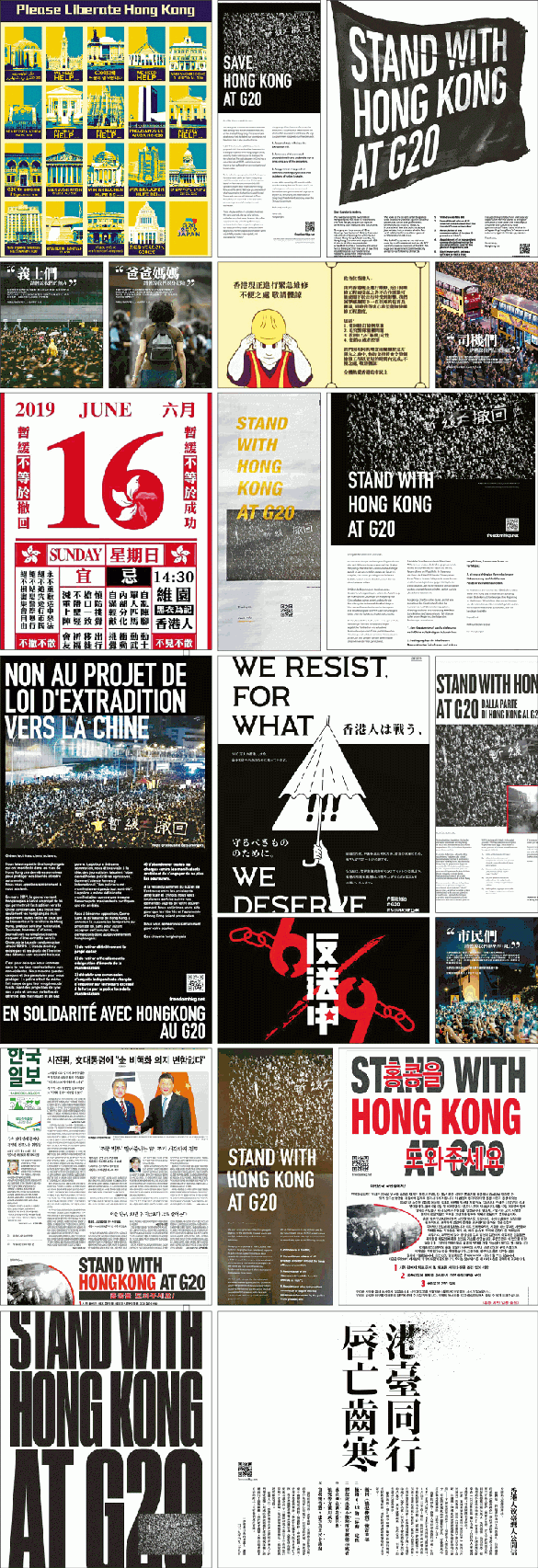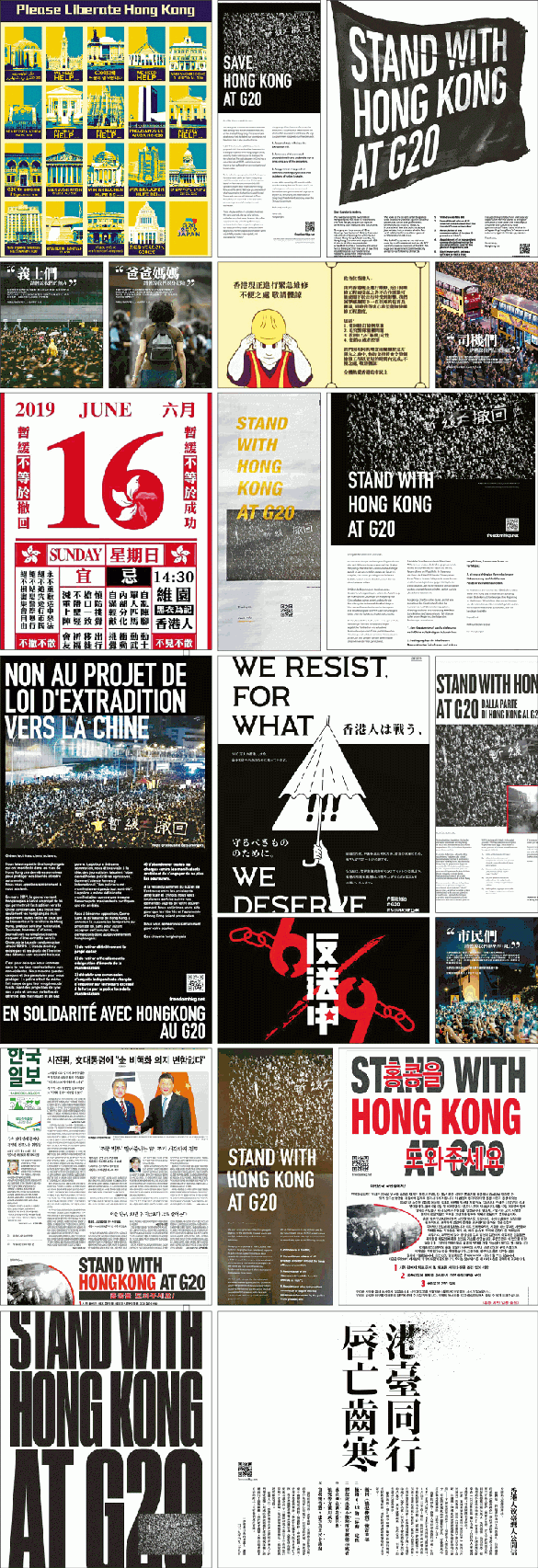
送中惡法引發出一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抗爭運動,令自2014年佔領運動後一直處於低潮的公民社會與抗爭行動從谷底反彈。這場運動有別於過去,美國《洛杉磯時報》分析認為,香港已發展出一種沒有領袖、由群眾自發參與的新社運模式,套用香港社運術語就是沒有「大台」,究竟看似沒人領導下,運動能走得多遠?
反送中運動雖有不少團體參與,但更多是不屬任何組織的人,不少是響應連登討論區號召,他們從社交平台獲得資訊,甚至在網上投票決策。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在6月16日200萬人遊行後曾公開撰文,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已進入新階段,「所有上街的都是不認命的香港人,我們手挽着手,為我們的自由,為我們的尊嚴,為我們的命運而戰。」經過反送中一役,大家更建構出一種強烈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縱明知敵人強大野蠻,但香港人仍選擇站出來,「選擇站直,選擇說不。」惟他同時認為,前面的路一定很難行,但只要走出來的港人願意一起行,彼此扶持,互相打氣,「那麼香港未來的歷史,一定由我們來寫。」
愛丁堡廣場一夜後,他再補充一些新觀察,包括參與者絕大部份是年輕人,他們對這場運動有極強的認同感,而這種能量很可能已遠遠溢出「反送中」本身,未來對香港整個社會的政治及文化衝擊,可能才剛剛開始。運動訴求亦開始回到「重啟政改」這個香港民主運動主軸,有意識地接續雨傘運動的使命,他認為這個轉變,對運動下一波會產生甚麼影響值得留意。
除了沒有「大台」,今次抗爭的另一特色就是「Be water」,參與者不住提醒「流動」的重要,不與警方硬碰,強調「不流血、不受傷、不被捕」。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引用美國學者Lance Bennett分析佔領華爾街的案例,探討了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指去中心化的群眾運動在網絡平台上要做到有效的群眾自發組織,就要做到生產、策展和動態整合各類資訊和資源,今次「連登仔」似乎發揮很大作用,其實一個「推post」行為,就是變相投票。
去中心化運動的一大好處,就是容許不同參與者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其中,套用今次運動的語言,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然而,李立峯也指出,自政府宣佈暫緩修例後,運動開始進入反守為攻的階段,開始出現「要甚麼」的正面訴求,若雙方膠着,拖延下去對運動不利;若政府企硬,如何把訴求聚焦,行動模式如何轉化,進退之間如何拿揑,如何保持團結,都會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