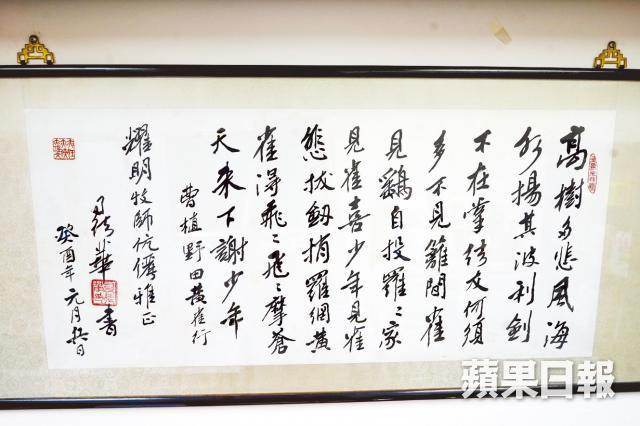6月16日凌晨,朱耀明牧師手中握着兩朵白菊花,來到金鐘太古廣場外獻花。幾小時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男人,在廣場外逾20米高的臨時工作平台,懸掛「反送中」橫額,及後墮下身亡。朱牧看了新聞,很不安樂,本來回家了,打算睡覺了,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睡,最後還是拿着花,駕車到金鐘,與自發前來的市民一同默哀,一同流淚。有年輕人走到朱牧身旁,與他抱頭痛哭,朱牧說:「可以傷心,但不能失望。」那晚,廣場外的人都希望完成烈士的遺願:「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
選文:趙曉彤
攝影:梁志永

回家後,淺睡一會,朱牧又來到616大遊行的人潮裏。他在灣仔地鐵站附近位置站台,為「反送中」被捕者籌款。從下午1時半,站到晚上9時半,為了與川流不息的人握手,他一次又一次俯身。他對記者說:「腰骨很痛,全身散晒。」其實,他仍未從6月9日的遊行恢復體力,那天,他也是站了整整八個小時。75歲、滿頭銀髮的人,預料不到香港人在一星期後,竟再次遊行,而且是從100萬人,變200萬人。五年前的佔領運動,他自言只是一個敲鐘者,希望發出警告,令人知道不幸和災難正在發生。他希望自己的微弱鐘聲,可以喚醒香港人的良知,令他們一同抵抗,一同保護香港。而現在,他看見很多香港人是醒來了,他很激動,又很安慰。
他最難忘大遊行裏的「救護車分人海」,那刻的震撼畫面,令他想起了《聖經》摩西分紅海的奇蹟景象,但他同時想起了罷工罷課那日,一排防暴警察不讓路給救護車。他覺得,香港人不應該有這樣的政府。「香港人這種公民質素,香港人這種高貴的品質,為何會被這麼殘暴的政府踐踏?這個政府怎可以對得起這200萬人?」
6月12日,他整天留意事態發展,從新聞片段看見警方如何以武力對待只是站着、坐着的示威者,甚至把催淚彈投進人群裏面,導致中信圍困事件,朱牧表示,中信最後沒有發生人踩人慘劇,是全靠群眾自發地、有秩序地不讓悲劇發生。他看見愛與和平,在示威者心中植根。然而事後,林鄭、盧偉聰乃至政府各部門的回應,卻是出來卸責、出來說謊,這令朱牧感到痛心:「香港政府本身已失去了社會道德倫理及政治倫理,由上而下地破壞原有的規矩和秩序。」他想起警察在開槍後面露笑容,極其氣憤,「這些畫面在我腦海中無法磨滅,你從一個人來講,你殺一個人,你開心嗎?」
朱牧並沒有在6月12日到達罷工罷課的現場,一方面是因為「階下囚」身份,他會避免到任何不確定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現場。其實,他更怕是如果他身在現場,其他人對他的指控會污衊了在場的示威者,轉移了運動的焦點。不過,他看見新一代人已經上場了,自覺出不出現也無所謂,無大影響。
他身在遊行現場。遊行裏,很多人高喊「林鄭下台」口號,有市民問他:「香港現在沒有真普選,林鄭下台又怎樣?」朱牧回答:「現在叫林鄭下台,是表明要她對6月9日、12日、16日發生的事,包括警方所用的武力、暴力負責任。」更重要的,是:「(林鄭)下台是讓我們反省制度上一定要改,試過幾任特首,一個比一個差,一個比一個令人民憤怒。」
「她的眼中沒有人民,只有選票,只有通過這條法例。」朱牧如此評價林鄭。他認為,不公義的制度一日存在,社會永遠無法和諧,因為沒有真普選,只能產出林鄭這類特首。「一人一票最重要的地方是我們和特首建立了一個道德上的關係,原因是我選你,我對你有監察的責任,你有向我負責的責任,但現在她根本不用,她對1,200人負責就可以。為甚麼她如此藐視我們?因為她不需要我們。」
朱牧站在人群裏,表達「反送中」與「林鄭下台」的訴求,同時仍在爭取真普選,他看見越來越多香港人醒覺,甚至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也敢於站出來,他說,爭取真普選,仍有希望。
親歷鬥地主 以勇氣反抗不義
五年前,他與戴耀廷、陳健民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爭取真普選。當時,他已70歲,希望在民主路上,與香港人多走一步。4月24日,朱牧因「串謀作出公眾妨擾(中環)」罪成,判刑16個月,緩刑兩年,戴耀廷和陳健民被判即時入獄。兩個月過去,朱牧的「階下囚」生活不太開心,好像常常有一塊大石壓在心頭。
「健民是我三十幾年的朋友,我每次想到他穿着囚衣回頭一望那張相,我都流眼淚。在大學界來說,你難以再找一個如此正直又能夠對社會如此瞓身的學者。在受審的時候,他自辯,律師問他為何要這樣做時,他只是說了句:我愛香港。」
說着,朱牧便流淚了。「最近很多事情,我要作決定、要處理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少了一個人。即是,很多問題我都會問陳健民,就算有時我佔中後的訪問,我也會問他意見,我應不應該做?」從前,陳健民一直是佔中九子的「班長」,一力承擔了很多工作,但如今九子有四人在獄中,他好像也要兼顧原本班長的工作了。
同時,他很擔心陳淑莊的狀況,因為她的治療尚未完成,看東西仍有雙重影像,他說,這段時間對陳淑莊來說是身心也經歷了很大的困難。他希望佔中九子經歷的痛苦能夠喚醒更多人,更有勇氣去反抗政權的不義。
現在,他每天最快樂的事情,是黃昏和九歲的孫仔一起游水。遊行時,他總覺得自己75歲了,且不少時間花在內科、痛症科、呼吸科的覆診,他不知道自己還可以遊行多少次。孫仔便對他說:「爺爺,等你行不到的時候,我代你行。」
1956年,12歲的孤兒朱耀明來到香港,抵港那刻,他鬆了口氣,他終於逃離了他所恐懼的大陸。他在香港出生,因父母遺棄而被嫲嫲帶到台山居住,那年,內地饑荒,他有時到魚塘偷魚吃,最餓的時候只能撿樹皮吃。但對飢餓的恐懼,還遠不及對土地改革的恐懼。那年,他走在河邊,不時看見有人投河自盡,他身邊的「地主」,以各種方式自殺。
一次,他走到山腳下的一個竹棚,看見幾個被綁着手腳的地主跪在棚上,面向人群。地主身旁的官員問群眾:「他們是否有罪?」「有!」群眾起哄。「應不應該槍斃?」「槍斃!」官員不用拿出證據,地主有沒有任何申訴途徑,群眾同意他們該死,他們就被押到竹棚不遠處槍斃。朱牧記得,其中一個地主本來是不用槍斃的,但在槍聲裏,那個地主嚇得倒下來,死了。才十歲的朱牧,目睹了甚麼是生不如死。
朱牧的嫲嫲臨終前,託朋友無論如何要把他帶回香港。他一無所有,來到香港,在洋服店裏當學徒,後來逃走,在街頭露宿,無錢吃飯,被黑社會打,但他決定留在香港。當時,他深深恐懼那個視人命如草芥的大陸政權。


監視與虐待 半世紀依然
「到今日看見現存的政府,對劉曉波也是,對王全璋也是,對所有人也是,在監獄入面困着困着就死了,放出來也是死,這種折磨,我每次想起劉霞,在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時,劉霞被拍到她整個人在家裏顫抖,是一種這樣的恐懼。這個政府對無辜的人的監視和虐待,我覺得幾十年也無變,這些可怕的事情,現在仍在發生,所以送中為何那麼多人反對,真是生死攸關,與我們的自由攸關。誰能忍受我們的家人、朋友、兒孫會送中受死呢?」
朱牧表示,政府的最大管治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人免於恐懼,安居樂業地生活在這個地方,但修例卻使人人恐懼,「我們很多人就是恐懼共產政權然後來港,你把我們送中?」
六四事件後、香港回歸前,朱牧照顧了很多像他當年一無所有、逃難來港的民運人士。從89年6月至97年6月,他參與了「黃雀行動」,以地下通道協助來港民運人士離國。90年,他到旺角去接一個剛抵港的民運人士,只見這個人非常迷茫地站在街上,一身所有就是手中一個膠袋,以及膠袋裏的幾枚硬幣,朱牧看着他,感到非常淒酸。「這班人為了甚麼?這班人其實是反官僚、反腐敗、反貪污、要求民主,為何會有一個這樣的結果?」
當時,他一心幫助民運人士,沒有考慮自身安全,但臨近回歸,身邊朋友都提點他要離港「避避」,於是,他以訪問學人身份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原定留校一年,但一到異邦,他就非常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非常關心香港的狀況。他不斷探聽:可以回香港了嗎?不到半年,他就買機票回香港一趟。
政府是否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對朱牧的人生安全影響,可能比當年回歸更大。朱牧表示,即使他可能是受影響的第一批人,但他的人身安全如果受影響了,其實很多香港人也受影響,因為送中條例是拆掉了香港人的法律保護網,「所以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個條例而送中,香港其實就人人都陷入危機。」
97年,他逃到美國又回到香港,再回美國又再回香港,飛機抵達香港那刻,他已放開心懷,再無任何關於人身安全的陰影。以後,他有很多機會移民,因為很多國家都願意給他護照,但他不想離開香港。朱耀明說,他愛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