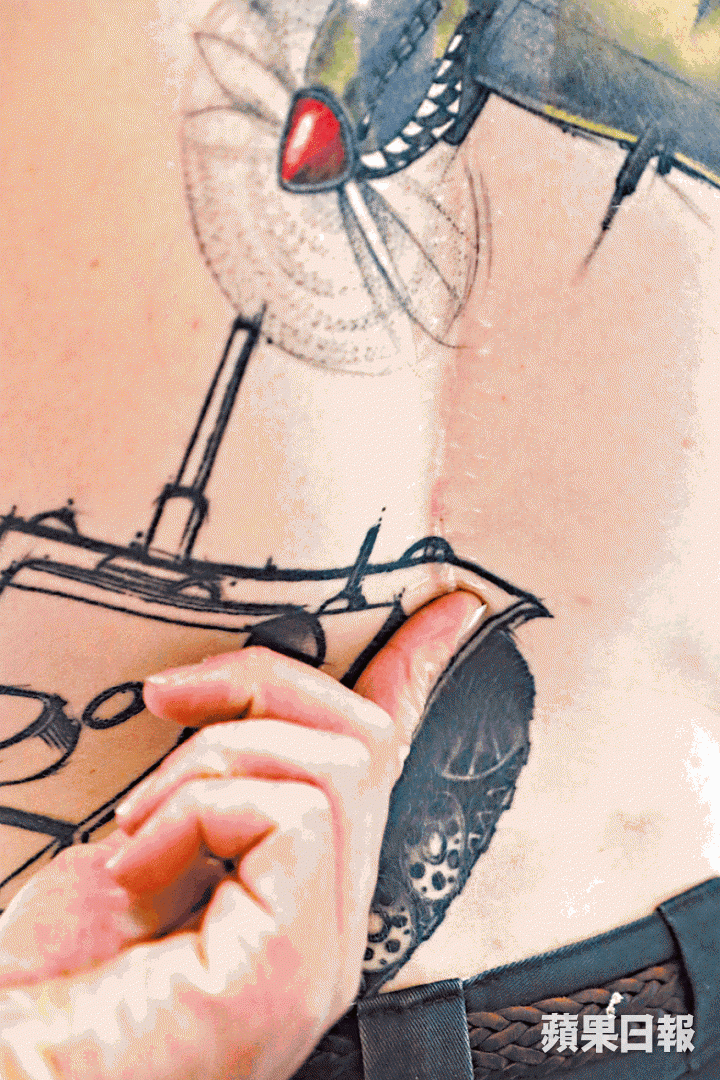
6月12日金鐘衝突過後,特區政府曾放風指此乃所謂顏色革命,背後有組織預謀云云,企圖為大家的眼鏡染上顏色來看是次抗爭。
幾日後6月16日二百萬人大遊行,加拿大人Nik Harrison與你我並肩,他的胸口、整個背部、手臂、大腿都紋上色彩斑斕的圖案,頭髮也染上藍色。香港沒有顏色革命,顏色鬥士倒有一個,不過中央政府或會說這是外國勢力煽動港人的例證,尤其華為太子女孟晚舟正正在加國落網。
阿Nik躋身遊行隊伍不是鬧着玩,他自小受香港文化影響,一心來港尋根,希望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再談下去,原來其脊髓受過重傷,幾經苦練如今才得以撐着手杖走路,這個生命鬥士勉勵港人,再難的關口都能闖過。
撰文:陳勝藍
攝影:謝榮耀、司徒世華
26歲的阿Nik來自渥太華,那裏雖是加拿大首都,人口卻不足一百萬,少過香港一次遊行,故此沒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易受外界影響,本文主角便為東方文化着迷。初體驗來自朋友的爸爸,這個香港移民經常帶他去當地唐人街菜市場,名為Kowloon Market,西方人一般都去超市買包裝好的肉類,未見識過港式街市的屍橫遍野,好小子如入大觀園,他憶述:「年紀小小便去肉類市場,看見動物的頭顱,嗅到強烈的魚腥味,很震撼,甚至有點可怕!」
渥太華鄰近香港移民集中地多倫多,他在該處唐人街吃到紅豆包、叉燒包、芝麻卷,他說:「所以我很早便發現這裏的食物比加拿大菜好吃。」認識一個地方的文化最初總是透過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裏面有大量亞洲元素,例如大廈外牆日本藝伎扭腰作舞的影像,主角又在港式大牌檔吃麵,這個小子便對日本、香港文化着迷。說也巧合,《銀翼殺手》的主角正是夏理遜福Harrison Ford,他的名字,Nik Harrison的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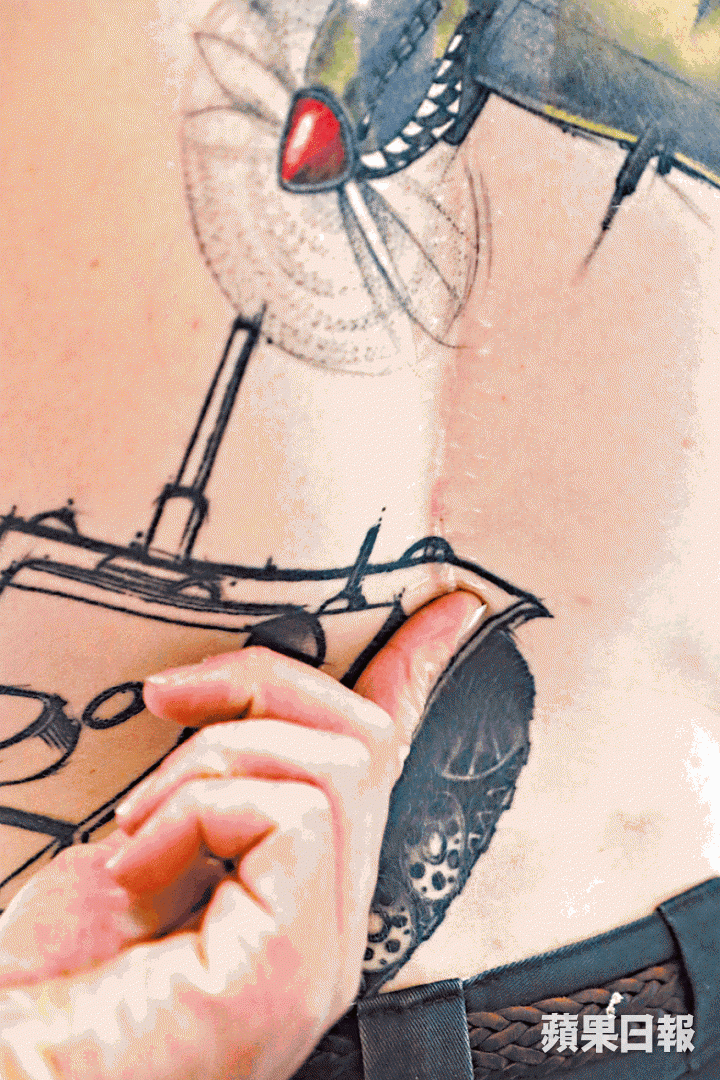
重慶大廈不淒美 大角嘴最真實
1995年《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動畫電影雖是日本製作,片中卻以九龍城寨為藍本;2017年真人版電影也以香港為背景,銅鑼灣糖街圓形天橋、鵝頸橋、灣仔街市、鰂魚涌舊樓、勵德邨一一印在阿Nik的腦海裏,他也在這年首次來港,「但影響我最深一定是王家衛,《花樣年華》、《重慶森林》,我因此經常去重慶大廈,但我失望得很,戲中展現重慶大廈淒美的一面,但我去到完全投入不到王家衛的境界,人人都纏擾着要我去他們的店子,叫我幫襯他們的咖喱。」
香港的食物跟他在多倫多唐人街吃到的一樣,因此2017年起連續三年來港,「我在加拿大成長中接觸到很多香港文化,這些經驗成就今天的我,令我決定親自來看看我的根,而我第一次來到這裏便愛上香港的感覺,這裏多麼的有趣,多麼有動力,每個人多麼友善,我計劃有生之年都會繼續來港,我在這裏有很多朋友。」他大讚香港人:「我身有殘疾,香港人往往很快施以援手,將我的摺叠式單車搬入地鐵車廂,又扶我跨過空隙,這情況在香港發生多過在加拿大、日本;我在車廂內失平衡跌一跌,撞在別人身上,對方也毫不介意。當你身體有殘障便知道幫忙雖小意義重大,一般人覺得輕而易舉的事對我來說可能困難重重,所以助人之念極之重要。」
比起別的遊客,阿Nik是個異類,喜歡在尖沙嘴、大角嘴、旺角混,尖沙嘴自然是旅遊熱點,另一個嘴大角嘴卻有些出人意表,他解釋:「我覺得這幾個區最真實,對我來說也最有趣,因為我覺得港島區被金融佔據了,感覺上更像是公司環境,而那幾個區的文化對我來說更有活力。」從不涉足中環、愉景灣、金鐘,除了6月16日遊行,「我還是比較有興趣去舊區後巷的食肆,凌晨3點鐘在那兒跟人談話,看他們辛勤工作,令我憶起小時候在加拿大所知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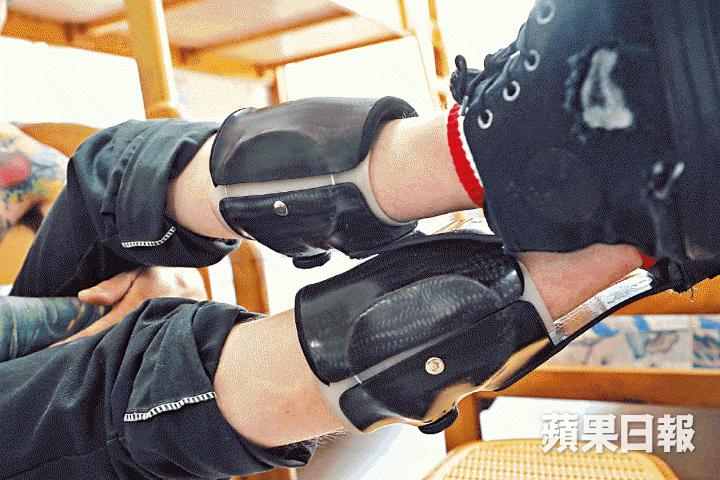
每每在深夜2、3點時分踏單車穿梭旺角街道,一去便是一、兩個小時,「聽到的士駛過的聲音,街上路人有幾疏落,工人叠報紙,食肆忙着準備做生意,這是我最愛的活動。」他對香港這份感覺實在有點不能自拔,「我喜歡香港真實的感覺,夜裏街道很靜,將日間刺激繁忙動感與深夜安寧作個對比。我每次來港不管去哪玩,晚上總是踏單車返回住處,我覺得這樣令我與香港更加親密,就像是一種冥想活動,尤其在雨季,雨點散落地面,濕地映照出各種燈光,構成美麗的景觀,單車在上面走過令我覺得很安寧,很禪。」
他多麼希望留在香港工作及生活,之前在渥太華University of Carleton完成Political Economy碩士課程,各企業有買趁手。他也喜歡東京,一共去過六次,身上很多紋身由此而來,更曾在當地工作,也跟在港一樣深宵走單騎,感受東京街頭,「一樣的活動,但體驗完全不同,兩個城市感覺有異,深夜的東京可能表面看來漂亮一點乾淨一點,但那是絕對停頓,沒有人,街道死寂,其實不怎有趣;在香港我雙眼忙碌多了,香港凌晨兩、三點鐘也很寧靜,但你總會看見一些事情。」
都說阿Nik的旅遊口味異於常人,2015年22歲的他在東京平白無事爬上一棵大樹,「可能當時我住在東京快一年了,厭倦了石屎森林,想返回大自然。」一失足從大約三層樓的高處掉下,砰一聲背部着地,脊骨一部份插入脊髓,生命從此走上另一條路,雙腳及臀部失去活動能力,在輪椅上待了好幾個月,醫生說他可能餘生不能再走路了。
他憶述:「為了離開這張輪椅,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我知道我是可以的,在離開輪椅之前我要一直戰鬥。如果我想再次走路,哪怕只有丁點兒機會,我的身心都要完全投放在這個目標上,即使只有兩成機會可再走路,甚至是一成、百分之二我仍會這樣做,嘗試將這百分之二機會轉化成甚麼都好。如果我不盡力一試,不豁出去,之後我面對不了自己。」如此意志真有點像軍人,在此之前他的確幾乎投身了軍隊,只因輕度色盲而打退堂鼓。
這個人心境與真實年齡不相稱,記者問他為何人生總是多波折,他說:「It'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highest highs in life without understanding how low it can really go.(未去過低谷,不可能攀上人生高峯。)」其父也提醒他:「Nothing great comes without hard work.(成功須苦幹。)」正正憑着這份驚人鬥志,遭遇人生最大低潮而意志並不低沉,阿Nik說得很禪:「要樂觀,為自己、朋友、家人戰鬥到底,而如果你做到最好,不管你最終情況怎樣,你的心都會得到和平。」後來終於可以撐着兩支枴杖走路,再進而改用一支手杖。
克服自身傷患 籲港人奮戰
他的情況跟香港人走上街頭抗爭差不多,「就是樂觀,以及為了達到目標全力奮鬥的精神,我參與遊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我生命中經過一些難關,而現在香港經歷困難時期,前路也多波折,但我很受香港人的樂觀及毅力啟發。香港有把聲音,而這把聲音值得被聽見,即使看起來前路困難重重,甚至很多證據顯示越來越難,但這個現實無阻二百萬以上的人出來向政府表態,全世界一定注意到。如果人們不發聲,令聲音被聽見,將來大家就會後悔,這是最令人傷感的事。」
他接受了自身傷患,即使今次站在我們鏡頭前也不願放下手杖,「也許你可以將《逃犯條例》理解為香港一次傷患,要從重傷中康復是極難的一件事,可能很令人沮喪,可能極難找到意志去戰鬥,但若你不做到最好,若你不為了你想要的戰鬥,前路將會很難走。」據他看香港問題很多,例如特首不是民選產生,今次修訂《逃犯條例》只是浮出水面的一角,「不滿情緒由來已久,水一直很熱,這個議案成了沸點,二百萬人才走上街。」
阿Nik和香港都小勝了一仗,前路再難也不擔心,「當然我經常碰到新的問題,而我擔保這不是香港最後一次面對困厄,但大家付出的已帶來改變,在這次運動成就了一些事,沒有理由不能再做一次。」他最佩服6月16日示威和平冷靜,事後年輕人清理所有垃圾,看樣子很多不過16、17歲,「在我看來他們就是香港下一代政治人。」
阿Nik恒兀兀苦練單車已八個月,準備明年代表加拿大競逐傷殘奧運,比賽地點正是他熟悉的東京,到那時候大家不妨留意一位藍髮單車手,「可能到時我會染上粉紅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