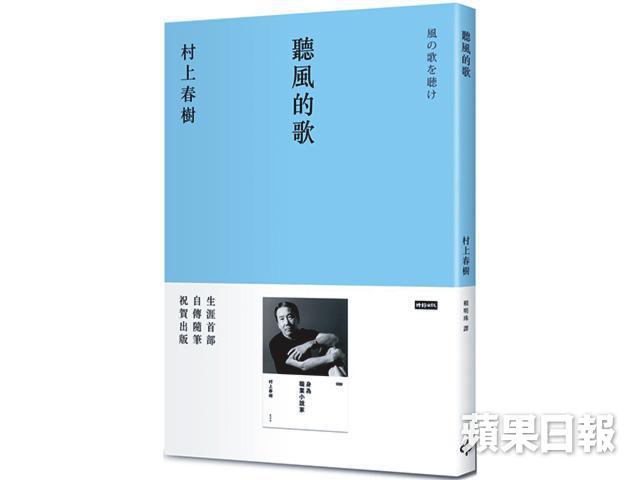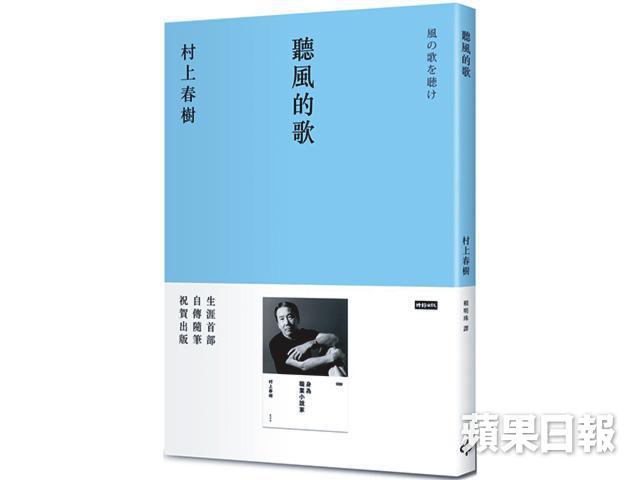
【WriteHouse裏的人】
三月聽賴明珠的講座,四月看劇情式紀錄片《夢見村上春樹》(Dreaming Murakami)。在漆黑的電影院裏,佔一整個大銀幕的綠色草叢,隨風晃動,輕柔如歌。我看到風,心裏感動。
如陳耀成在《我們有雨傘》對談會上引用T.S. Eliot的詩《荒原》(The Waste Land)首句:「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在最殘酷的四月,地下的根要春雨喚醒,我,想聽風裏的歌。
完全的絕望 並不存在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全的絕望不存在一樣。」村上春樹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開首第一句。紀錄片中,丹麥繙譯家Mette Holm繙譯村上春樹的作品已經二十年,她媽媽曾對Mette說:「若果沒有村上春樹,你甚麼都不是。」繙譯在於她,不是紙上工作。在作者一整個世界裏,任何人都有權隨心遊走。
《夢見村上春樹》導演Nitesh Anjaan把丹麥女繙譯家的工作視為一個共同創作(co-creative practice)。我認為,譯者,一若讀者,可以把作家個人經歷有軌迹地延伸,包括他曾經的生活,有過的幻想,這一種自由,比創作更高更大,那就是表達的自由與愉悅了。
介紹電影的場刊寫:「Mette Holm着手繙譯村上春樹的一本小說《聽風的歌》時,一隻兩米高的青蛙突然出現於東京。巨蛙似是將Holm帶進了村上小說中的幻想世界,召喚她對抗巨蟲,以阻止對方用仇恨摧毀世界。」大青蛙有時在咖啡室出現,有時在公園的滑梯上,在虛構與紀實的平行世界裏,是無邊無際思考與表達。我想,一切的意象,都沒有特定的解釋,而是無盡的再想像、再解釋。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全的絕望不存在一樣。(There'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writing, just lik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despair.)」
就為了這一句,Holm跟不同的人討論村上的文字,包括在日本及德國的朋友。她生活化地,一點一點走進村上的世界,慢慢了解他描述過的東西,到日式小酒館跟人閒聊村上,在吧枱看那個沉醉在西洋老歌的日本老闆,在上野跟衣着平凡的外國學者一起吃拉麵,討論作家,完完全全進入一個異國而自由的文化世界,在繙譯裏看見另一種生命。
我並不是村上迷,朋友對早前賴明珠在中大的講座鞭撻程度,我是既同意也不同意的。直至我再跟這位極具批判性的評論人去看《夢見村上春樹》,它開啟了一種自由的想法,讓我緊張的揸車去小Connie家拿走《聽風的歌》。朋友到訪,我揸車去買食材,也會幻想自己是Jamie Oliver。至於揸車去拿《聽風的歌》,試圖從第一本小說看作家的起點,就更加感覺是極幸福的旅程了。
村上春樹少年時候會買來訪東京的水手留下的英文舊書,他曾自述一個叫哈德費爾的作家令他成為很不一樣的作家,並到美國展開尋找心愛作家之路,從紐約坐上如巨大棺材的灰狗巴士到俄亥俄州小鎮,在心愛作家墓前獻上蒙塵的野玫瑰後,合什,然後抽菸。生死安詳,閉眼聽雲雀的歌聲。
心中有一個作家,就能創造一段令自己享受的旅程。911那年那月,我剛在古巴,到訪了海明威故居,探過他的百多歲老助手。然後,在Matanza海邊酒吧餐廳,輕輕點一杯海明威愛喝的Mojito,我幼稚的看着薄荷葉笑起來,像看着一杯文學再生花。
語言這東西 是激烈的武器
在賴明珠的譯後記裏寫,村上曾經說過,他學習哈德費爾寫文章,把前人「以文章為戰鬥武器」當為自己的寫作抱負,並於2000年3月在《Eureka》雜誌說過:「我認為語言這東西,是激烈的武器。」
《聽風的歌》結尾,村上透過偶像作家的墓碑銘誌引用尼采的遺言,「白晝的光,如何能夠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優美深沉對立的哲學語言,吸引村上,而村上的想法,吸引誰?「我既是一個pessimistic(悲觀的),常被黑暗的心所吸引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樂觀的moralistic(重道德的)人。」
四月之冷之酷,真實生活有這麼多人有這麼多磨難,寫作會快樂?村上是這樣看的:「寫文章也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為比起活着本身的困難來看,為它加上意義是太簡單不過的事了。」
當我看着銀幕上女繙譯家Mette Holm走進一個有層次的綠色森林,心裏開闊,一些一瞬即逝的語言,或許頃間是無法記着。我能想像繙譯的孤獨及必須孤獨,但女譯者認真對待村上真實世界的細節,勇敢的爭取想像或是夢想的空間,她在紀錄片的繙譯旅程,也是無數觀眾各自的思想旅程。要發現村上春樹,還是發現自己?跟村上相遇,就如片末,Mette Holm準備出台與村上對談之時,從後台看台前的光芒,大家期待的,讓大家各自去尋找好了。
「擁有黑暗的心的人,只做黑暗的夢。更黑暗的心連夢都不做。」《聽風之歌》祖母留給主角的說話。在女譯者的思想世界裏,不能失去自己的心,也不能失去愛的力量。四月,我看到如風之歌。
作家:冼麗婷
fb:sinlaiting.j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