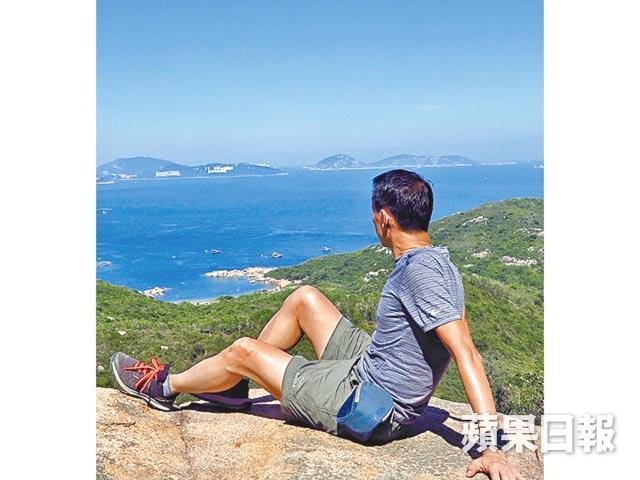【野人周記】
人為的環境轉變,短短一年,經已可以翻天覆地。面對轉變,有人喜歡,有人失落;有人想當然地認為在地人定會歡迎,但有人發覺並非必然。
巴亨丹達(Bahundanda),是尼泊爾「安娜普納大環」徒步路線途經的一條山村。山村一般建於山腰或較低位置,巴亨丹達卻與別不同,村子中心在海拔1,300米的山崗頂上,俯瞰着深邃溪谷與層層叠叠的梯田。頂上四無屏障,受風雨直接吹襲,也遠離溪流水源,出入亦不便,山頂建村,大部份是基於防衞理由,就像是雄踞制高點的防禦工事。不知道村民祖上在選址建村之際,是否有防務上的考慮,但易守難攻的形勢,卻在不久之前,惹來兵戎相見的腥風血雨。
一路上不難看到村舍石牆上漆上的「鐮刀鐵錘」圖案和標語,這是毛派游擊隊的標記,十多年前巴亨丹達一帶的山區,曾是他們的重要根據地,有一段時期,登山的徒步客甚至要向他們繳納過路錢。梯田滿山,牛羊成群,一派世外桃源般的山鄉美景,很難聯想到,十多年前這裏正是政府軍與毛派游擊隊激烈血戰的戰場,政府軍強攻,游擊隊恃地形死守,結果雙方死傷枕藉。數年之後,毛派已經放下武裝,並通過選舉取得政權,眼前一片寧靜和諧,卻隱藏多少血的印記。
急陡山路引向崗頂,村莊以一棵大樹為中心,廣場四周是一些小商店、幾家旅館和一個公眾電話亭,通通髹上清一色的湖水藍。在旅館前的樹蔭下午餐,聽旅館老闆說,近來經過的人流少了,生意不太好。尼國政府為了開發旅遊,當時已開始沿着徒步路線開闢行車道,不少徒步者乘吉普車直接上山,不再停留這些沿線村落。巴亨丹達偏離了河谷彼岸的新闢行車道,影響更是明顯。
接近正午,空蕩蕩的村中心廣場一片寂靜,懶洋洋的氣氛,教吃飽了的我昏昏欲睡。忽然傳來一陣喧聲笑語,原來是一隊奧地利徒步團隊,當大多數人選擇包車前往札吉(Jagat)或查姆傑(Chamje)作為徒步的起點,他們跟我一樣固執地全程徒步。步出村口,面前是開闊而深邃的山谷,梯田一直開墾到山頂,十分壯觀。步下谷底,山路一拐,又回到了瑪斯揚第河邊。對岸高陡崖上,一道道山泉飛瀉而下,不過只要目光稍向下移,映入眼簾的,是那大煞風景的影像:開鑿中的行車道在對岸繼續伸延,沿岸山壁上,盡是爆破後留下的纍纍傷痕。
推廣高消費旅遊 村民受惠嗎?
礙於地形,安娜普納山區一直沒有一條完整的可通車的道路,純樸的生活和文化傳統、脆弱的高山生態,多年來因此得以保存。興建深入山區的行車道,主要不是回應民眾所需,也不是為了徒步旅行者帶來的蠅頭小利,背後動機,如尼國旅遊局旅遊市場推廣部高級總監Aditya Baral曾經強調,期望吸引高消費遊客,以取代傳統的徒步旅行者,「要吸引更多的遊客,我們需要興建多些人工的旅遊勝地,例如高爾夫球場、主題公園……中國遊客劇增,他們大多喜歡豪華運輸和住宿設施……」高消費旅遊可以讓當地人受惠,是很普遍的誤會,龐大經濟利益事實上只會落入少數取得發展權的財團手中,貧窮的當地人依然是貧窮,甚至每下愈況。山路被公路取代,加上高消費,徒步客卻步,民宿經營者、嚮導、挑夫等一連串相關從業者的生計亦一併消失。
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的八級大地震重創尼國旅遊業。近月再次走完「安娜普納大環」歸來的朋友分享見聞,災後山區頹垣與塌方隨處可見,不過更突然的,是聽到中水電海外投資在巴亨丹達附近興建的水電站。電力緊張是尼泊爾的急切問題,但深山中的水電站,顯然是為發展鋪路,建徑流式水電站,亦破壞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
世上有一類旅行目的地,叫「趕緊去否則沒機會」,山村巴亨丹達,是教人沮喪的例子。

撰文:Daniel-C
好山愛水的城市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