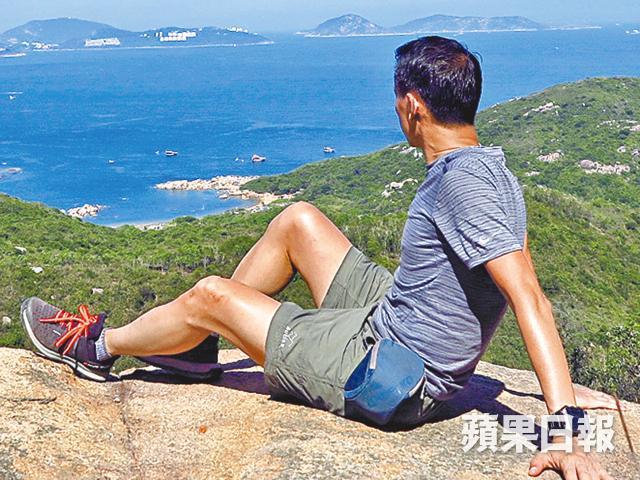【野人周記】
從加德滿都到甘達基專區的貝西薩哈(Besisahar),是漫長的150公里巴士旅程,上一次走這條路,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尼泊爾君主專政剛結束,武裝對抗的毛派游擊隊亦成了執政黨,長期動盪的時局,總算暫時穩定下來。生活依然貧乏,但起碼人心稍定,對於未來,也可以有所憧憬。然而,2015年4月25日11時56分,八級的大地震,把剛建立的,再次摧毀。
安娜普納大環,是尼泊爾其中一條著名徒步路線,繞着安娜普納諸峯,可順時針方向走,也可以逆向而行,西端的起點,是度假勝地博卡拉,而東端的起點,便是貝西薩哈。海拔820米的貝西薩哈是個繁盛的山區小鎮,大街上有一個國家公園的通行檢查站,也有不少登山裝備的小店,登山客們萬一漏掉甚麼,也可以在這裏作最後補給。朋友剛走完安娜普納大環回來,跟他打聽沿途見聞,災後重建緩慢,山區頹垣敗瓦依然隨處可見,問及貝西薩哈與布貝爾(Bhulbhule)之間村莊的情況,卻無印象。也不奇怪,尼國政府為了開發旅遊,十年前已開始沿着徒步路線開闢行車道,為省腳程,徒步者大都乘吉普車直接上山。當年行車道其實已經接通十公里外的布貝爾村,但我還是選擇了徒步。
離開貝西薩哈鎮的大街,不久便進入農村範圍。秋收季節,村民都在田裏忙於收割,飽滿的禾穗隨風起落,翻起重重金黃稻浪;收割完的農地上,是一堆堆小山丘般的稻粒。選擇乘吉普車上路的,一路上也許只能專注地忍受道路顛簸引致的五臟翻騰,無心細味這一片充滿秋收喜悅的田園風光了。
沿着瑪斯揚第河(Marsyangdi Khola)河谷走,不久便來到海拔830米的古迪(Khudi),霧氣從林中升起,斜陽村舍,陌上歸人,詩般的圖畫。穿着校服的孩子們,在村前平地追逐嬉戲,大概都慣見路過的徒步者,對我這個外來人,完全沒有在意。正在呼叫追逐中的兩姐弟,朝着我的方向奔來,我向他們點頭微笑打招呼,姐姐很有禮地用英語回應,年幼的弟弟卻忽然變得很害羞,帶着靦腆的笑容,轉身便跑開了。這是沿途第一座古隆族(Gurung)的村莊。
古隆族啹喀兵 守護邊界救災築路
尼泊爾的古隆族人,對於年長一輩香港人來說,應該頗為熟悉,每年中環舉行的和平紀念日儀式,亦有他們的身影。97年前駐港英軍中,來自尼泊爾的啹喀兵團,主要成員都是古隆族人。啹喀兵團在二戰期間曾駐防馬來亞半島抵抗日本侵略,戰功顯赫,戰後隨英軍駐紮香港,負責守衞邊境,不時要面對攜帶武器的非法入境者,也參與救災、修橋築路的工作,守護香港半個世紀。可惜他們的貢獻漸被遺忘,不少97後出生的香港人,甚至是參加源自啹喀兵日常訓練活動的「樂施毅行者」,從未聽過他們的事迹,也不知道元朗新田軍營的尼泊爾軍人墳場,躺着五百多位客死異鄉的啹喀士兵。
古隆族主要分佈在尼泊爾中部安娜普爾納山脈南坡的甘達基專區,就是安娜普納大環途經的區域,這聚居恆河支流上源、驍勇善戰的民族,曾有自己的王國,十六世紀被尼泊爾滅國後,一直有輸出士兵的傳統,儘管古隆族人能視之為專業與榮耀,為脫離貧困和奴役而選擇為他國捐軀,是何等蒼涼的事。
2015年5月3日,大地震後的個多星期,尖沙嘴鐘樓下有一個為尼泊爾祝福的燭光晚會,跟在場一位香港出生的尼泊爾女孩談到災區情況,她父親是退役啹喀兵,原來就是來自古迪。忽然想起古迪村偶遇的兩姐弟,如果安然逃過地震,如今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很想再走一次安娜普納大環。



撰文:Daniel-C
好山愛水的城市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