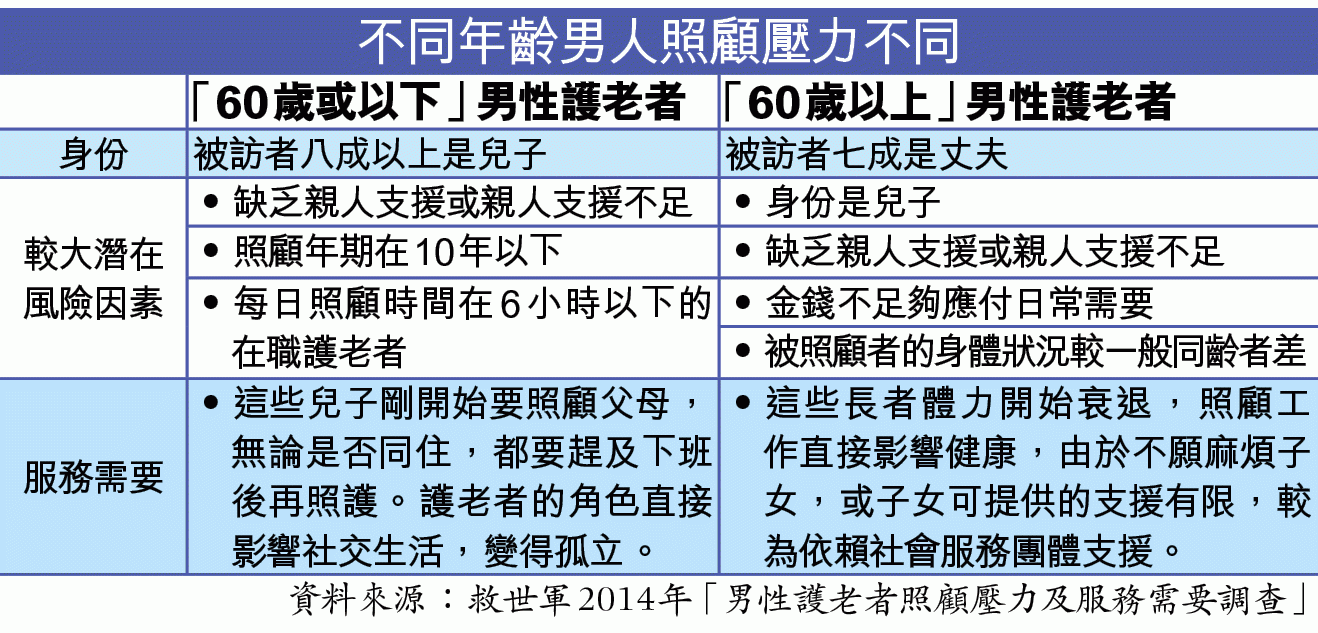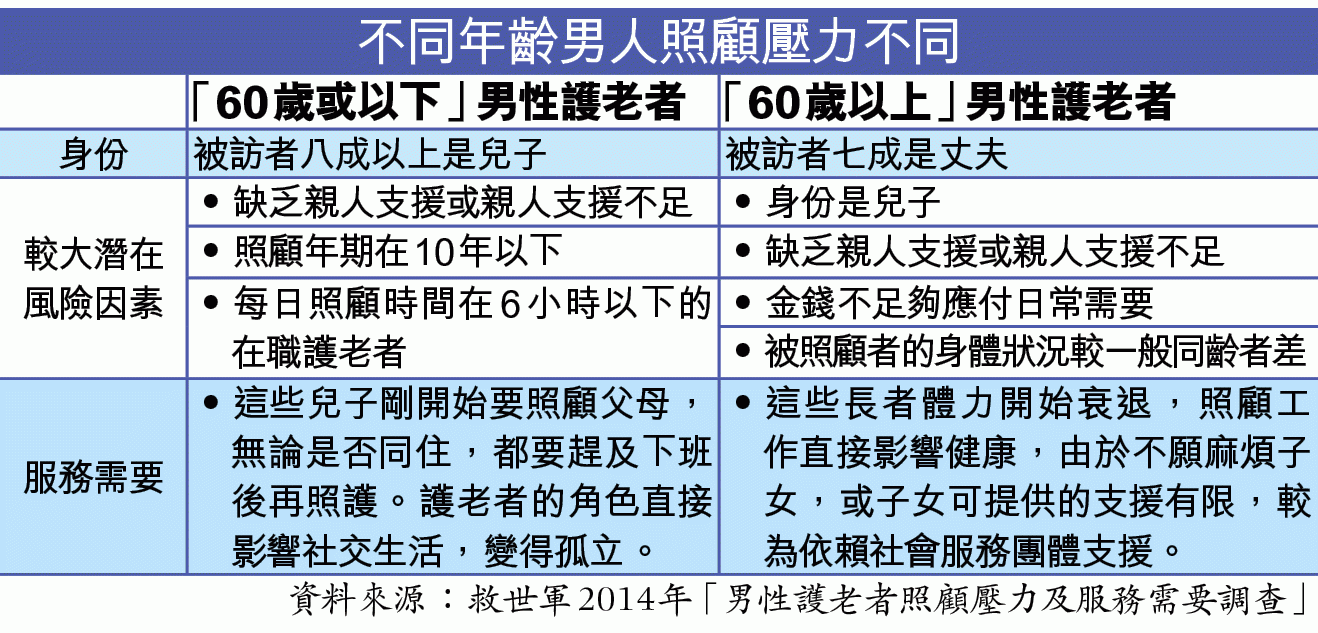
阿澤家有六兄弟,為了照顧爸媽的責任和金錢負擔,不斷爭執。家人還曾經衝口而出:「為何爸爸還未死?」
爸爸曾經輕微中風,2010年腎衰竭,每日都要家人協助進行三次腹膜透析,每隔兩年又會患一次腹膜炎。媽媽有糖尿病和抑鬱症,近年更有心臟病——阿澤為了照顧兩老疲於奔命,至今仍然單身。
「平等分擔照顧的工作?不可能。」雖然兄弟眾多又住在同一大廈,阿澤說:「有些兄弟自顧不暇,奢望他們協助只是緣木求魚。」兄弟本來各付家用,再月供800元作為照顧父母,可是不時會為錢銀吵起來。
爸爸曾經醫務社工轉介,分別得到職業治療師及長者中心社工支援,爸爸卻把上門服務人員趕走,亦不願意參加病者及家屬支援的組織,整天自怨自艾。「媽媽有抑鬱症,曾經服藥自殺,爸爸的言行格外令我們覺得煩惱,即使幫他洗肚,其實也只是開着電視,沒有交談,因為我們不懂得面對。」
爸爸離世前一年,日夜不分、時常失禁,媽媽精神瀕臨崩潰——當爸爸終於離世,大家竟然感覺鬆了口氣。
爸爸走後,照顧媽媽的工作並不輕鬆。「所有糖尿病人的禁忌,媽媽都照樣做!有事又不肯看醫生,我陪她到精神科覆診,等大半天,醫生只看五、六分鐘。」阿澤很無奈:「其實我因為照顧家庭,影響工作評核,短期內都無希望升職。」
最高危:兒子獨力照顧父母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博士相信,男性照顧者的需要一直被忽視:「我有一些男士分享很實際的問題:和媽媽在公共地方去洗手間,非常尷尬。丈夫照顧太太,女兒照顧爸爸也有性別差異,但兒子與母親的差異更大。」
英國、澳洲、日本等地都會在病人確診時一併填寫照顧者資料,分數屬於高危,例如:只有兒子獨力照顧、沒有上班、酗酒等,一開始就有社工介入,邀請參加照顧者小組或按不同需要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