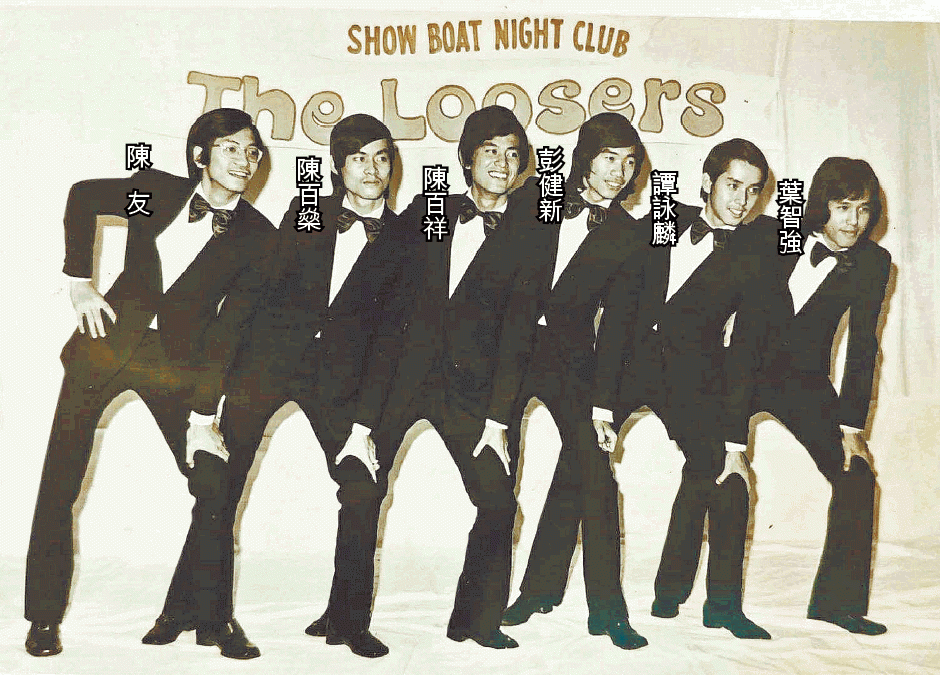
【影壇人物】
陳友都幾搞笑。
對上一次做導演,是1992年的事。1992年呀,別說麥巴比未出世,連施丹都未踢國家隊未做球王。陳友拍的,叫《丐世英雄》,找來許冠文飾演解放軍上尉,因生活困苦而偷渡到香港,票房1,600萬,算差。全年票房冠軍是《審死官》,收5,000萬,《丐世英雄》連十大也入不到。今日如果有齣港產片在香港收到1,600萬,應該會開香檳燒炮仗切燒豬。
東山復出,目標當然放在大陸市場。難道還在意區區小香港?奇怪,居然選拍溫拿的成長經歷。除了方便,還有甚麼優點?Beyond的《海闊天空》或者還影響到一代大陸人,一隊活躍於六、七十年代小香港的樂隊,對於沉迷抖音的大陸觀眾來說,真不知有甚麼價值。都算。這齣《兄弟班》,還夠膽起用一大堆香港新演員,放棄炙手可熱的大陸小鮮肉。陳友是不是對國情一竅不通?
由1993年開始跟大陸人打交道,比大部份香港同業都早,早得多。陳友不是不明白,只是還有點點堅持。「我有個花名,叫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甚麼也不懂,靠自己亂撞亂試,吃到滿嘴損傷。」他沒有開拍新一代的《丐世英雄》,沒有反映現實地講述香港人因為生活困苦而偷渡上大陸。
撰文:方俊傑
攝影︰陳俊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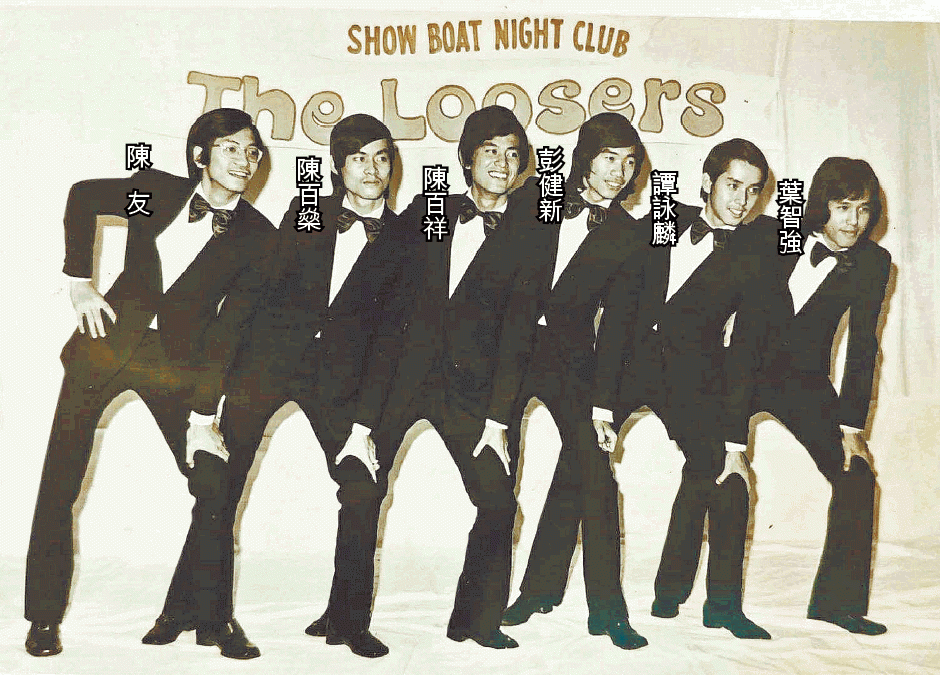
危機意識的錯
作為電影人,陳友的成績算不錯。跟張堅庭合辦電影公司,張堅庭執導過《表姐,妳好嘢!》系列,陳友也執導過《一屋兩妻》系列。錯在危機意識太強。「危機意識太強,特別麻煩。」
時為90年代初期,香港電影市道仍然欣欣向榮,陳友毅然拎起背囊北上探路。「兩件事。第一,開始有全身紋身的大佬揸架車闖入我們位於九龍塘的公司,話知道我阿爸在哪裏返工,知道我老婆在哪裏買餸。第二,越來越多電子媒體,播了我的電影,但錢回不到我手。賣了一個菲律賓埠出去,買家又可以拿着個電影版權周圍賣。於是,我們決定開發未接觸過的市場。」
沒有做錯,只是做得太早。陳友拿着投資者的錢,身不由己。「我想拍電視劇。那時,在大陸拍一集電視劇,四十萬一集,你看看現在?如果我由廿幾年前拍劇拍到今日,不得了。」結果,股東話事,陳友搬了香港《歡樂今宵》的一套上廣州,完全不符合大陸觀眾口味,一敗塗地。「遲十年才上去的話,會比較好。」
錢輸盡,公司結業之前,陳友在國內機場乘坐飛機。周圍的大陸人周圍衝周圍走,陳友正在排隊登機的長龍中,心情本就不佳,忽然回頭破口大罵:「推甚麼推呀,對號入座呀!你們沒有讀過書的嗎?」飛機起飛後,隔籬的老先生認出陳友:「對不起呀,別生氣。聽你的口音,應該是香港人吧。別怪他們,我們的國家窮嘛,之前又文革……」陳友才慚愧,他們大陸人的確沒有讀過書。「香港人幸福箒,大陸人有大陸人的原因。如果我在大陸長大,也一樣。」
時為1993年。往後拍攝《智取威虎山》的徐克當時身在香港,忙於製作楊采妮齣《梁祝》;往後拍攝《紅海行動》的30億大導演林超賢還未當導演,應該正身處《飛虎雄心》劇組。「別人笑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初上大陸,當地人甚麼都話可以;到我真金白銀出了錢,就甚麼都不可以。打他鬧他也沒用。由改革開放初期,無制度無系統無市場,短短30幾年,變成今日的模樣,你說中間的過程有幾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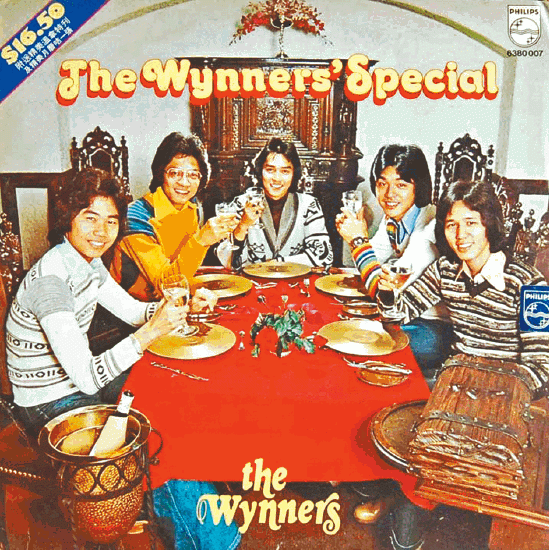
出賣朋友
陳友於2000年由廣州移居到北京,一住又住十多年。照道理,應該足夠貼地,拍國產電影寫大陸劇本也不成問題。「慢慢我變成一個廣告人,做電視節目也為賣廣告,每日要面對審查和收視率。知不知道政府的想法,甚麼題材可以通過,甚麼不可以?我知道。知不知道老百姓甚麼想看,甚麼不想看?我也知道。能否創造出來?我覺得自己不可以,也不是我的強項。」
陳友說,每日每天,無數大陸電影人也在拍攝國產片,香港人無得鬥。「你也懂得說:在香港,播世界盃,只播球賽;在大陸的話,又賽前預測又賽後分析,挖到極深入,計深度,贏十倍。香港人只能鬥種類上的不同。」才衍生出以溫拿成長經歷作背景的電影。反正大陸向來缺乏同類型音樂片。而且,只有身為溫拿成員的自己才拍得出。「溫拿橫跨了幾十年,可以從中看到人生的轉折,這是創作不到的,只可以出賣朋友,談自己的經歷。」
似《歲月神偷》,販賣60年代香港風情,也不失一項賣點。「我不覺得60年代舊香港是一項賣點。我只不過誠實地將60年代的情懷呈現出來。」陳友好記得,當他說要拍一齣香港片,拍香港的樂隊,成員的年齡總和超過300歲,很多人走出來潑冷水。「目標市場不錯是中國大陸,我相信南方人一定識譚詠麟、鍾鎮濤。我唔理大陸人認識不認識溫拿啦!」因為,陳友認為,大陸年輕人跟香港年輕人在最基礎上其實沒有分別,同樣自覺懷才不遇,同樣憤怒,同樣固執。看着溫拿的故事,也可以找到共通點,找到共鳴。「香港的社會結構由甚麼人營造出來?咪又係大陸來的難民?新中國成立、二次大戰、文化大革命,三次難民潮才成就出香港。
「我阿爸阿媽在大陸落香港,阿爸學卜卜齋,我經過殖民地洗禮,讀番書。跟上一代有甚麼衝突,有甚麼摩擦,是我們這一代最與別不同的地方。我想將我們成功的經驗勾劃出來,給大陸人參考一下,說一句:『你們也可以的。』這才有價值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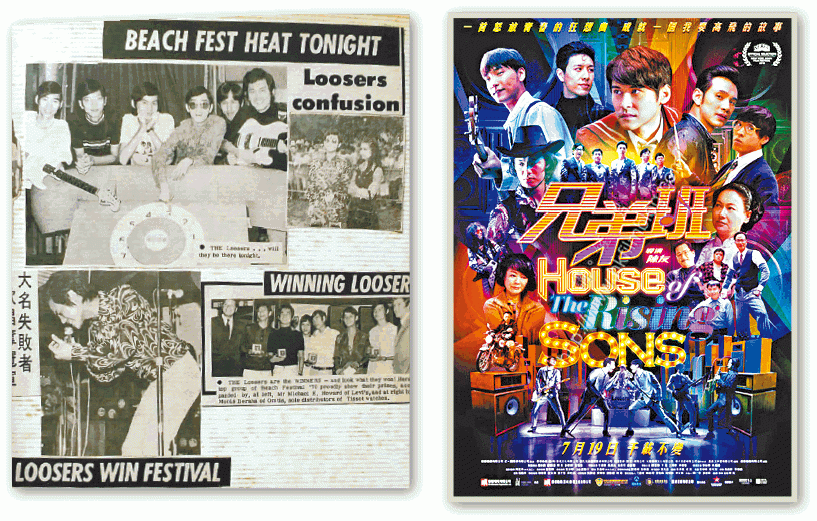
美國與非洲的分別
大陸的朋友會聽入耳?
或者大陸人跟香港人在最基礎上的確是同一類,但呈現出來的,畢竟南轅北轍。陳友也坦言,大陸演員跟香港演員的分別,遠超紐約人跟洛杉磯人的差距,直達美國人與非洲人的大不同。「與好壞無關,只是純粹的不同。」
話說陳友在籌備《兄弟班》的時候,已經打算完全起用香港演員,就似現時找陳家樂演少年彭健新,找錢小豪、惠英紅、任達華、金燕玲、廖啟智等港產片中流砥柱。香港演員演香港故事,本來很合理。當大陸市場遠較香港市場龐大,便相當不合理。「代表投資方的,覺得一定要有國內演員。全部起用香港演員,大陸記者不願來採訪呀!
「我不同意。戲好,就算對演員陌生,記者也自然會來;戲差,請也不會來。」不同意也要接受。結果,飾演少年鍾鎮濤的,叫于湉,天津出身的歌手,未拍過戲。「拍的時候,我辛苦,他也辛苦。」出生於1993年,曾在美國就學三年,畢業於洛杉磯音樂學院。不是那種經歷過戰亂經歷過文革的動盪一代,跟香港同代生有甚麼分別呀?「一邊由共產主義演變成社會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邊是殖民地主義是資本主義,根本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文化差異極大。一班人一齊坐低不發聲,落差或者不太顯眼;一旦拍成電影,差別就好大。要磨滅這種差別,非常困難。」
陳友的最後處理手法是刪改劇本,帶有斬腳趾避沙蟲的意味,遷就大陸一方硬生生插下來的安排。仿似大部份香港人的現況。
如果是白紙黑字明文規定,還好,心甘情願。慘就慘在太多規則模模糊糊。「這部片由銀都機構投資,以我所知,銀都即是國內的駐港影視機構,目的是把香港的訊息拍成電影,再提供給大陸市場。所以,銀都出錢拍攝的電影,會被視為國產片,根本不存在任何起用演員的限制。是基於這個原因,我才選銀都。
「何況,以前的合拍制度,列明大陸演員要佔幾多比例,香港演員又佔幾多比例。回歸廿年了,香港已經被視為大陸一部份,香港演員也被視為大陸演員,係未有明文規定寫出來。」換句話說,香港演員被漸漸邊緣化,被取代,根本不用在條款上動手腳,市場自然自動地決定一切。香港也是。
我是零
開天闢地,損手爛腳,眼看後來者個個正在吃螃蟹吃得津津有味,陳友這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感受恐怕不會太好。他最後悔的,卻是更早的80年代,沒有反對太太跟兒子移民美國。「應該要反對,一家人分隔兩地,影響太大。當時只不過不知道九七後會變成怎樣,對香港前景沒有信心。現在看來,一直留低便最好。」兒子在美國生活,孫兒最近也剛出生,陳友大可以選擇去美國安安靜靜。「如果離開自己的地方,我是零。」
「香港是我的能力所在,離開香港,能力會降低一百倍。在美國,就算我有兩層樓收租,但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價值。我有我自己,我的兒子也有他的自己,偶然碰碰面是可以,但你的生活和生命不應該因為其他人而被影響……」
陳友說,相當後悔讓太太帶住兒子移民美國。原因呢?「個太太會變得跟自己不太相熟,個兒子會開始不認識自己。」今日,香港人未必再有需要為了移民美國而一家人分隔兩地,可惜,我們變了為生活而上北京到上海工作但任由下一代在香港爭入國際學校。
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