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光顛覆,燈火紅塵。香港回歸21年,彈指間滿路繁花。
提起回歸,就想起著名畫家劉宇一所畫的《良辰》,過百位中港知名人士活現畫上;原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另一位藝術家閉門三年創作了一張叫《香港特區新氣象》(Hong Kong Panorama)的畫作,一樣充滿故事。
這畫長12呎、高6呎,一直大隱隱於會展新翼地下大堂的一道牆上,平時不會有人留意,因為它太像一張放大了的香港鳥瞰全景照片,其實是非常像真的畫,它創作花費的時間,比建一幢高樓大廈還要多。畫中三千幢高樓不是用畫筆畫,而是用噴槍逐條線上色。
萬丈高樓是從草稿開始,每幢建築物如宗教儀式般被「重建」,似科學實驗多過藝術創作。
「我的委託人說這幅畫是送給香港人的,97年後英國交還領土,這小島將出現翻天巨變,但當時我還未去過香港,卻很想表達香港的個性和一種觀點。」著名英國藝術家Ben Johnson,努力地回憶着舊事,點滴回眸,恍如昨天才發生。他後來以大型都市景觀繪畫而聞名,出名以史詩式氣勢、上帝視野的造物理念來「重建」當代知名城市,這揚名系列的處女作,就是香港。
撰文:鄭天儀
攝影:趙志雄(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提到《香港特區新氣象》,「這幅畫簡單而重要的陳述是『嬗變』。」Ben斬釘截鐵的說。
九七回歸前,當時的香港電訊與英國大東電報局委託Ben創作這巨作,準備送給香港人作回歸禮物。Ben三度來港拍攝和搜集資料,然後就回英國工作室潛心創作,有天來了一位香港貴賓。
「我收到一位香港收藏家的電話,說他的一位香港生意夥伴想來我的工作室。我沒有門鈴,所以他們打電話給我,說我們在門口,你出來一下。」Ben走到門外,見到一輛勞斯萊斯和司機,突然有人從車裏出來,是一位穿着運動鞋和喇叭褲的女士。

「基於我的草圖她(龔如心)標記了所有華懋的出品,並要求我把她旗下的建築畫得更亮一些。」
「她束着孖辮,轉身說我是Nina Wang(已故華懋集團掌舵人龔如心),我來看你,我不擅長下車。」小甜甜來到Ben的工作室,就盯上那張畫,露出欣賞的表情。「她說有點擔心,因為她在畫中擁有很多棟大樓,但好像都顯得不夠重要。第二天我傳真機有一叠紙,基於我的草圖她標記了所有華懋的出品,並要求我把她旗下的建築畫得更亮一些。」Ben笑着憶述:「當然,我沒有這樣做。」
故事未完,小甜甜還未罷休。
Ben根據香港鳥瞰圖做了一系列八幅的素描。龔如心知道有人買下了其中一幅畫,要送給香港人作回歸禮物,她二話不說又買下同系列的另一幅。「龔如心發現對方已經買了畫,並可能會在那天早上把它交給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那天早上,她打電話給我說,要派一輛非常快的車,想把畫在另一幅畫送給董建華之前送到。」Ben透露說,她要飛車「截胡」的「另一個人」,正是當時香港電訊的行政總裁張永霖。
1997年7月1日回歸後的九天後,在會展新翼舉行贈畫儀式,香港電訊和大東電報局將《香港特區新氣象》贈送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以祝賀香港回歸和踏入新紀元,特首董建華親臨主持油畫命名與揭幕儀式。畫作以1997年7月1日由山頂俯瞰香港的面貌,以中銀大廈、聖約翰座堂及前港督府的正門為一中軸而鋪展。畫中以500種顏色繪製全港三千多幢建築物,當年香港電訊還限量發行以此畫作為題材的電話卡。
1969年畢業於皇家藝術學院的Ben Johnson,被喻為「繪畫建築師」(builder of painting),他一畢業就在紐約的Wickersham Gallery辦了個展,往後近半個世紀作品在各地博物館及美術館展出,作品被不少知名的博物館收購,包括倫敦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MoMA)等。
他每一幅畫總會重新結構,畫如建築要打好線條的根基,再一筆一筆的構建上去,但跟其他畫家不同的是,他不用筆而是用「槍」。談到創作的挑戰,Ben揚一揚手,有種不消提的噩夢感。他與六人團隊耗時三年精心繪製而成,等於普通打工仔六年的working hours。
「最初在香港進行攝影和研究便花了80小時,在倫敦工作室創作時,單是準備繪圖就用了逾2,500小時。」Ben作畫就如同建築施作,工序繁複又費時,以間尺作藍圖、為地基,把各種顏料充當泥土和磚瓦,慢速地起重建一幢一幢房子。
他工作室放置了三台繪圖電腦,負責把城市裏的每根樑柱、牆垣、窗戶輪廓,拆解成局部來記錄,析分出細膩的色彩,再把前、中、後的景觀,區辨出更多的次序和統調,以便切割無數遮色片噴色,最後再透過畫筆進行最後修飾。他2008年完成的利物浦城景,便動用了十人團隊,拼湊了3,000張照片和25,000張遮色片,耗時約三年來完成。
我們肉眼見到的顏色和層次比顏料為多,為求逼真,Ben花上240小時去調製超過500種顏色, 單是畫草稿大綱(line drawing)都動輒花上年半時間,然後再畫到油畫布上。他以特別的噴塗技巧大面積的上色,再透過遮蔽膠帶將陰影及雕花紋路一層層加叠上去,逐條線逐條線上色,最後再透過畫筆做最後的修飾。最幼的線條細於小於0.2毫米,噴製每條線都必須異常小心,花了或過界了就前功盡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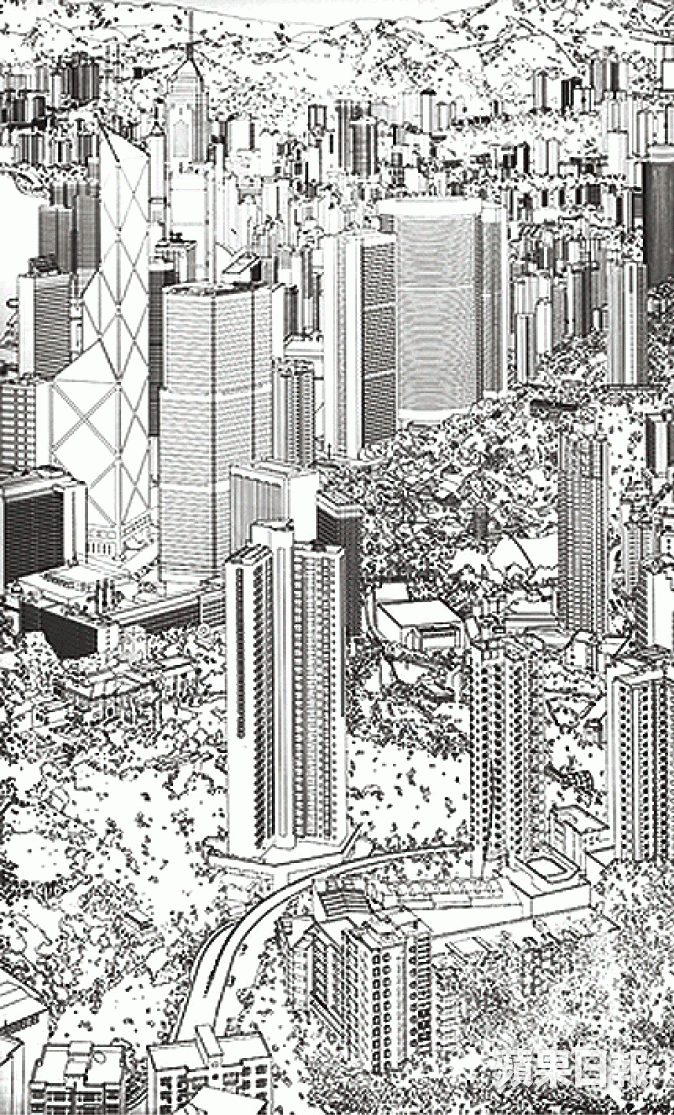
「有一天,我希望這幅畫能放在公共博物館裏。希望它會回歸公眾,孩子們會看到它,人們會看到它,並說這是我們的歷史。」
所以,他要做非常多的事前搜集資料與研究,創作力量同幻想都需要。
Ben說,創作上最難不是技巧,而且香港不斷發展,「這座城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香港人習慣今日經過一幢大樓明天就被拆除,過幾周後,就有一座新大樓蓋起來。發展得比我畫的要快很多,我要預示三年後的香港是怎樣,按發展藍圖構思建好的建築物,才是最困難的地方。」Ben記得,當年看着社會的變化。「我開始感受到來自內地的人的力量,那將是一個新政府,一個新的控制,中國人再次擁有香港。」
三年的辛勞都是值得,尤其是當Ben聽到港人對他作品的評價。
「人們會說,我知道這個建築。我的父親住在這裏、我母親就在那裏做飯、我的父母在這裏相遇、我在這裏遇到了我的女朋友,那就是我們第一次接吻的地方。」Ben認為,畫作呈現香港的「觀點」,就是他第一次來港時感受到的「獅子山味」。
「有一天,我希望這幅畫能放在公共博物館裏。希望它會回歸公眾,孩子們會看到它,人們會看到它,並說這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是甚麼?為甚麼這樣的建築發生了,人們將意識到為甚麼我們的生活改變了?商人會說,沒有我就不能改變,但沒有人社會就不存在,人是社會的基礎。」
後 記
Ben承認,時至今日,中國對許多西方人來說仍是一個很大的謎團。「但我懷疑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否也是一個謎。真正控制中國人的是意識形態?是經濟?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人民。」
連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覺夏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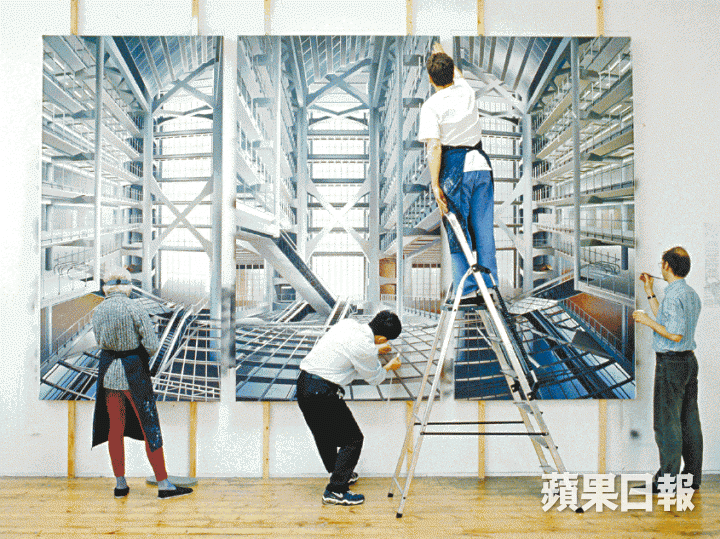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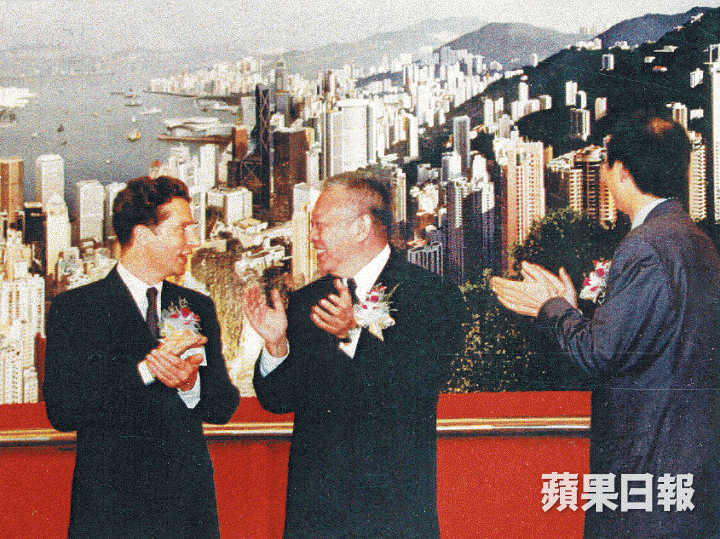
當下香港,依舊星光燦爛,但斗轉星移、面目全非。然後,最大的思考是有沒有然後……Ben想起當年來,淘盡他腦中廿年前偶遇的香港。
「我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這個城市永遠不會熄燈(never turn their lights off)。世界上沒有任何城市晚上10時、11時、12時燈光不會越來越少,人們二十四小時工作,充滿都市能量,每個人總是很有方向地向前邁步。」
時光荏苒,在跌宕起伏的廿年間,香港人經歷過天災人禍、沙士股災、第三波移民潮,港人仍是無懼世間迷離,很有方向地前進嗎?Ben跟我問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