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賭講賭運,原來租舖一樣要運。入行50年的末代手雕麻雀工匠張順景,直認不諱。「呢間舖租咗20幾年,未執係因為業主好人收平租;之前嗰間都係樓梯底舖,細一半,百幾蚊月租,個業主一年無嚟收租,我打去問,佢話你攞副麻雀過嚟當租啦!」那些年,一副二、三百元的手雕麻雀,竟可抵一年舖租,「以前就係有人情味」。三代經營麻雀舖,他直認錯過多次買舖好時機,業主夢難圓,卻總幸運遇上好業主。「係你嘅就係你,無得恨……」順流逆流,大半生與麻雀賭具為伴,偏偏「唔識賭」的他笑着說。
記者:呂麗嬋
每年只有大年初一放假的景叔現年65歲,「做舖最困身,一日到黑喺度坐監,邊有時間賭吖」。廟街牌坊對出的佐敦道,人潮熙來攘往,標記麻雀藏身樓梯底,貨品包羅萬有,各式麻雀、天九、紙牌及籌碼,儼如賭具博物館。大半生與索子萬子筒子為伴,就算不是賭神,至少是賭徒吧?「梗唔係,新加坡麻雀嗰幾隻動物牌,我都係照住啲貓同老鼠喺度雕,你問我點玩,我真係答唔到」。架着眼鏡的景叔,正為麻雀上色,口在說,手卻沒停下來。



「唔死就唔使活化,無生意,好多師傅一早轉行做看更,係我有間舖,賣住啲其他嘢先未執。」
傳統手藝,都在說活化,倒是景叔心水最清:「唔死就唔使活化,無生意,好多師傅一早轉行做看更,係我有間舖,賣住啲其他嘢先未執。」自從電動麻雀枱出現,加上大批生產的機雕行貨佔據市場,被迫封刀多年的景叔笑言,鹹魚原來真可翻生。「以前一年都無一、兩套,呢半年就超過十套預訂,三份一係外國遊客,其餘都係本地人,可能擔心我哋呢批人退埋休,無人再雕啩,都係話買番去珍藏」。四、五千元的手雕麻雀,有價有市,只因物以罕為貴。
「你嚟之前,先有兩個新加坡遊客嚟,本來想買手雕麻雀,嫌太貴,雕兩隻單字,都好吖,又有一、二百蚊,幫補吓我食餐晏」。過去門庭冷落的小店,在本土懷舊熱下,竟出現逆市小陽春,吸引大批愛懷舊的年輕人光顧,在社交網站口耳相傳,成為打卡勝地。有客人主動提供款式字樣,要求訂製,例如情人節,五隻麻雀並列的「情人節快樂」大曬甜蜜;結婚回禮,麻雀上來個囍字順理成章。
「母親節最好生意,最強最佳最正母親,就算過咗母親節,一樣有人嚟整,啱啱先整咗個最強媽媽.嬌;爸爸就唔得囉,父親節都無定單」。大抵自古以來,師奶才是麻雀枱上的主角,爸爸們恨都無謂。「好似手寫小巴牌,𠵱家好多人鍾意,以前間舖就喺我隔籬之嘛」。外國旅遊雜誌《Time Out》、日本期刊都來訪問他,衝出香港,被冠以匠人寶號,讀市場學的女兒為他在社交媒體開專頁,呼籲外國遊客打卡分享;甚至有年輕人慕名來到舖頭,希望拜師學藝。
「都有啲機構邀請我去教,仲有錢收,但講真,學咗都唔會做,呢行係無得做㗎嘞,做埋我哋呢代,畀我做多幾年,散埋呢度啲貨就唔做……同埋唔係你想唔想做,係根本無材料畀你做」。行裏有所謂「入料」、「開料」,景叔說即是將大幅麻雀膠原材料,用切割機器切成麻雀大小。「以前呢個工序喺香港做,我阿爺生前就專磨牌,用沙紙樹葉磨到佢平滑,後來啲廠俾人話污染,罰錢罰到搬晒上大陸,𠵱家剩番三、兩間,個個都七老八十,我幫襯開嗰間廠,成日無貨,話搬廠,上一代人係咁,無人想做到執笠,覺得好難聽」。
賭枱上有所謂莊閒,若供應商是莊,他自言便是閒,「無料可入」,想繼續做都無可能,被時代淘汰已是預料之中,「可以做到𠵱家,都係因為業主好,唔係執咗好耐」。手雕麻雀無法再生存,但曾幾何時,打麻雀卻是「最入屋」的聯誼活動,倒出麻雀「打番幾圈」,以指頭在牌面「甩牌」,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也幾乎每家每戶皆有一副麻雀「鎮宅」。「以前玉器市場隔離,全部都係麻雀舖,十幾間,成行成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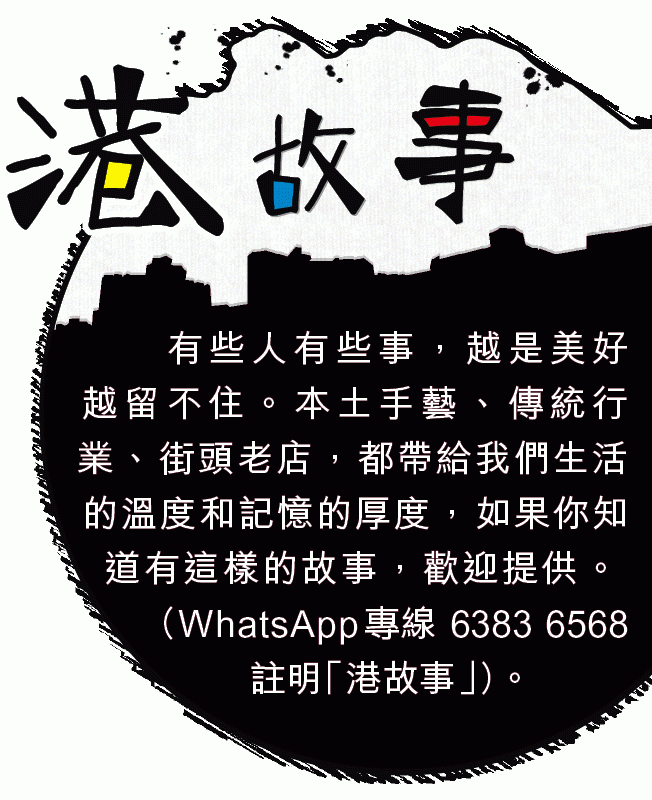
「我係街童,成條街啲舖熟晒,好細個已經喺舖頭幫手執頭執尾,最初係上色,後來就用啲舊麻雀試刀。」
自小在廣東道街頭打滾,七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大,子承父業,順理成章。「我係街童,成條街啲舖熟晒,好細個已經喺舖頭幫手執頭執尾,最初係上色,後來就用啲舊麻雀試刀。」那些年,人人都在忙,自動波練習,遇上爸爸和其他師傅路過,從旁指點兩句就是,並無正式拜師學藝。「雕一隻牌,要雕十幾刀,唯有筒子唔使,用個鑽固定;雕錯隻牌就要丟咗去。」對比刻板的機雕成品,他說手雕麻雀,更見師傅各自風格。
「我哋行內人,一睇副牌,就知出自邊個嘅手」。以雕刻刀勾勒圖案,然後用毛筆把顏料塗在麻雀圖案或字上面,待顏料乾透,就用銼刀鏟去多餘顏色,一隻手雕麻雀便大功告成。「其實工多自然藝熟!」說來雲淡風輕,何止麻雀,用茶葉罐改裝的「照明、加熱」兩用燈,都是出自他的一雙巧手。「以前嗰個年代,做細路仔有咩好玩吖,我哋住喺避風塘附近,捉魚嗰支魚槍,都係自己做」。那些年,快樂很簡單,仍然手不停的「手作王」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