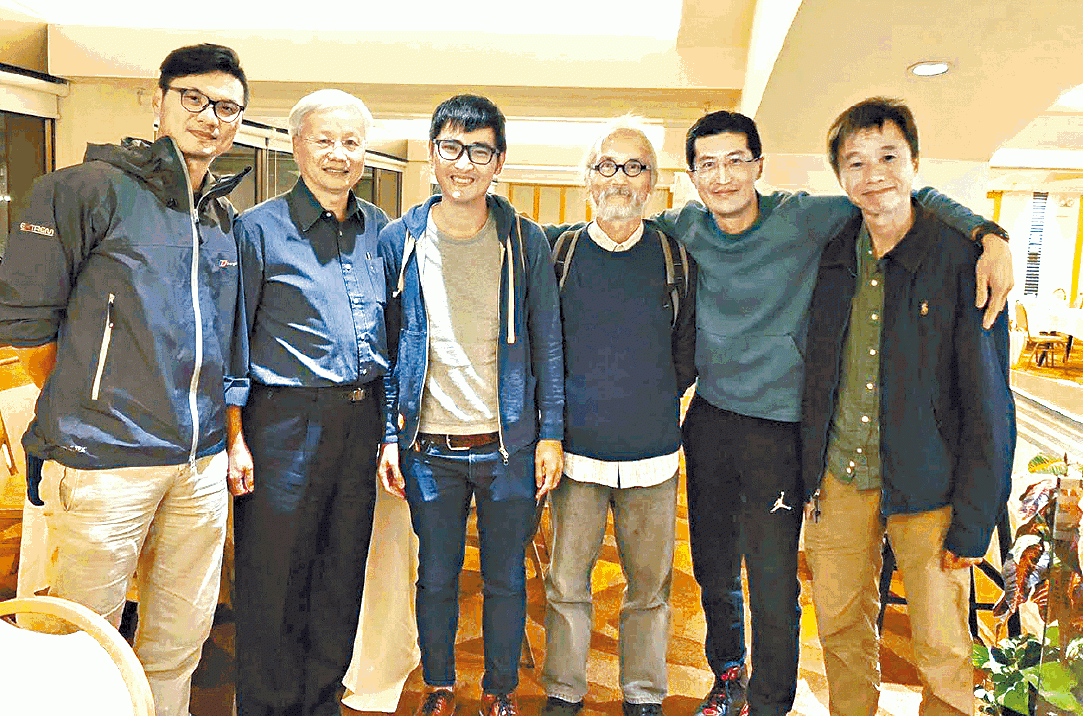
周永康的成長,他今天的內心世界,是這樣煉成的。
11月27日晚上,周永康跟中學老師吃晚飯。退休視覺藝術科老師楊秀卓最想不到的是,當初比較「訥言」的學生,今天可以「口若懸河」; 退休校長只求學生當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幾個教育界中佬,很樂意跟剛出獄的門生拍照見報,毫無壓力,並期盼師弟妹以學長為榮。自由純樸,關心社會,是這所粉嶺中學的特色。相中每一位老師,在周永康心中,都曾經有特別角色、做過特別的事情。
特別的老師,教出特別的學生?那晚師生敍舊,也談到北京驅逐邊緣人口。傘運之子,怎不是跟香港教育有關?
周永康跟記者說過去與將來之時,一副佛心,「前面的路,不是說好多年之後,下一個剎那,已經是將來」。他說話有時會意想不到地動聽,因為,他有純粹的柔韌與清醒。
在香港出生,先居於九龍,後來隨父母到東南亞生活了一段日子,周永康曾先後於錦綉花園及粉嶺一個私人屋苑居住。因為小學當插班生,他沒有太多死黨。可是,他對世界充滿好奇,除了請媽媽帶他到公立圖書館看書,特別喜歡聽長輩說話。特別記得在上水陳式宏學校念小學,校長好慈祥,愛在早會分享故事。
「可能是關於他前一晚駕車去某個地方,其間遇到一些事情,開首有一個想法,過後,又有一個想法,於是跟學生分享自己的反思。」說話內容忘記了,但說話的一幕,卻是很深刻。慈祥的人,留着小孩子的記憶,因為,他留下了小孩子的心。
到中學時候,周永康形容裏面有好多「激進」老師。不時在星期日《明報》刊登作品的老師楊秀卓,「他曾經有一個藝術作品是把自己赤裸困在籠裏幾天」,而藝術家老師,對周永康10年前一件藝術作品也很深刻,準備寫文表達分析 。
其他老師,當年也經常在早會、周會分享好多不同的現實議題,包括香港水資源短缺、貧窮問題、香港板間房問題等等。周永康看到其他人狹窄的居住空間,感受特別深,因為,他住的地方,大多了,「為甚麼大家的生活是這樣的,這時你心裏面好激動。你會想,為甚麼這個世界會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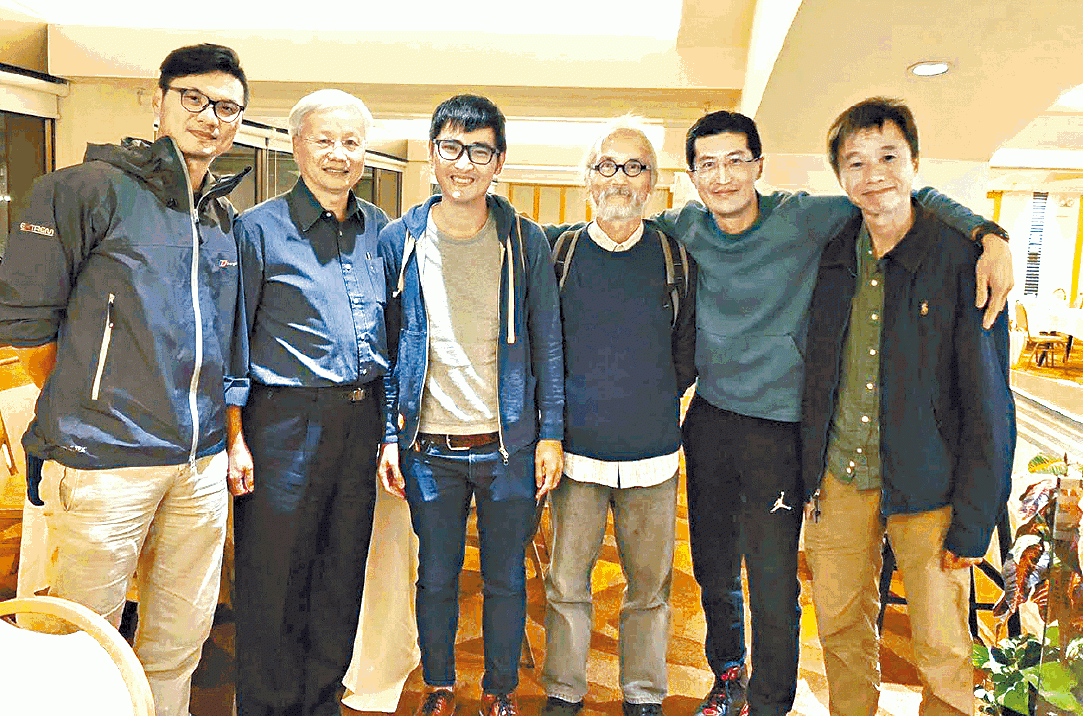
老師哭談六四 頓生疑問
十多歲時候,他在廁所開始看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在批判裏中感受民族大義。回到學校,站着的早會,他會思考,坐着的早會,他也會思考。「有些歷史科老師,講到年輕時代的八九六四,在台上講了不多久便哭起來。那刻,你又會很震撼。你會覺得,為甚麼會是這樣的?你會有很多疑問。」有時,中史老師類比現代社會、現代政府,「以前漢朝有中書省,當代政府行政架構又是怎樣?講貧者無立錐之地,是講圈地嗎?香港囤地,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老師不但把課本扣連現實生活,甚至用一場埋身預演,讓學生直接面對權力的從屬關係。「有個中史科老師好癲,因為要講學生與老師的權力關係。突然之間走入課室,指着學生說:『你做乜咁咁咁?』質問一輪,再開始上堂,然後才解釋古代政府權力運作,誰發號施令,誰聽誰的命令,與及官員黨爭等等。到最後,他分析學生與老師的權力關係,問學生有沒有想過權力怎樣形成?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健康?」
這一所位於粉嶺的信義會心誠中學,在七十及八十年代,是北區排名很低的中學,在對面的警察訓練學校,曾經是不少學生心裏的出路。
一間學校像一個人,落泊時候,偌大的操場花園都像有點破落,至九十年代,卻偏偏絕處又逢生,轉為直資學校。原來,當有一班人願意,一所學校的命運是可以被改變。
「我在心誠看到,以往可能是一間無沒多好的學校,但當有很多好有心的老師支撐,學校可以運作,然後有一個轉型機會,令更多有心老師校長進駐,獲得更多資源,視野不同,一步一步,都是人做出來的。」
周永康之後入讀的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以文化政治哲學理論解構文學文化,權威可以被拆解。就如學系本身,在1989年世界各地迴蕩翻天變化、創新與暗湧,香港從殖民狀態中轉變,台灣已經解嚴,柏林圍牆也倒下,當時一批老師,成功把比較文學從傳統港大英文系(原稱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分裂為獨立學系。
按該系前教授司徒薇解釋比較文學始源,二戰時,因為納粹迫害,歐洲各國不少學者逃亡英國及美國等地,凝聚了不同的跨國界、跨文化、跨學科學術精英。形成從世界視野、文史哲全面思維的一門學科,一種古典的做學問方式。台灣的大學,則稱此為外語系。
司徒薇是該系前系主任Ackbar Abbas得意門生,Abbas在她眼中,思想跳脫有創意,關心身處環境,也能從容於逆境之中。他2000年代離開以後,一度剩下接任的張美君一人守在殺系邊緣。2004年司徒薇從美國回港,在一個研討會跟張美君相逢,被這位獨自守系女學者感動,惺惺相惜,最終兩人結聯力量,撐起一個學系。今天生機再度煥發之時,張美君已經離世,司徒薇亦於今年8月提早退休。
周永康的老師們,包括楊秀卓、張美君、司徒薇,引證香港自由盛世,有一種人,認為對的事情,不惜一切,不怕一個人,也可以一個人,繼續堅持。直至周永康這代學生,他是這樣看這個學系的。
「有人話以前的比較文學系很rebellious,你有這感覺嗎?」記者問。
「我覺得是和不是都有。它有很解放的地方,亦有好多危機,令你變得好執迷不悟」,過度批判是為執迷不悟。周永康選修比較文學,是因為裏面講求文史哲貫通,甚至融合社會學,除了知識,也講實踐,「你可以說我實踐上有錯,但不代表我當初認為讀書不重要」。
知易行難,知難而不退,他這一代的特質,似乎就是這樣的自然發展着。
3年前傘運期間,記者找過司徒薇,想了解周永康。最公平的記憶是,老師好肯定,只要周永康願意,他的能力一定可以修讀哲學碩士及博士,無論香港或外地的大學,都應該會取錄他。也在那個時候,記者聽到,周永康很尊重的系主任張美君病重。一場風暴過後約3個月,她於2015年2月不幸辭世。
今天,學生還記得這個系主任。因為,當年每一個新生都要上張美君的Introduction Course。他說:「有些人覺得她大癲大肺,卻也是學養好深、好寬容的人,這方面,是會潛移默化。」
如果學生還記老師的一舉一動,因為,他也記自己的一舉一動。
周永康上系主任堂,經常遲到。而且還坐在前排,「因為,後排已經沒有位」。當時有位tutor私底下很認真地跟周永康說:「張美君好鍾意你,不知何解。不是說話『潤』你,而是事實。」
如果你感覺自己不是特別smart,又不是出口論點無數,跟系主任在前排四目交投,又有甚麼好處呢?「冇冇冇,可能我經常穿的外套,好紅噹噹,好似一個利是封。大佬啊,你穿這個樣子,誰都看到你走入來!」年輕的迷戀,往往是別人眼中的自己。不羈、紅色的躁動,非規範行為,在女教授眼裏,年輕不正應該如此?
「就是說,無論你是怎樣的你,她都會喜歡你?」記者問。
「是,否則做不到一個如此liberal的情況。」張美君在錄影教學片段大致說過:有些事情,如果你想做,要即刻,要適時做,你不做,那個人是會走的。
張美君於2011年獲得傑出教學獎,2015年去世後,系上網頁悼念她,形容她一輩子做了三輩子的事情。笑時嘴唇紅得讓她看似一粒士多啤梨的張美君,令周永康相信世間有天使:「我向來都感受到她是個好liberal的人,包容性好廣。她背後好像有對翼攬住好多人,那是她的光芒。」
「她(張美君)怎樣影響你?」
「學風,這種學風是他們的為人及教學,要我們經常反思甚麼是真相、事實。他們好關心學生,你感受他們揮發出來的能力。這個人,你真的好喜歡她,你被她吸引了。」
後來周永康信佛,是受司徒薇影響。按周永康所說:「陳允中是司徒薇的partner,嶺南有3位教授退休,羅永生、許寶強及陳允中,3個都是萬人擁戴的名師,良師益友。開始認識他們是雨傘之後,雨傘運動之前,我跟他們交情很淺。陳允中在學聯罷課時候做公民講場統籌,司徒薇在我報MPhil以前做過《學苑》,我修過她的課。」
2015年新年,司徒薇送了一本《The Joy of Living》給周永康,從佛理到生活,開壠了周永康的心。「 當時我心裏有好多疑問、煩惱,雨傘之後大家情緒大起大落。我自己如是,身邊的人如是。退聯發生,我受到好多批評,如何理解批評,有些同路人好傷心,你不知怎樣回應,有些事,有理說不清,有些你認為不公道,有些你內疚,有些你不知如何解釋事情的複雜性……」
一個人送的一本書,有時成為一個階段的出路,那是因為書裏面,找到自己的投射。
「他是team builder 本性慈悲」
司徒薇對記者在電話裏這樣形容這位傘運學生領袖:「他不會兇猛,本性溫柔敦厚,喜愛看也斯的詩,人緣太好了,因為『抵得諗』,才會被人選了上來(學生領袖)。他關心同伴及身邊的人,絕非政治動物、戰鬥機器,他只是個team builder,關心別人,都是出於本性慈悲。」她甚至認為,周永康追求的民主,不過是他追求眾生大公平、大慈悲的一個很細少的部份。
司徒薇曾教周永康的科目包括學習把哲學應用於生活的Advance Theory Seminar,也有一科是「一對一」的獨立研究,周永康選擇了研究香港獅子山精神的論述。從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精神面況,到2000年後被梁錦松用作官方和諧論述,至雨傘運動再次被爬山俠客在獅子山掛上「我要真普選」,又再重新扳回一種民間闡釋主導位置,周永康以不同年代的獅子山精神,演繹香港人對身份認同的不同看法。
他喜歡聽司徒薇的後殖民理論,「香港是後殖民城市,好多時因為英國殖民文化政策,令到今日有好多遺留下來的政策或者習慣、喜好、偏見,是我們完全沒注意的」。至最後一課講佛學和哲學思考,東西交流,西方政治思想之不足,以佛學彌補,達到真正人的自由、自主,「你發覺,哇!好厲害啊。博通所有事情,而且make sense,完全融會貫通」。
他開始明白,佛學不是入廟拜神,而是可以說服人的智慧,更感覺自己被說服了。「看《The Joy of Living》,修行僧人對科學家好有興趣,對創新科技及知識好渴望對話,然後你見到好多西方科學家想同佛學有聯繫、對話,想了解到底心理學是怎樣一回事,探索人的內心,面對焦慮、憤怒、恐懼、情緒,怎樣跟他們同生共存?」如司徒薇所說,人的腦袋是有彈性的,佛學上的慈悲、智慧及力量,能改變身心靈及外在環境的困苦。
佛學、修行、投入社會,周永康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一年,也抽時間到倫敦西南部一個有修行人參與的中轉社區Totnes,了解社會運動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完成哲學碩士課程後,為了參與公民抗命佔領運動還沒有「找尾數」,他甘願回港,面對覆核刑期。
學佛的人,入獄當刻,懂得觀照自己一舉一動,「從上扣,到步上囚車,駛出法院,走上公路,直至到達監獄,我一直留意着,好想把每一刻都記下來」,他希望用智慧面對一切後果。獄中,也一心等待朋友寄他法國哲學家Michel Foucault關於監獄規範哲學理論書。最終等到出監,書還未寄到手,「我跟他說,沒事,飲茶時候你把書帶來,我真的好想看」。
囚中年少日,羅冠聰總是不停書寫他那本「死亡筆記」,聽說現在仍在趕工。如果周永康提筆書寫,懲教職員會掩着胸袋名牌探頭來好奇一下,知道是寫獄中情況後,說一句「衰鬼」便走開。「有朋友說,藍絲跟黃之鋒時常針鋒相對,之鋒會挑機,跟他辯論政策。日見夜見,不停辯論。」
「懲教人員有分藍絲黃絲?」記者問。
「我聽之鋒那邊有個好明顯有藍絲特質的懲教職員,我這邊不明顯,甚麼光譜都有。由參與、聲援、心裏面支持都有。」
「有無人靜靜雞講出口:『我支持你㗎』?」
「有嘅有嘅,有靜靜雞,也有心領神會的。」
曾經有懲教職員做了某種事情,周永康跟他說多謝,對方說:「欠咗你哋㗎嘛。」然後大家不說話,心照。亦有職員開首對他很有成見,認為他搞事,但到後期也會跟他說話,「有職員對我說:『其實你個人不錯』,或者會跟我說:『共勉之』。」
學佛人出獄,又是另一番觀照,「上了懲教車,開出監獄,前往高院,突然呼吸自由氣息,那時我思考,自由其實好貴乎內心是否能自視自己的想法。為何那刻有這種自由的想法?是我太水皮,修行未夠,好膚淺,所以有種誘惑,覺得出面世界比較自由嗎?」他說佛陀修行跌跌碰碰,一樣學過各家各法,也曾做苦行僧,「他思考是不是要置自己於好苦的狀態,才可以修成正果?最後結論:不是。」
記得出獄第二天,周永康跟記者6小時無間斷對談,從那天開始感覺學運之子內心世界,跟當下真實世界一樣不澄明。傘運裏的hehe如今又怎樣?
「他情緒不好嗎?」記者問起岑敖暉近況。周永康說離開監獄當天,岑敖暉因為身體不適,沒有來見戰友。
「我也不好吖。」傘運3年後的今天,他如度苦海,接受訪問,用詞充滿猶豫不自知,瞻前顧後,怕自己開空頭支票,總是先求諒解再闡釋立論,今天,他太知道一句說話、一步路的重量。
他看民主不只是辯論,是以人為本,關懷人的需要,才有力量。「但過去一年,黃之鋒對人越來越關心,我好感動。」他在美國時,曾經去探梁天琦,兩人對靈修都感興趣,有好大共鳴,希望更了解自己,明白不足,做得更好。
重新建立信任 實踐政治
「你懂不懂看前面的路?已經有規劃還是在茫然摸索?這個旅程,這一刻你在哪一個階段?」記者問。
「我沒有這種智慧及高度去回答這問題。以我有限了解及知識,隱約看到前面是會去美國西岸UC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博士,未來幾年地理位置在此。第二個層面,將來是怎樣?我會覺得好扣連現在這刻。將來如何,跟我每日、每刻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有關。」他希望用每刻清醒,每刻堆叠,在日常中實踐政治、實踐方向、實踐自我價值觀,「前路不是說好多年之後,下一個剎那,就是你的將來」。
用行動去回答眾生的疑問,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他說:「修行人,則重一句話:Don't speak, practice it.生命實踐,人家會看見,看見時候你再說,水到渠成。」
「這些質素,去處理政治,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非常重要。人倫關係,人與人信任關係好重要,今天信心消散、崩潰,民主陣營好似大家都無信任,好多批評,不知從何建立信任,有時候,別人說的,只是換了語言,我們用慣常方式去說民主、自由,其實他們說的是相同的東西。」
8月入獄前,周永康特別去找何秀蘭道歉,因為知道她曾經對學生很失望。他還對記者提起見過佔領運動其中一幕,學生要把李卓人推出防線前面,想讓他去被警察打。他也很記得,獄中懲教職員問他:「20多年來,涂謹申做過甚麼事情?」這一刻,他用問題回答問題:為何香港多年學運、民主運動發展的內容,都沒有被書寫記錄?他做了一個行動:「阿涂,我投的票是給你的。」
春夏秋冬,日月如梭。下一個剎那,就是將來。
■記者冼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