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號風球翌日的金鐘,白晝恍如黑夜。煙雨淒迷之中,道袍一襲、盤髻留鬚的袁中平孭着古琴腳踏殘葉,頗添幾分仙風道骨。有老外佇足窺看,以為他在拍穿越劇。其實,這位離地得像古畫走失的高士,道袍下是牛仔褲、居美三十年最愛港式鳳爪;還是小鮮肉時更是個熱血band 友,與台灣歌手童安格等組成「旅行者」合唱團,風靡一時。

由吉他到古琴、少年到暮年、時裝到古裝、崇洋到慕華,袁中平的五十八載歲月在指隙間流轉。人生如琴,經歷風霜背後有無數故事,例如有關他夾band和戀上古琴的奇遇。
「他去了美國後便消聲匿迹。相隔三十多年後再見竟然變了個古人,完全認不出他。」袁中平一位台灣的老朋友說。
在香港訪問那天紅雨交加,袁中平抹去額上的雨水,他的徒弟笑說每次老師彈《瀟湘》就下雨,訪問前一天,他恰巧在揚州就彈奏了此曲。
有沒有一彈就轉晴的曲子?我問袁中平。
「有,待會彈首就會好。」
出身台灣文藝世家的袁中平家裏排行第五,大哥在美國是畫家,二哥是建築師。中學時已是合唱團團長的他在青葱的十九歲與童安格和邱岳組成了「旅行者」三重唱(Travelers),出道時鋒芒畢露,三子的貴族氣幾乎寫在臉上。旅行者的酷在於,專輯包括唱片封套設計、編曲、作曲、填詞與配樂主唱都由三位小鮮肉包辦,當時的袁中平寬膊、三角腰,男神模樣,還參演了好幾齣電影。
他還在電台主持過音樂節目,試過開咪跟着歌曲一起唱,招積地說:「讓我們聽袁中平與John Lennon二重唱吧。」他還有一句經典的台詞:「你如果不想聽,可以轉台。」兩年後童安格要到金門服兵役、袁中平負笈美國,旅行者從此散了心,時為一九八四年。
極度崇洋、搖滾入血的袁中平,原本琴、棋、書、畫一竅不通,竟然在異鄉戀上中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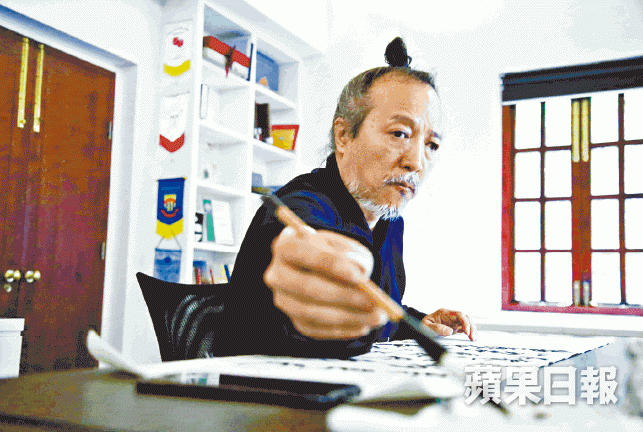
一聽如故
袁中平記得,當時他在大哥紐約家中聽音樂,爵士樂、藍調、印度音樂,無意間他聽到一張古琴的卡式錄音帶。「我一直在尋找甚麼是世間最好的樂器和音樂,那一刻我受到極大震撼,我說這是最棒的音樂,不只好聽而已,我覺得它跟我的血液和靈魂在呼應。」幾十年前的回憶,袁中平歷歷在目。
他從紐約坐火車到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找尋古琴的歷史和琴譜。美國買不到古琴,他哀求香港將到紐約演出的交響樂手替他弄來一把二手修復過的古琴。「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他時,也是下着濛濛細雨,那天是清明節,我擁有生平的第一把琴。」後來,「清明」二字亦成為他的齋號。
少年得志的袁中平以為有了琴譜,他就能自學上手,他幾十年與古琴的淵源與追求,就由打擊自信開始。「琴弦是三度空間,究竟應該這樣按還是怎樣按?必須人傳人。」他回到台灣拜師古琴家孫毓芹,「我父母跟着我一起帶着束脩,行三跪拜師禮。」古琴磨掉他的菱角,一年才只學到一首曲子。他慢慢領悟琴技是次要,琴德更重要。
記得曾經有一位琴人跟我說過一番話:「古琴,疾風甚雨不彈、於塵市不彈、對俗子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坐不彈……於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這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有着很深的內涵。
「琴代表德,所以我們彈琴是把內在修煉成可以與道相合,你必須要有德性,透過我們在彈琴的過程當中,從內到外溝通天地。」回美國後,他再到上海蘇州,拜既通古琴又擅太極的古琴演奏家吳兆基習藝,一學就是十年,直到老師過世。後來再跟隨中國近代書道大家張隆延學習書法,到處拜訪名山大川修養內心。「書法與古琴是一體的兩面,書即是琴,琴即是書。」示「琴書合一」為宗教的袁中平說。
古琴早期為溝通天地的法器,袁中平撫着琴細心地解說,古琴是接通天地人的載體。「它長三呎六吋五分,代表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琴面是弧形代表天,琴底為平面象徵大地。剛剛彈到這個泛音,聲音往上飄代表天;散音就是空弦,聲音向下代表地;第三個音是按音,按音是從手指之間感受感情的表現,這個代表是人。」
因為要學的太多,他從此沒有放下古琴,在紐約創設「中道琴社」、「紐約琴社」,到青島大學任研究室主任及教授四年,又在台灣設「台北琴道館」,以古琴教學為中心,並有書畫、花道、茶道與武術,培養現代人文武兼修的傳統才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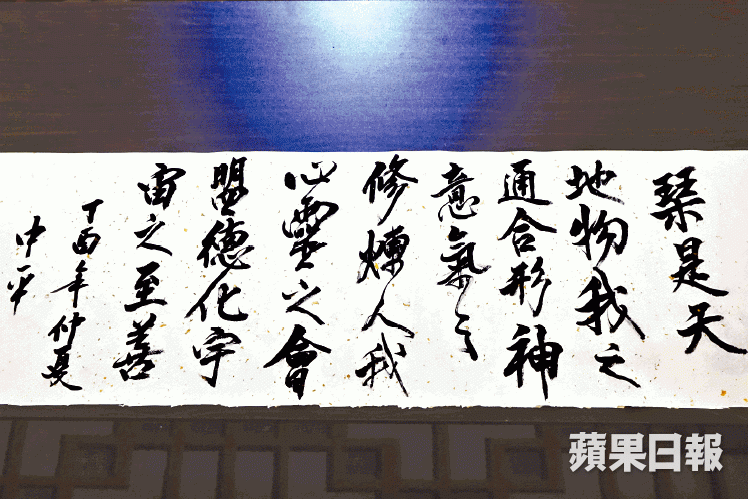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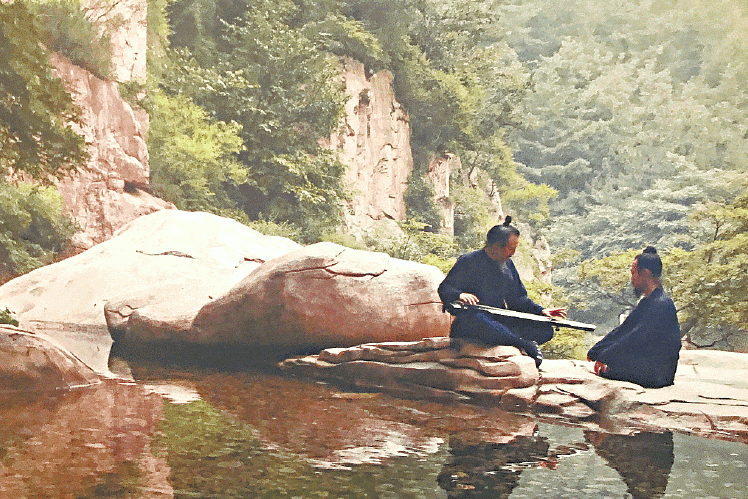

band友重聚
認識袁中平在友人的「六感生活館」,一個周末夜他過境深圳時順道留港,在茶館裏演出了一首《長亭怨慢》。我首次見人用古琴自彈自唱,他把姜夔的宋詞《長亭怨慢》譜上樂曲,琴風古樸蒼勁,運指內蘊沉着,曲詞幽幽動人。跟他聊得興起,我說快到台北旅行,他邀請我再去探他,想不到第二次見面他就換了形象。
在台北西門紅樓的live house「河岸留言」,袁中平拿着吉他自彈自唱,驅散了古樸,震撼來自那場演出,原來是曾經熱血的一班老band友的Reunion。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孕育在忠孝東路的IDEA HOUSE,曾是台北重要的live house,當年熱血青年四十年後重逢,只有袁中平一個還未「登六」。台上各人或許都戴着帽掩飾地中海和禿頭;或許要降key減低出錯的風險;索性唱《Doctor my eyes》來自嘲患上白內障,但重現的搖滾精神不死。
四十年後天變地變,情不變,那種互動、一起老去的經歷實在感人。
我與袁中平第三次見面在香港,他又切換成古人。高士愛泛舟湖上,我帶他坐天星小輪過維多利亞港,他在小輪上彈了一関小曲。因為填海過度,維多利亞港不及古時一條小河寬闊,小曲還未彈完我們便到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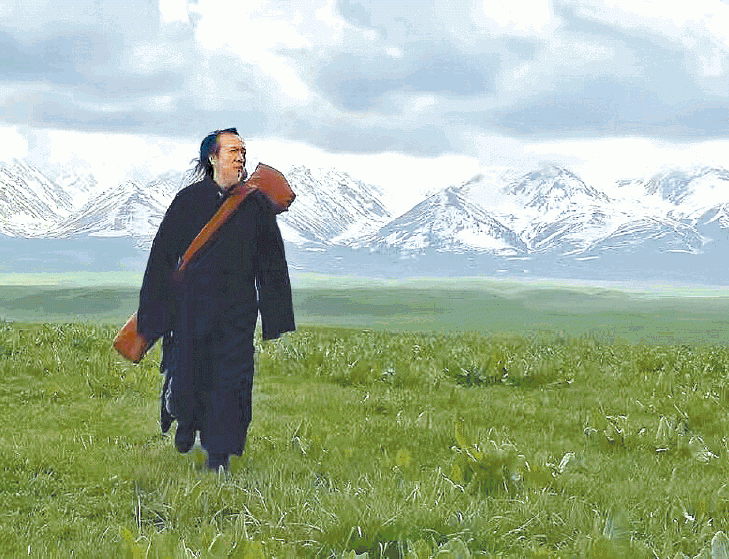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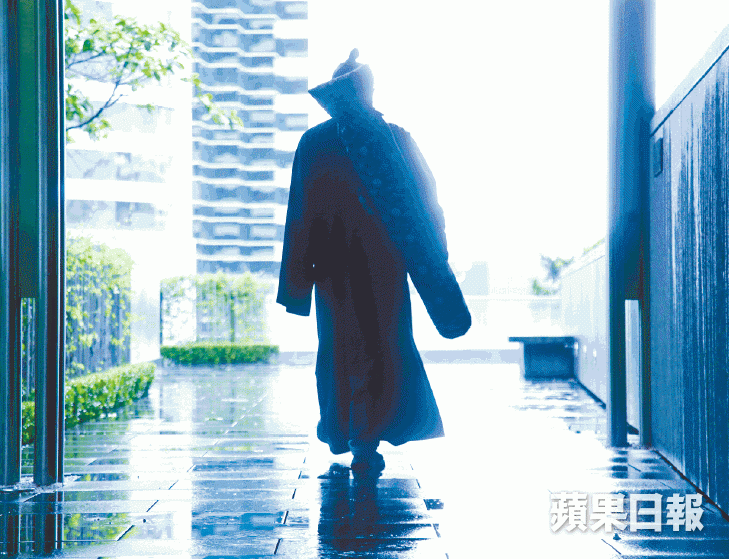

四無階級
袁中平戲謔自己是「四無階級」:無樓、無車、無妻、無兒,兩袖清風,了無牽掛。他只為自己的追求而活,道袍一襲攜琴走天下,踏遍名山大川,遍訪僧道高士。慢慢,他就沾染了濃濃仙氣。
走在石屎森林,途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着這位古人,但袁中平已經習慣,更坦言古裝比西裝革履更配合撫琴。「我這身打扮,不是為了接受採訪才穿的,平時我也是這樣。
問他何故要「奇裝異服」?他又說了一件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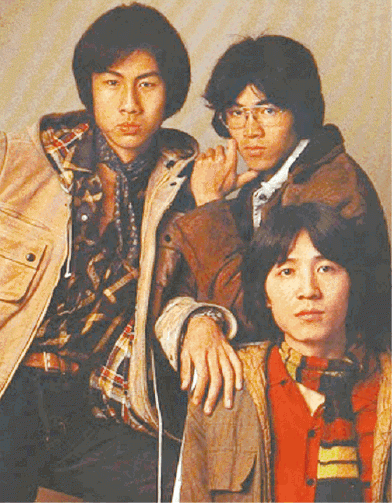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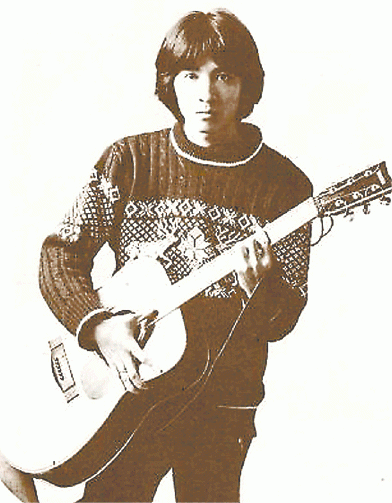

約二○○四年,袁中平任職青島大學古琴研究室主任及教授,遊歷青島嶗山華樓宮,該宮奉道教全真華山派。沒想到甫步入宮內,住持冷智慧撲通就下跪,對着他說「弟子叩見師傅」。
「他說就在我上山的前兩天,他忽發奇想把人家送他幾十年、壓在箱子裏的古琴拿了出來。他覺得這舉動很奇怪,就在廟裏拜了一拜抽了個籤,廟裏的籤聽說很靈,說將會有一個師傅來,所以我一到,他一聯想琴、師傅,就激動起來。」
結果,他便住到廟裏教主持學琴,他穿上和道士一樣的衣服。「住啊穿啊也習慣了,所以我說這衣服不能隨便穿,一穿上去你便被改變了。」袁中平笑說。
袁中平認為古琴是對人德性、內心和氣度的一種磨練 ,讓人不需要再用物質填永遠填不滿的欲望。「透過彈琴你就會更了解自己,所需要是甚麼,追求甚麼,或者生活和生命的意義。」袁中平抱着琴,遙望維港景色時說。
青海高原、戈壁灘上、廬山腳下、仙人洞內、梅樹茶會、黃河邊、玉門關……,處處留下他的蹤影和琴聲,他以琴聲獻給天地萬物。回到滾滾紅塵的紐約、台灣和香港,他大隱隱於市塵,家住陽明山之嶺最隱密的百年老宅,樂得逍遙。
我說世道很亂,香港很亂,袁中平抱琴自言:「無論世界如何快、如何亂,你的心都能處於這種靜的心態,就能冷眼面對世界。」他一身道袍在冷風中飄逸,凸顯儒雅的風采。
袁老師應我要求,彈了那首據說一彈就放晴的神曲《陽春》,轉瞬果然神奇地停了雨。
「早知道老師你一大早就應該彈。」我咕嚕,袁中平笑着,露出一幅天意不能挑機的容顏。
記者:鄭天儀
攝影:鄧鴻欣、許先煜(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場地提供:亞洲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