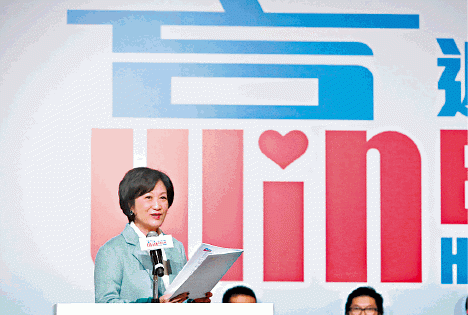王家衛話齋,每座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傳奇,擺渡人就是城市的英雄,替人解決問題,抵抗俗世洪流。香港設計界就有一位「擺渡人」,過去近一個甲子,滙豐銀行、連卡佛、香港賽馬會等都找石漢瑞(Henry Steiner)擺渡過,2000年他為香港印製大獎構思了以精子為主題的大膽設計,驚為天人;銀包裏找到的滙豐、渣打銀行鈔票,隨時是他手筆。
很多年前,大家已稱他「香港設計之父」,因為這位老外比很多本地薑還「香港」。生於維也納、成長於紐約的他,較香港第一代設計人靳埭強更早投身香港「開荒」。「當時香港設計領域是片處女地,大家對設計都沒有預視。」
我說:「你住港時間比我這個土生土長的人要久,名副其實『老香港』。」話未說完,83歲的石漢瑞搶白:「應該說,比大部份香港人還久。」他摸着滿頭銀絲說。
1961年還未有直航,他經三藩市、夏威夷及東京三度轉機,歷時一周從大蘋果投奔小香城,甫落機便被香港穿旗袍的女神們吸引,自此沒有離開過,與港人一同經歷67暴動、97回歸、03沙士、07金融海嘯,春去秋來56載。如今旗袍消失了,熱褲、迷你裙再性感還是難以媲美含蓄曲線的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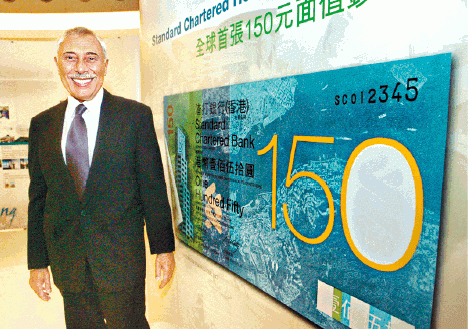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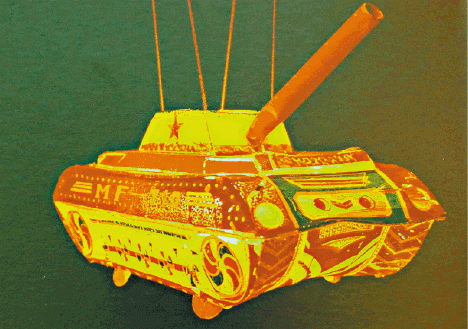
故宮海報 精心部署的失敗宣傳
從無到有,石漢瑞與不少國際設計師任意馳騁,在建築、規劃、品牌、生活各方面,與本土設計師、官員、大小企業合作,創造了無數有型價值。「設計師替別人解決問題,藝術家嘗試替自己解決問題。商標並非裝飾,而是企業身份象徵,與公司名稱同樣重要。」這品牌醫生,更熱衷為香港把脈,句句流露愛之深責之切。
「我對香港當下感覺是停滯不前(Stagnation),首爾、上海和新加坡都面對各自問題,但她們都比香港時尚和有活力,香港曾經擁有的『做得到精神』(can-do spirit)已蕩然無存,現在已沒有甚麼必能做到,反而很多事都不能做。」他認為,香港的無力感來自咋舌的生活成本及政府越來越多的「can't do」。
「最簡單你連出書都未必有自由,小店則被恐怖租金趕絕。」消失的、留下的,石漢瑞看在眼裏,他說自己居住的西營盤算是最能保留六七十年代香港風貌的角落,都已漸進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香港曾經美好因為很自由,香港需要開放,社會太多指令,不能這、不能哪,以前至少我們能講真話,表達意見,現在廣東精神都被壓抑,很失望。」老人說時一副不吐不快的模樣。
一個浮雲淡薄的下午,我和石漢瑞來到西九文娛區的M+展亭,一起看M+首個設計藏品展「形流意動」,從中看香港經濟轉型。除這個展亭,西九仍是個狼藉的建築地盤,前面不遠處就是鬧得滿城風雨、拍板後才諮詢的北京故宮分館將來的落腳地。「我覺得很遺憾,偌大的故宮海報貼滿中環地鐵通道兩旁,很明顯是精心部署的推銷行動,但我認為宣傳失敗。港人可以親身飛到故宮參觀,為甚麼要故宮遠道來設館,展示小規模但相同的展品?」抑壓得最深的彷彿是他自己,他連珠發炮,好像連呼吸的停頓都嫌太長。
「政府好像已不再人性化,難與市民對話,我會稱之為官僚喪屍(bureaucratic zombie)。」石漢瑞悻悻然加上註腳。
看到已故日本著名設計師龜倉雄策的海報,他又進入一陣沉思。「當我看到他的日本67奧運、70年世博和Nikon的海報,我感到苦樂參半。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設計,但仍很美麗、長青不老,但香港的設計……『垃圾』,大家還不覺可惜,尚希望外界以屈尊俯就的姿態來接納?很令人失望,因香港可以做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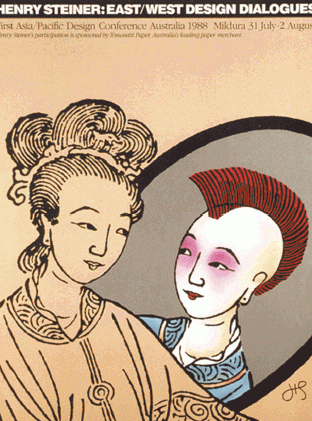
less is more 飛龍淪為破爛龍
1997年,石漢瑞還自資出版小書《Foolish Things》,當中收納了12件港產名物,包括天星小輪、白花油、當舖招牌、竹棚、梁新記牙刷、坦克造型的燈籠,還有電車。「電車最能代表香港。如果回歸廿周年我再做那本書,我會放王家禧的老夫子進去,因為他很有獨特的香港精神,也很幽默。」回憶那些年,他印象中的香港每天像一粒跳豆,充滿活力,也很classy。「Made in HK」除功能實用,還講求美感。他指着2010年香港被立命為「亞洲世界城市」的飛龍設計搖頭,紳士如他似是憋了很久,擺擺手補一句響亮的:「failed。」「很不幸,這設計竟代表政府。有人說它像一頭狼,它的賣點是裏面隱藏了香港和簡寫HK、彩帶勾勒出獅子山,但誰會看到呢?我形容這條飛龍是破爛龍(tattered dragon)。」石漢瑞強調了兩次,再說香港是亞洲世界城市,已不合時宜。石漢瑞師從設計大師Paul Rand、在耶魯大學師從Herbert Beyer,算得上是包豪斯第三代,自然是less is more 的信徒。
昔日香港,百業待興,物質講求耐用,修補完又輪迴重生,衫褲鞋襪、鉸剪菜刀、單車鐘錶、家具電器,連絲襪都有得補,而且是門絕活。石漢瑞記得以前常在街上遇上修理工匠,一位很老的改衣師傅因負擔不了高昂租金,從此在社區隱了形。一位又一位師傅在時代巨輪下消失,也斷絕了物品轉世重新的機會,「上一代其麼都可以修補,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
記者:鄭天儀
攝影:伍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