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籽:假日散心】
多得高鐵大白象,「牛潭尾」這個地名在幾年間聲名大噪。牛潭尾位於東元朗,包括牛潭尾村、圍仔村、上下竹園村、新圍村等多條村落,當中佔地最廣的牛潭尾村,又名攸潭美村,大部份居民自五十年代在此落地生根,靠山水養魚務農,自給自足。這片元朗最後靜土,近十多年來被貨櫃場、物流倉侵蝕,二零一一年高鐵動工後更是變天,山崩地裂,水井乾涸,老村民生活大受影響,至今仍未解決。在當地服務多年的救世軍,聯同「文化葫蘆」及一班藝術家與師生,走訪攸潭美村,以壁畫、家具粉飾村屋,在村內手製二十一個遊覽路牌,並定期舉辦藝墟、導賞團,趁牛潭尾未消失,讓城市人遊走探索。
攸潭美村自一九零五年開始有人聚居,全盛時期村民數千,不少村民靠農牧業養大一家人,現在村內有二百戶,約有逾二十戶仍耕種養魚,整條村共分東區、中區、西區及南區四大區域,由攸美河及一條車路貫穿,由村公所起步,城市人在鄉間小路遊走,菜田魚塘盡入眼簾。
「以前全部都是茅屋,打風落雨呀,驚到腳毛都甩,茅寮唔穩陣,風一陣一陣吹來,天花板都吹得走,要搵嘢撐住道門。」在東區居住七十年的青哥,形容舊時村民生活艱苦,金工木工皆拿手的他,早年在家門前建涼亭,添置膠椅,方便街坊吹水,藝術家張瑋晉便帶同學生,以回收卡板美化涼亭,為這裏增添十多款手工椅子,「卡板這種物料在香港比較容易找到,村內也有,加入插畫、編織椅墊等卡板凳都是由學生設計。」涼亭還設有路牌,記錄小涼亭的故事,「我們覺得村民在涼亭聊天好開心,像開派對,便在路牌上畫了在跳舞的村民。」除了涼亭傢俬,他們也為行動不便的村民改善家居設備。

藝術家美化 巨型壁畫諷發展
藝術家何文聰與另一學生團隊,則入村了解村民生活,將他們的故事刻畫在二十一個木製路牌上,方便遊人了解村落故事,路邊荒廢的「兄弟農場」,也有段古,「養雞業經歷兩劫,九十年代初政府收緊環保條例,雞舍需加設排污水設備,很多小型農場無力加建而結業。」兄弟農場捱過到第一劫,也難逃二零零三年沙士滅雞命運。由東區走到西區,經過村民的菜田、魚塘、蘆薈田、金魚場,來到停用十年的攸潭美學校,「三十年代因為要起學校,村民認為以牛潭尾作為校名不夠優雅,自此牛潭尾村也改名為攸潭美村,所以兩個村名也通用。」村校於一九三一年由私人出資修建,六十年代學生人數急增,得政府資助兩度擴建,黃金時期全校超過五百人,荒廢的校舍仍滿載村民回憶。
離開村校向西區進發,抬頭遠眺氣勢磅礡的綠林山嶺,卻被高鐵的通風樓大殺風景。插畫家李香蘭,與學生在村內繪畫四幅巨型壁畫,當中位於受高鐵工程影響嚴重的西區,也是他們的重點着墨之地,村公所門外看似和諧的壁畫,正是諷刺鄉郊發展政策,「畫內的樹其實是裂痕,城鄉發展好像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同時在破壞大自然生態。有一次在村內見到好多工業和電子廢料,隨便掉了出來,破壞了農作物。」畫中以電路板星斗圖案諷刺發展破壞村內風景。
高鐵惹的禍 裂痕斑斑的家園
水源主宰村落的原始鄉貌,牛潭尾河道多年來經歷多次重創,七十年代興建錦綉花園、八十年代建造牛潭尾濾水廠,也影響河道井水,二零一零年逃過發展為「綜合發展用地」,但後來動工的高鐵工程使地下水流失,影響近年湧現,令依靠井水灌溉農作物及養魚的村民叫苦連天,部份更因而被迫放棄耕種,「港鐵二零一零年來動工,開鑿及鑽挖地底隧道時,我們就覺得奇怪,點解越來越少井水?」周貴賢村長說,全村約二百三十多個井,估計已有十三個乾涸,其中距離工地二百米的六號井,乾涸情況就最明顯,「六號井約十呎深,水不斷噴出來,會沿坑渠流入成個區,村民用水來種植,但去到二零一一年已經冇晒水。」
水土流失,令上層土壤沉降,破壞地面建築,部份西區村民的房屋出現地裂及裂縫,老村民羅生慨嘆裂隙日益嚴重,「以前就裂少少,而家越來越犀利,高鐵有來幫我屋企整鋼筋,但周村長表示,港鐵已着手處理,暫時只跟進小型工程,為居民作小修小補,城鄉發展的影響還是未知之數,趁原始鄉村風貌仍在,不妨參加救世軍及文化葫蘆定期舉辦的生活墟及導賞團,入村呼吸香港現已不多見的鄉土氣息。







手做路牌 刻畫村民故事
蘆薈場
前身是養殖金魚場,90年代改為種植蘆薈,透過村內的「菜站」運送至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寄賣。


金魚場
場主父婦多年養殖觀賞魚,魚塘規模完善,金魚會銷售至歐美各地。


兄弟農場
2003年結業的兄弟農場,一個雞舍可以養2,000隻雞,全盛時期養雞十萬隻。


攸潭美鄉立公校
學校的後門通向街坊在家門經營的小食部,方便學生小息時購買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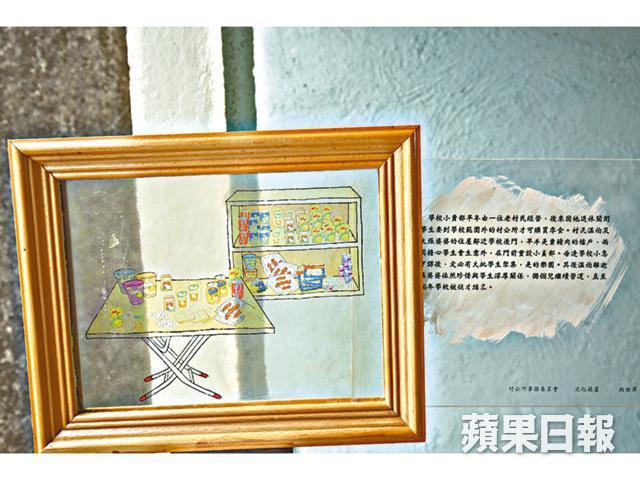
牛潭尾生活墟
日期:20/11/2016、08/01/2017
時間:2:30pm至5:00pm
地點:攸潭美村公所
交通:元朗市中心乘37號小巴於攸潭尾村公所下車
記者:王佩兒
攝影:陳健邦
編輯:謝慧珊
美術:黃創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