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p on me(踐踏我),來!」攝氏三十多度艷陽天,日本越後妻有的農田上,蚊子與紅火蟻盛情招待,有人突然躺在髒兮兮的泥土上,請農夫和學生們當她地毯來踩,在場當然沒有一個人伸腳,O嘴伸脷的佔大多數。
烈女3.0,這是68歲的伍宗琳(Dora)給我第一印象。她在富豪中早已很「另類」,曾以一元租金,把商舖租給經營環保時裝社企Green Ladies,又曾主動保育跑馬地古建築,還承辦過「百無禁忌」壽衣展。
「我甚麼出身?灣仔婆娘囉。」場景切換至灣仔集成中心,過千萬當代藝術品簇擁的藝廊空間,搖着香檳的伍宗琳吐出這番話,空氣頓然添加一陣麻甩味。從來,在這位別人口中Dora姨姨的字典裏,就缺了「身嬌肉貴」四個字,那管她是集成中心始創人、已故「棉紗大王」伍集成的掌上明珠。
「富二代」這稱號於低調的伍宗琳,應該老土過八股文。
香港寸金尺土,發展商無所不用其極,把公共空間榨乾為商場;她做逆風者,把港島核心地段的商場劃為公共藝廊,家族地標集成中心逾二千呎商場舖位今年中開始變身成Our Gallery,無償讓所有人接觸藝術,標榜任摸任睇唔嬲。「藝術有乜咁巴閉?藝術屬於每個人的,不論你是誰。我不售賣藝術品,目的只是分享,作為讓公眾欣賞藝術的平台,學生哥、BB仔得閒入嚟睇書坐吓,婆婆行累了又可以入來嘆冷氣, that's it。」她豪氣過灣仔之虎。




大方 藝術品任摸唔嬲
過百萬元、被喻為似薯片的Anish Kapoor經典裝置掛在門口當眼處,Lucio Fontana的《空間概念》、Agostino Bonalumi的《白色》、Richard Serra的《伸延3》、Alberto Burri的《黑白駝背》散落斗室,她對極簡主義情有獨鍾,炙手可熱的當代藝術家作品,任人觀賞。巴基斯坦買的地毯、印度旅行時買的小凳戰利品,都是她想跟社區分享的,更索性把畫廊稱為Our Gallery,意味是屬於大眾的公共空間。
伍宗琳喜歡藝術的原因很純粹,收藏哲學也很簡單。「談不上哲學。我喜歡就買,心情不好就買沉鬱的,開心時會找些很奇趣的藏品。對不起,藏品不一定能滿足大家口味。」她最喜歡的作品,是搞鬼歐洲藝術組合Elmgreen & Dragset的《但我在客人名單上呢》,佇立於藝廊當眼處。那是藝術家2012年的作品,一道超大尺寸的鏡面鋁門,上面寫着「VIP」,門開了個縫其實是打不開的,旨在挑戰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和體制。展覽開幕當日,她特意安排凶神惡煞的守衞看管這大門,VIP其門不能入,令接受與排斥之間的界線變得含糊,相當諷刺。
「我很感動,覺得作品反映到我內心。」她覺得好玩,對這作品一見鍾情。階級觀念在她看來,從來是不文明觀念,誰擁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威?誰又在無聲吶喊?
Elmgreen & Dragset最愛拿歐洲歷史文化符號來調侃,包括屹立世界各地的美人魚像、音樂家的巨型肖像及男童騎着搖馬的雕像等代表作,不時譏諷商業對藝術領域的侵蝕、資本主義制度。伍宗琳有幸到過他們由貨倉改裝成的工作室參觀,說是畢生難忘的有趣經歷。
從來,美術館、畫廊都是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伍宗琳不這麼認為,至少在她的主場。
「當真讓人觸摸你的藝術品?」我問。
「摸就摸吧,請清潔嬸嬸抹乾淨不就行了?」伍宗琳這位聖保羅男女校校友答得直白。
「弄壞了不心痛?」我亦步亦趨。
「有買保險嘛。只要不是刻意人為損壞,像黃毓民掟杯,我就沒辦法。」烈女依舊一副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改的表情。
伍宗琳更出動自己讀過的私伙珍藏書籍,充實藝廊的圖書閣。分享是件開心事,唯一不爽,是近日竟發現有文雀偷去部份藏書,皆因很多都是絕版收藏,讓她感心痛。圖書閣貼上告示,請公眾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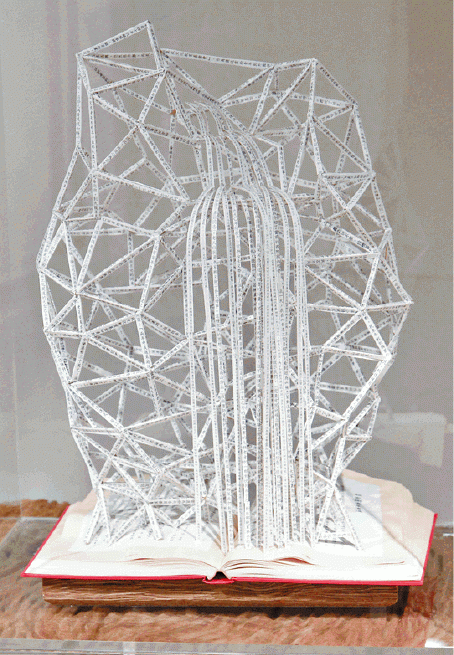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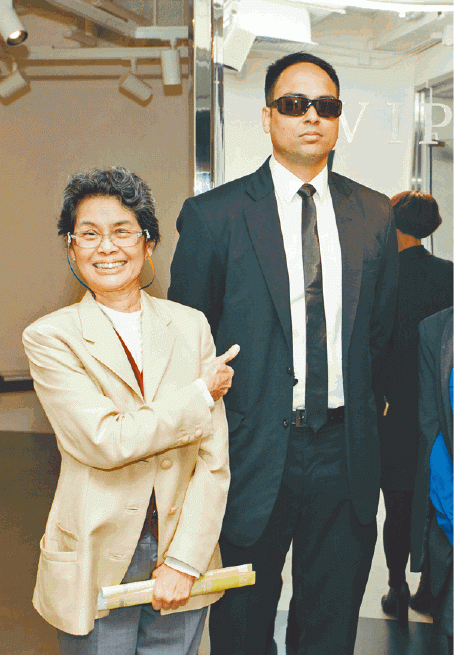
愚孝 服侍父親剪腳甲
至於現在舉行的展覽是與馬寶寶社區農場及鄉土學社合辦的《大地予我》回顧展。 《大地予我》是去年「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其中一個參展項目,《大地予我》意欲探討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存,並以加強港日兩地文化交流為目標。是次展覽報告了整個計劃,藉此機會向公眾介紹自然永衡法概念的耕作方式。
「叫人踐踏我因為感動。我哪厲害呢?全部都是學生和農夫們、有想法的人實踐整件事,我想向他們致敬。」回溯文首做人肉地毯一幕,她毫不忸怩地說。看到學生被大地藝術祭感動和改變,縱被你踩在腳下也矜貴。
草根貴族是如何煉成的?伍宗琳說受親民的父親影響。
伍集成經營棉紗貿易生意,當年獲港府特別發出「100」車牌,但作為超級富豪,他卻每天堅持乘電車上班,還到處宣揚他的「電車罰企論」,指自己乘電車永不坐着,一定站着雙手拿着扶手,一來訓練身體不懶惰,二來電車徐徐而行有助血液循環。他為人節儉,領帶都不願買,用航空公司的贈品,一生人也不遊埠。
「他總是慳自己,對別人好,影響我很深。」談到已離開22年的父親,她說:「我不知父母是否痛錫我,不錫都沒辦法,因為得我一個,我是兒子也是女兒;也不知甚麼叫親密,怎敢親密?以前的老人家都很嚴肅,很惡。」
父親生命倒數的日子,伍宗琳寸步不離的照顧他,甚至住到醫院裏,服侍父親剪腳趾甲、按摩、讀報,連續幾個月每晚睡不到三小時。「他病重,我是一百個願意照顧他的。」她在悼念父親的文章如是說,一種無我的愚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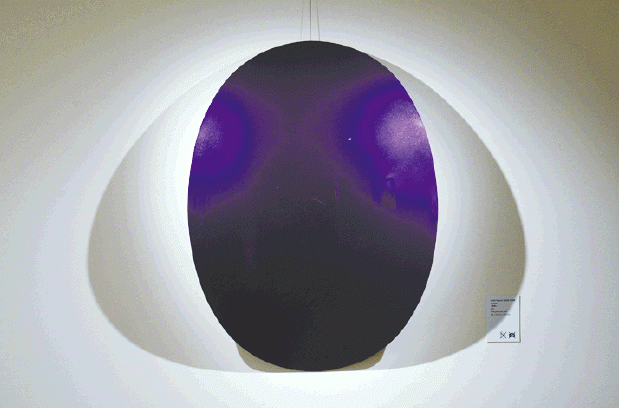


勤力 每天最早上班
飲水思源是父親的處世哲學,伍宗琳特意請藝術家Stephen Doyle製作一件有父親精神的藝術品,結果以伍集成的自傳轉化為裝置作品《疊水河》。「他沒有看過這本書,也不知我父親是誰,我就跟他說爸爸是充滿力量的人。」
坐擁至少十八億元物業,富貴如伍宗琳,今日仍然勤力,每天最早返公司,似父親,但她同樣心繫藝術事業。「我唔識藝術,但鍾意。」無尾音的回應顯得更堅決。
世上有沒有一個藝術空間,是伍宗琳最仰慕的烏托邦式美術館?「有,在心中,能做到就不是烏托邦。」說罷,伍宗琳又優雅地搖着香檳,像蝴蝶飛快地遊走收藏品中,她哪像一位姨姨?明明是位少女,剛烈品種。
記者:鄭天儀 攝影:鄧鴻欣
(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